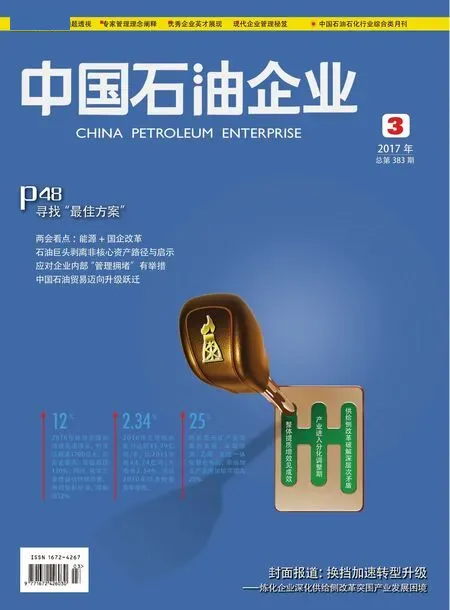角色錯位
角色錯位
企業“小社會”成氣候,不僅是社會分工上的倒退,還破壞了市場經濟公平法則。
國企“小社會”規模究竟有多大,估計沒有人能提供精準數據,因為這個數據過于龐大,且處于變化之中。而媒體目前引用的數據,是國資委負責人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報告時的估算數據。國企辦社會職能主要包括員工住宅“三供一業”(供水、供電、供氣及物業)、離退休人員管理、承辦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和消防市政等其他機構5個方面。央企目前有上述5類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年度費用800億元;地方國有企業年度費用超過1000億元。201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就“國有資本管理體制改革研究”這一課題,專門深入全國多地區展開調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袁東明參與了此次調查。
“國資委已開展三次全國性摸底調查,但一直都無法獲得準確數據。一是各地填報數據可比性差,難以直接加總。目前雖已明晰了5類企業辦社會職能機構,但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很難以一個口徑準確界定成本負擔范圍和移交費用標準,各地對企業辦社會范圍、標準等理解也不一致;二是地方和企業不合理預期會夸大費用規模。自上而下的摸底調查會給地方和企業形成不合理預期,即上報負擔越大,未來獲得的補助會越多,由此會擴大企業辦社會范疇,夸大費用支出規模;三是實際所需費用彈性很大。如‘三供一業’移交,地方一般要求‘先改造后移交’,改造標準、移交費用等都是多方談判的結果,彈性也非常大。”
一直以來,困擾分離國企辦社會職能主要存在底子難摸清、費用承擔主體難確定、地方承接有難度三個難點。對于上一輪改革成績,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邵寧在其主編《國有企業改革實錄》中透露,在2002-2007年國企去社會化改革中,已剝離1.1萬個國企職能機構、分離72.24萬人,特別是國企辦普通中小學和公檢法機構基本實現了分離。
現在雖然底子仍然難以摸清,但費用承擔主體和多方分攤機制已確定,因而實際操作已具備可行性。“從時機上講,現在分離移交難度確實比以前更大,不過國企改革的一個特點就是,改革條件比較好時,改革者主觀意愿并不強烈。改革大都是倒逼出來的。”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表示,按照深化國企改革指導意見時間節點,到2020年,國企改革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現在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了。
應該說,企業辦社會是圍繞新中國工業體系建立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產物。對資源型老國企而言,大都地處偏遠地區,社會化服務無從談起,很多生產生活配套設施都需要企業自身完善,當時辦社會也是企業的無奈之舉。但到了社會化服務高度發達的今天,繼續承擔辦社會職能,無疑是“帶著鐐銬舞蹈”,很容易被輕裝上陣的外企、民企甩在后面。
“國企改革雖然經過了近30年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仔細分析,它很多方面是非常不徹底的。政企不分這個改革是不徹底的,企社不分這個改革也是不徹底的,財務約束的改革也是不徹底的,這3個不徹底就是國企市場化改革非常不徹底。企業‘小社會’成氣候,不僅是政府和企業在社會分工中的‘角色錯位’,而且還會破壞社會效率和公平。”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稱,“日本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在考察完中國企業承擔的社會化職能之后,竟然發出‘我的印象是,中國不存在企業,至少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這樣的感慨。我認為這種感慨是理性的。”

企業與政府的分工是社會分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社會追求公平與效率的必然結果。其中,企業通過市場等價交換,在利益驅動下提供價廉物美的商品,滿足私人需要,并為產品質量和安全負責;而政府則通過強制性征稅,提供通過市場機制無法提供的產品,即公共產品,也應對其提供的公共產品質量和安全負責。這就是說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企業的歸企業,各司其職,而“錯位”的結果只能是企業不為效益負責,政府不為公共產品負責,而市場最終會拋棄政府和企業,按照自己的邏輯運行。可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我國國有企業“越俎代庖”,承擔了本應由政府和社會承擔的公共產品職能,形成了企業“小社會”現象。并且,從經濟學角度看,本應通過市場機制以競爭方式提供的私人產品,卻采用無償的、非競爭方式提供也必然是低效率的,前者是提供主體錯位,后者是提供方式不當,兩者都是由于角色錯位造成的。 盡管企業辦社會曾對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但這種以犧牲公平與效率為代價的生產模式成本也是很高的。眾所周知,國有資產應是為全體生產資料所有者服務,而經營“小社會”僅僅是為各企業內部員工家屬服務,無疑是違背了國有資產的資本屬性,造成社會分配不公。從國有資產效率角度看,這種非生產性資本大量被占用,本身就降低了國有資產的產出率和利潤率。從企業經營成本角度看,企業經營成本必須為提供經濟效益而支付,但在企業承擔社會職能情況下,其相關人員必然產生勞動付出,企業也必須給予勞動報酬,由此形成企業成本。但問題的關鍵是,承擔社會職能人員所創造的效益是社會效益而不是企業效益,其成本與效益扭曲,在相同勞動生產條件下,必然使經營“小社會”的企業效益低下,失去在市場競爭中的優勢。更重要的是,由于國企承擔“三供一業”和其他社會職能,使得自身變成“半福利機構”、“半政府機構”,嚴重制約了市場化改革向縱深發展。
“不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構建現代企業制度,以及強化國有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就無從談起。”作為國資國企改革的參與者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院副院長王繼承稱,“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啟動以來,國資委已把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這是對企業負責,也是對歷史負責。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總指針。對央企來說,就是要在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而在更深的層次和意義上,剝離國企辦社會職能是10多年前中央就做出的承諾,10多年過后,這一工作并沒能完全讓公眾滿意。如果在新一輪國企改革還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將更加透支政府信用,既無法向公眾交代,也無法向企業交代。一言以蔽之,如果說國企辦社會在計劃經濟時代是一種必須的話,在今天則已成為阻礙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的一大障礙。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不僅關系新一輪國企改革成敗,也關系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因而必須把剝離企業社會職能提升到關系改革成敗的高度來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