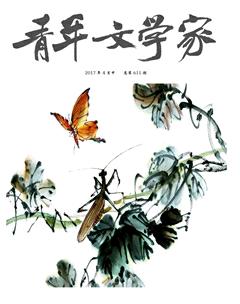從建構與重構看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嬗變
周志峰
摘 要:最后一位京派傳人汪曾祺,在早期受沈從文等諸多因素影響,所建構的小說無論在思想還是在藝術上都帶有刻意模仿的痕跡,尚未形成自己獨有的審美趣味和風格;而在八十年代以后,汪曾祺對自己的部分小說進行了重構,改寫后的小說,較之于先前有了自己特有的審美傾向和創作個性。探索其重構的表征,研究其重構的緣由,對于分析汪曾祺小說的發展與嬗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建構;重構;嬗變;戴車匠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1-0-01
汪曾祺,作為京派的最后一位傳人,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學術界對汪曾祺的研究也比比皆是。然而,這些研究多是停留在單一的作品或文學史意義等層面。但縱觀汪曾祺的創作,不難發現他在后期對諸多的文學作品做了重構,而對于這一重構的表征和緣由卻少有涉足。因此,本文以他的兩篇《戴車匠》為例,探索其小說的嬗變與發展歷程。
一、建構與重構的表征
(一)思想主題的人道化
兩個版本的《戴車匠》所要表達的都是“最后的車匠”和“沉默的城”這兩個主題。但由于在繼承與嬗變中,側重點和程度的不同,使得1985年的重構呈現出思想主題更加人格化的傾向。
首先,對“最后的車匠”的繼承。兩個版本的《戴車匠》,都共同表達了“最后的車匠”這一主題。從表層上傳達出了對傳統手工藝消逝的哀婉,又暗含了對傳統優秀文化流失的思考。面對追名逐利,世風敗壞的當下,作者希望虛構一種寧靜而又優美的烏托邦世界,來與現實形成對照,表達對優秀文化、民族精神流失的擔憂與思索。
其次,對 “沉默的城”的重構。1947年的小說描繪了小而充實的店鋪和戴車匠的生活方式,他 “只是緩緩地,從容地與他的時光廝守”[1],他的個體生命中包蘊著中國人堅韌、勤勉等諸多品性。這座城,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和其比肩的是“邊城”、“果園城”、“呼蘭河[2]”。另外,小說的第一段,運用大量的筆墨插入了對兩個老太婆的敘述。她們時而和顏悅色,但更多的是處心積慮,處處為自己謀利;而1985年的重構,作者便基本上略去了對“沉默的城”的寫照。一方面,作者回鄉時,戴車匠店已不復存在了。這種省略表達了作者對故鄉、童年的追憶與隱忍的惆悵。文本顯得更加溫和,顯示出其人道主義的關懷。
(二)敘事風格的個性化
本文以清明節孩子們玩“螺獅弓”這一情節為例,從敘事語言及風格層面來探討汪曾祺小說在何種程度上呈現出個性化的傾向。
在語言層面,40年代的版本用了更多的筆墨來敘述這一情節,有許多刻意模仿的痕跡和重復之嫌。而80年代重構的小說略去了過多的細節刻畫,緊緊圍繞著清明風土人情這一意境展開敘述,顯得更加簡潔明快,清晰質樸,更富有詩意。這種嬗變可以看出他對語言的重視。汪曾祺本人也說:“我很重視語言,也許過分重視了。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只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3]。”
另外,還應注意重構后筆調的散文化。汪曾祺自敘:“我不善于講故事。我也不大喜歡太像小說的小說,即故事性很強的小說。故事性太強了,我就覺得不大真實。”[4]他成熟后的小說不再注重傳統的人物、情節的刻畫,而是僅僅圍繞某種意境與氛圍展開。因而,他省去了細節性較強的戴車匠與孩子的互動,略去了富有情節性的老太婆和戴車匠生活方式的敘述,而留戀于無完整情節與人物的風土人情描寫。這也使其小說更“純”。
二、建構與重構的緣由
汪曾祺處在傳統與現代更迭的時代。因而,受時代影響,他的小說一方面帶有濃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另一方面又具有西方的現代意識。其小說的重構與嬗變,與他的成長經歷、創作經驗、求學歷程等有著密切的聯系。
(一)傳統文化與師承關系的影響
汪曾祺的小說傳統文化底蘊豐富。這一方面來自家庭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受學校教育的影響。其父汪菊生溫和的性格,對他日后的創作與審美旨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后,他進入學校學習了中國古典文化,受儒家文化熏陶,形成了濃厚的傳統與民間文化氣息。另外,汪曾祺的恩師沈從文也對他獨特風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沈從文樸實文字傳達的清晰的故事和健全的人生形式,成為汪曾祺其后創作的有益養料。另一方面,沈從文對自己小說重構的習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汪曾祺80年代對自己審美天地的重新建構。
(二)西方文化的沖擊
當汪曾祺進入西南聯大求學時,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沖擊。西南聯大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辦學氛圍,促進了各種文學潮流、文學創作藝術的涌入。紀德的“純小說”風、卡夫卡象征暗示的手法、契訶夫隨意自由的語言,批判與溫暖的情懷都對汪曾祺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三)人生閱歷的變化
汪曾祺的一生是充滿坎坷與磨難的一生,母親早逝,在反右斗爭中被劃入右派下放、文革中受到打擊和壓抑等等。在經歷了無數歲月與世事的滄桑變化之后,老年的汪曾祺內心更加趨于平靜與安穩,有一種看破紅塵的坦然與隨性,也充滿了溫情脈脈的人文關懷。因此,在80年代的《戴車匠》中,汪曾祺刪去了對兩個老太婆的生活方式的描寫,由最初的冷漠態度變得更加平和,給予了她們更多寬容。
綜上所述,汪曾祺受生活經歷、師承關系、求學經歷和人生閱歷等諸多因素的交織影響,在80年代對前期的部分小說進行了思想內涵和敘事手法上的重構。在這一嬗變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和審美觀念,其作品也走向了成熟。80年代后的復出,使他在文學史上獨樹一幟,成為現當代文學中一位杰出的大家。
參考文獻:
[1]張雪蕊.寫和重寫[J].名作欣賞,2011(25):27-28.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3]汪曾祺.矮紙集[M].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
[4]汪曾祺. 汪曾祺短篇小說選[M].北京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