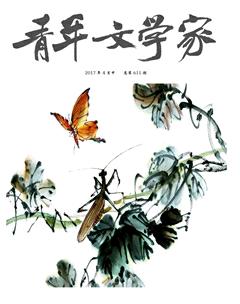酒主沉浮
摘 要:酒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而“禁酒”則是中國傳統酒文化中一個極為有趣的現象,它往往同國家意志相關聯,在時代的發展中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豐富的內涵。本文以《尚書·酒誥》等數則材料為具體分析內容和文化個案,力圖揭示“禁酒文”的豐富性,略窺其背后深刻的社會與文化根源。
關鍵詞:禁酒;政治;文化
作者簡介:嚴東(1992-),男,四川廣元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1-0-03
1、引言
酒的產生與發展催生了豐富多彩的酒文化,有文人雅士宴會餞別時飲酒賦詩,有品評鑒賞美酒佳釀的專門著述,在民俗史和文學史的書寫中,酒一直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古代統治者多從政治角度出發,把飲酒這一日常行為同國家政治命運相聯系,催生了“禁酒”的現象。
目前學術界對酒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涉及酒文化或專門對酒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論文頗豐,主要有:郭寶鈞《中國青銅器時代》,莊華峰《中國社會生活史》,謝文逸《中國古代陶瓷酒器的發展》,吳傳梅的《飲酒與酒文化——酒文化雜談》、孫婷婷《先秦時期酒文化探析》、徐少華《中國酒與傳統文化概論》等。而致力于研究“禁酒”現象的,數量較少,主要有陳兆肆《芻議古代禁酒令》、黃修明《中國古代酒禁論》、夏家駿《歷代酒禁與刑法》等寥寥數篇,但這些論文也大多停留在對歷代施行“禁酒”現象的列舉,對其背后的社會和文化根源并未做更多的分析與探討。
本文從先秦“禁酒”的相關記載中,擇取出《尚書·酒誥》篇、《晏子春秋》中晏子勸誡齊王數則材料作為文本細讀和分析的對象。目的在于,通過對“禁酒文”的時間、背景以及內容的分析,將當時的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欲窺一斑而知全豹,力圖揭示出其文化與社會根源。
2、先秦“禁酒”論
同酒有關的故事可追溯到上古堯舜禹的時代,或以為三皇五帝時代之事不足為征,須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來對待相關材料。《戰國策·魏策二》記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1]禹在飲下臣子進獻之美酒后,敏銳地意識到酒對人巨大的誘惑力,從為君者的角度而言,沉湎于酒或將不利于統治,因此提出了極有遠見的“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的警示。
禹的預見在夏、商兩代得到證實。漢劉向《列女傳·夏桀末喜》:“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道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2]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紂)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3]桀紂很早就被視為以酒亡國的典型,也即意味著古人很早便將“酒”同“禍”聯系起來,統治者縱酒或戒酒的取舍便成為統治能否長久的影響因素。
殷周鼎革,原本為殷諸侯之一的周取得了天下。《酒誥》一篇,是周公針對殷人尚酒、總結殷商滅亡經驗教訓而發的誥辭,從中可以看出周公對于酒的態度和政策,亦可看出當時的社會和文化狀況。
《酒誥》中涉及到了文王對于“酒”的態度,其具體內容如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4]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5]
文王鑒于商紂王荒淫敗亂的教訓,明確了三個原則:一,酒是祭祀用品,多用于祭祀先祖和天地的場合,平時不常飲;二,祭祀之時飲酒也須有度,要以德自我規范,勿令至醉;三,戒誥的對象是少正、御事等官吏。周人對于祖先神的崇拜意識十分濃厚,因而文王之教里指出祭祀必須要用酒,酒同祭祀這類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相結合,必然導致從禮——即制度的層面對于酒予以規定。文王接著又說明即使是在祭祀這類可以飲酒的場合,也須有度,防止過度飲酒導致失德。在周時,生產力還不是很發達,酒相對于平民百姓而言是一種奢侈品,酒是當時的貴族才能享用的,因而文王誥教的對象是眾國眾士各級官吏。
周公繼承了文王的政令,在《酒誥》中他對于用酒和禁酒做了更為細化的規定,具體內容分別論述如下。用酒的規定: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6]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7]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偽孔傳解釋為“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孔穎達正義疏云:“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8]從偽孔傳和孔穎達正義來看,這里強調的是“勤商得利,富而得養”,也即子女贍養父母,若沒有多余的收益而要厚養,是有損于家產的;倘若子女從事商業活動,“載其所有,求易所無,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這種情況下厚養父母是值得肯定的,厚養父母的“珍異”之物即酒。這表明在當時生產力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酒仍屬于難得的珍異之物,而周公鼓勵“以有易無”的原始物物交易活動,穩定了社會局勢、促使周從殷周易代的戰爭中盡快恢復過來。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偽孔傳解釋為“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孔穎達正義疏云:“釋詁云:羞,進也。若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事可憂,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9]“耇”即傳文中所謂“老成人”,本意為老人,但“老成人”在《尚書》中多次出現,其所指代的多是當時的賢能有智慧的人,是在治國為政方面有才華或有賢德的人。結合孔穎達將“羞”釋為“進”,即各階層的官員要向最高的統治者推薦這些德高望重之人。周公在《酒誥》中的這兩條規定,實際上都是從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來制定的,將酒的用途同國家的政治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禁酒的規定:
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10]
周公要堅決予以懲罰的是不符合禮的飲酒情況,即“群飲”,懲處的手段是強硬的“予其殺”。偽孔傳釋“群飲”為民眾群聚飲酒,這是值得商榷的。周公在論述殷紂之罪時說“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天,誕惟民怨”,所以,“群飲”其實指的是飲酒過度、威儀盡失的情況,殷鑒不遠,故周公對于這種飲酒無度的行為是堅決予以禁止的,甚至不惜采用最嚴厲的刑罰手段。
周公在對待殷朝遺民的時候顯示出了大政治家的智慧,“姑惟教之,有斯明享”,是在對待以酒犯禁的殷朝遺民時予以包容和教育,孔穎達正義認為殷朝遺民“漸染惡俗,,眾官化紂日久,乃沉湎于酒”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公這樣做實際上是一種籠絡人心的手段,也是出于統治穩定的需要。
《酒誥》篇作為明文記載的最早的一篇“禁酒令”,是周初的統治者面對建國之初錯綜復雜的形式,吸取殷亡的教訓而制定的政令。它是周初社會狀況和禮樂文化的一個反應,也是政治意識在關系到普通百姓飲食方面的直接體現。
從社會層面來說,周初尚處于農業社會的低級階段,生產力十分落后,酒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因此周公作《酒誥》所面對的對象是王公大臣,是當時處于統治階層的貴族群體;作為后起而奪得天下的新興族群,周人對于殷紂王因酒亡國的事情認識非常深刻,認為過度飲酒導致的朝政混亂朝綱廢弛,是統治迅速衰朽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文化層面來說,周公制禮作樂,將國家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都納入到禮的體系之中,對民眾飲酒行為和社會酒事活動予以嚴格控制管理,把飲酒行為納入到“禮”的倫理道德范疇,通過酒禮政教活動強化這種意識,為歷代專制王朝實施“酒禁”提供了圣賢的歷史依據;周公用政治意識形態觀念去審視酒事活動,把飲酒行為與國家治亂現象相聯系,形成“飲酒亡國”的基本文化觀念,對后世影響深遠。
“禁酒”現象不僅存在于統治者與民間的關系之中,從“酒與國家政權”的關系出發,在中國傳統政治結構中,臣子對于君主也多有關于實行“禁酒”的諫言。《晏子春秋》中記載了數則晏子諫戒景公飲酒的篇目,如: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愿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群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11]
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樂以妨事,女不群樂以妨功。男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愿君節之也!”[12]
晏子直言以諫景公飲酒的故事,是臣子對君王提出的規勸,目的在于諫戒景公荒縱無度的生活,避免引起統治的動搖。不同于《酒誥》的自上而下,這是自下而上的諫議。核心在于第一則以“禮”的規范來勸誡景公;第二則是在要求景公飲酒以度,并以桀紂亡國的歷史教訓為證。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晏子以“禮”來諫止齊景公的荒飲,他說“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晏子的重禮思想既是禮樂文化的產物,也是齊國社會形勢的結果,他把禮視為扭轉齊國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勢的強大武器,因此他賦予了禮極高的地位。晏子試圖恢復禮的約束力的嘗試,從《晏子春秋》的記載來看,效果也僅限于一時,否則晏子也不至于再三進諫,晏子的努力最終仍被歷史滾滾而前的車輪碾過。
西周初到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的分裂與征伐,思想的解放與控制,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這一綿長的歷史時期的特征。這些變革在社會生活中留下鮮明的烙印,“禁酒”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也隨著時代而有不同的成因與內涵。
一,從生產力的層面來說,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糧食是影響政權穩定的重要因素。先秦時期,生產力欠發達,農業產量本就不高,釀酒的技術也不夠精約,兩相結合,釀酒往往會耗費大量的糧食。因此,“禁酒”的推行是有其客觀的生產力的原因的。
二,西周初到春秋戰國“禁酒”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推行“禁酒”的統治者將“酒”同政治意識相關聯,認為酒會導致亡國或招來災禍。“飲酒亡國”,將飲酒行為同國家的政治命運聯系起來,也就為從國家層面上予以立法禁酒提供了依據。
三,周公頒《酒誥》,既誥之以酒禮與酒德,又采用刑殺的政策來約束飲酒行為;晏子試圖在禮樂崩壞的時候恢復禮對景公的約束力。“禁酒”現象是禮文化與法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
四,西周初至春秋戰國,不同時期都有“禁酒”現象,而實際的施行結果是并未完全徹底地做到禁酒。酒文化就在“禁”與“弛”的政策中發展起來,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3、結語
酒文化是豐富多彩的,“禁酒”現象是其中頗具特色的一個方面,本文通過簡短的分析,略窺其豐富的社會與文化底蘊。由于水平有限,在很多方面淺嘗輒止,希望本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各家對“禁酒”現象做一個系統的研究與有益的探索。
注釋:
[1][漢]劉向編:《戰國策》,卷二十三,《魏策》二,濟南:齊魯書社,2005,第266頁.
[2][漢]劉向撰,劉曉東校點:《列女傳》,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72頁.
[3][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05頁.
[4][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49頁.
[5][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1頁.
[6][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2頁.
[7][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3頁.
[8][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4頁.
[9][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4頁.
[10][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61頁.
[11][春秋]晏嬰(撰):《晏子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2頁.
[12][春秋]晏嬰(撰):《晏子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2—3頁.
參考文獻:
[1][春秋]晏嬰(撰):《晏子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5.
[2][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3][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 尚書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漢]劉向編:《戰國策》,卷二十三,《魏策》二,濟南:齊魯書社,2005.
[5][漢]劉向撰,劉曉東校點:《列女傳》,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6]黃修明. 《尚書·酒誥》與儒家酒德文化[J]. 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