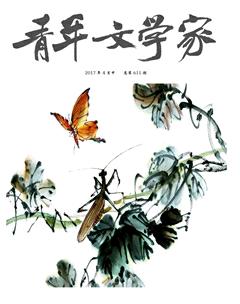一曲“強者之世”中的人道主義挽歌
摘 要:德富蘆花通過《黑潮》中東三郎和喜多川貞子兩個性格、地位迥異人物的悲劇,揭露、抨擊了日本處于國力上升的明治時代的殘酷,以其人道主義情懷映照了當時的日本社會,唱出了一曲“強者之世”的人道主義挽歌。
關鍵詞:明治政府;德川時代;人道主義
作者簡介:王葉方(1976.1-),女,江蘇省宜興人,江蘇省無錫市無錫職業技術學院科技英語講師。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1-0-02
今人論及日本文學,均以明治時期為日本近現代文學之權輿,并以紅露逍鷗(尾崎紅葉、幸田露伴、坪內逍遙、森鷗外)為宗主。自1885年坪內氏發表《小說神髓》倡導寫實主義起,日本文學便走上了近現代之路。這一時期的文藝,對其后的大正、昭和文學起到了辟蕪除萊的作用。之后的文藝里,無論是耽美派的谷崎潤一郎,還是自然主義派的島崎藤村,抑或是新感覺派的川端康成,甚至是無產階級文學奠基人小林多喜二,他們的作品中都可以覓到那個時代文學的影子。然而,正如陳子昂雖然一洗六朝綺靡詩風卻沒能真正開創唐風一樣,以坪內氏為代表的寫實主義派也僅為明治文學趟出了新路。直至19世紀末大量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大量被介紹到日本,日本寫實主義文學才真正成為一股自覺的文化運動,德富蘆花及其《黑潮》就是其中的名篇之一。細味這部長篇小說,不僅可以了解明治后期日本處于“盛世”階段的社會現實與矛盾,甚至對認識今天的日本民族的心態也是很有裨益的。
作為一部小說,《黑潮》的故事情節其實很簡單,主要講德川幕府的舊武士東三郎在明治政府建立二十年后,為了治療眼疾和考察自己從報紙和別人口中聽到的政府的腐敗情形,應故友檜山男爵之邀,從甲州鄉間來到東京,在鹿鳴館與派閥勢力代表、內閣總理大臣藤澤茂光伯爵和一眾大臣舌戰,尖銳地揭露、批判了當時明治政府的專橫暴虐,卻最終在敵人的嘲笑聲中敗下陣來,回到鄉間孤獨地死去。小說中還穿插了另一條線索,描寫了喜多川賢道伯爵的妻子貞子受盡喜多川的折磨,最終含恨自盡的故事。
黑潮本是一個自然地理上的名詞,指沿日本列島由南向北流動的一股暖流,德富氏創作這部小說的本意在初版扉頁上已經寫明,就是:“正如黑潮的熱流著我們的海洋一樣,讓人道主義的潮流也來清洗我們的國家。”他還把寫給其兄德富蘇峰的信作為小說的代序:“是以強健如兄者必然同情強力,孱弱如弟者必然同情弱者矣”,“兄重視國力之膨脹,走帝國主義道路;而弟則愿承雨果、托爾斯泰、左拉諸先生之教誨,執人道主義之大義,因循自己之社會主義。”
從作者的自述看,頗有“哀民生之多艱”的意味。所以在小說中,德富氏借東三郎之口,對明治政府作了在當時可謂最強烈的抨擊:“你們這些靠著國庫里的錢生活的人,也許真的會認為這些農民難道每年只有五塊錢都拿不出來嗎?可是,對于鄉下的農民來說,五塊錢卻和一條生命一樣寶貴哩。”“你們上欺君、下欺民;可是,人民是不可能永久地被欺騙下去的。”“明治政府是亡國政府。”
然而,囿于自身的認識,德富氏針對這種現象,也提不出療救的方法,作為作者的利刃,東三郎僅是站在舊時代立場上針砭當時的社會的,可是,即使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德川統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緒。然而,也正是因為這個角度,東三郎已經脫離了傳統意義上的“遺老”的概念,真正樹立了一個人道主義形象,這或許與德富氏出生時已經是德川氏敗亡后的明治時代的1868年,沒有親身經歷過江戶幕府時代有關罷。
筆者之所以把小說中主人公的抗爭視為“挽歌”,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作者通過東三郎表達的思想確實已經與時代脫節。東三郎在舌戰群臣時,時常表露出對德川政權的懷舊,這就注定了無論他的話語是多么尖銳激憤,也終歸是軟弱無力的。就像同情他的朋友檜山男爵說的那樣:“今天的地租是二分五厘,但從前幾乎是五公五民;從前的武士殺了人可以不問罪,今天卻是四民一律平等……今天只要是有能力隨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大政治家、大學者,或是大財主;對一般人民的情況來說,到底是哪一個時代好,哪一個時代幸福,恐怕用不到比較就可以知道了吧!”對此,東三郎也只以“這是時勢所趨,自然的賜物”這樣虛弱的話來無力地回擊。其實,在他心里,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時代是比舊時代進步的。然而,他的心依然為新時代華麗外貌下呻吟的群氓感到悲憫。二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強者之世”。面對東三郎的攻擊,藤澤只是得意地告訴他:“世界上的勝負就靠實力”,“像東兄這樣的時勢落伍者卻是不行的了,對不起,你就只能站在我們的下風。”“你要搞我的話,就搞起來吧!甚至像剛才南條兄說的,來個造反也可以!”就連主管教育的原子爵也當面對他說:“像這樣子的私塾(東三郎所開),有一百個封一百個,有一萬個封一萬個,一家都不能讓他開下去。”
雖然如此,這部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價值,主要就是作者在當時日本國力處于上升期,不斷取得勝利的時代,用一顆“人的心”關注到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普羅大眾。雖然沒能提出療救那個社會的良方,但這種悲憫本身就是一個時代的良心所在!這一點,從作品中兩個悲劇人物東三郎和貞子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從性格上講,東三郎剛烈如火,貞子作為舊時公卿家的小姐性格嫻靜如水,東三郎似乎是強者;從地位上講,東三郎是幕府舊臣,蟄居鄉野艱苦度日,貞子本人是皇太后的女侍,丈夫也是維新從龍之臣,是時代的新貴,但兩個人卻被同一個時代摧殘。作者通過他們的境遇,深刻揭示了明治時代“盛世”下的殘酷面目。
小說中還有一個細節,書中所有人物都有名有姓,只有主人公就叫“東三郎”,沒有交待他的姓。日本古代除貴族、武士之外,百姓、商人等都是沒有姓的。但東三郎是武士,應該是有姓的,而且明治政府于1875年頒布了《苗字必稱令》,要求每人都要有自己的姓氏。特意不說東三郎的姓氏,是否是作者在暗示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呢?
作為一個注解,小說設置的背景是明治維新后二十年,即1887年,當時日本國力迅速上升,七年后中日發生了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小說創作的時間是1902年,出版于1903年,翌年就發生了日俄戰爭,俄國戰敗。從此,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二戰結束前,作者盼望的清洗日本的人道主義暖流始終沒有出現。
參考文獻:
[1]何乃英,《日本當代文學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06.
[2]德富蘆花,《德富蘆花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12.
[3]瀨沼,茂樹,《明治文學研究》,法政大學出版社,19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