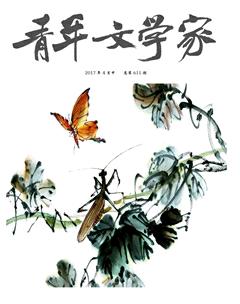戰爭電影中的女性話語權
李雅昕
摘 要:戰爭是政治較量的突出表現。戰爭的話語權似乎自古以來就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對于戰爭大多是被動地接受,但是也有一部分女性敢于直面政治,直面戰場。本文將戰爭中的女性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完全被動的女性,第二類是以戰士身份介入戰爭的女性,第三類是用身體表達話語的女性。最后得出結論,女性獲得政治話語權,必然以犧牲某種利益為代價。
關鍵詞:女性;戰爭;話語權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1--02
一、引言
在“戰爭”這一崇尚武力的特殊背景下,男性幾乎占據了歷史的整片天空,他們的陽剛之勇在戰爭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詮釋,而女性似乎就只能作為和領土、財富一樣的戰利品被爭奪,她們對戰爭的看法,對政治的態度,無人問津,甚至連表達自己都成了奢望。就像三十年代的蕭軍和蕭紅,以強者和英雄主義人物做自我要求的蕭軍必然占據更多的意識形態優勢和社會優勢,而蕭紅對溫柔與愛的需要則不受社會環境的袒護。
二、戰爭中女性政治話語的表達。
那么女性究竟能否在戰爭中表達自我?如果要表達該以什么樣的性別?什么樣的方式?本文認為戰爭中的女性或許有這樣三條出路。第一、心理上遠離戰爭,面對巨大的孤獨,“悄悄地活著”、“悄悄地死去”,被動地承受戰爭帶來的苦難;第二、背叛傳統角色,抹殺性別,以女戰士的形象參與戰斗,表明立場;第三、利用性別,主動犧牲肉體,來維護自己的政治話語權。下面將分別舉例論述這三類女性。
(一)《南京!南京!》——沉默的羔羊
《南京!南京!》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講述日本侵略中國,殘害中國人民的慘痛歷史。影片從1937年12月,南京淪陷開始,國民黨的部隊無力抵抗日軍的進攻,大批國民黨士兵逃出南京,但仍有部分愛國將士誓死抵抗,最終失敗。接著就是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數十萬中國人慘遭殺害,南京淪為一座死城。眾多女子被日本人霸占為慰安婦,甚至被蹂躪致死,無論老少。她們面對戰爭只有恐慌和無助,只能被動承受災難,她們連自己的生命和尊嚴都無力維護,就更談不上參與政治。唐先生的妻子和小妹還正在避難所里興致勃勃地玩麻將,突然聽到槍聲,才意識到危險降臨。戰爭打破了本該屬于她們的美麗和寧靜,她們像物品一樣被掠奪,被欺侮,再被任意地拋棄(影片中的一個鏡頭——被折磨死去的慰安婦都赤身裸體地扔出來,像牲口般地交叉層疊被扔上車)。戰場上的勝敗和女人是無關的,即使勝利方的女性還是要遭受男性的欺侮。在日本軍士的價值觀中,任何國籍的女性對于他們的意義都是欲望的發泄對象。對此導演陸川表示這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當時有很多日本婦女自愿隨軍,日本用一種口號式的東西欺騙了一批日本婦女,來自愿慰藉參戰士兵,她們每天也要接待100—200名士兵,下場命運都很殘酷。”男性尚可奔赴戰場,為國效力,死得其所,雖死猶榮;而女性卻無法為自己辯白、申訴,她們只能逆來順受,將自己的生命化進沉默的悲哀。關于政治,關于戰爭,她們不僅沒有表達的權利,甚至也沒有表達的意愿。
(二)《全金屬外殼》——褪去本色的鋼鐵之軀
從1927年北伐戰爭開始,中國就陸續出現了一些女兵、女戰士,她們使女人的形象第一次與槍炮、與力量,與流血犧牲的戰場生活聯系起來。她們“首先找到的似乎是一種最大限度地背叛傳統角色的可能性:背叛‘女性之軀,至少,背叛歷史給女人之軀規定的傳統功能。……女性第一次參與對歷史的抉擇,她第一次有了一個巨大的事業,女人的生命因著這為百姓為中國富強的事業而有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意義。……她們為了反抗傳統角色還不得不忘記性別,還不得不以男性作為衡量自己能力的標準。”(孟悅 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
女性要成為革命者,要介入戰爭,要有自己的歷史話語權,就必須摒棄女性身份,舍棄性別,像男人一樣奔赴戰場,血雨腥風,用陽剛的力量的標準來證明自己。她們很難找到一種恰當的,帶有女性特征的方式介入戰爭。也就是說她們要反抗的不僅是封建社會對于女性的角色規定,甚至要反抗自己的性別。“紅的女人應該把自己是女人這回事忘掉,否則會干擾革命進展的。”女作家馮鏗筆下的馬英如是說。“十七年”是我國長篇小說創作出版的高峰期,大部分描寫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其中不乏展現女性從家庭婦女走向革命戰士歷程的作品。如楊沫的《青春之歌》,敘述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林道靜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女性的優柔寡斷,最終成為一名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曲折過程。
《全金屬外殼》是斯坦利· 庫布里克根據古斯塔夫·哈斯福特小說《短期服役》改編,一部反戰影片,也是一部描寫越戰的杰作。越戰期間,一批年輕人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來到魔鬼新兵訓練營,任何一位想要加入戰斗的年輕人,必須接受生理的嚴酷訓練,和心理的殘酷羞辱,以至于最終被訓練成一個沒有情感,以殺人為樂趣的機器。派爾是個憨厚老實的小伙子,不堪忍受非人的訓練,就在出發前往越戰戰場的那晚,傻瓜派爾在他的M14裝滿“全金屬外殼子彈”(Full Metal Jacket),一槍打死軍士長,接著自己也含槍自殺。
選擇編入新聞組的小丑,被長官派去前線采訪,他隨眾巡視,誤入未掃蕩的地區,結果遭到埋伏的狙擊手攻擊,犧牲了好幾位同伴。僵持很久,小丑終于找到狙擊手,發現竟然只有一個人,而且是位非常年輕的越南少女!她全副武裝,手持狙擊槍,眼里閃著勇敢無畏的光芒,她為了挽救民族而走向戰場,如果沒有俊俏的面龐,我們很難想象她是個女性。美國士兵立即制服了她,少女在地上痛苦的掙扎,哀求“殺了我”,小丑不忍地拿起槍,扣下扳機。這位年輕的越南女性及其精準的槍法,勇敢的精神,頑強的意志,已經絲毫看不到女性的溫柔,完全和一個優秀的男性士兵別無二致。當然這部影片不單純表現女性性別的泯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也表現了戰爭對人性的摧殘與毀滅。
走向戰場的女性,首先是個女性,其次才是革命者,可是經歷了槍林彈雨、流血犧牲的戰爭,她們是否還能找到自我,她們該如何定位自我?
(三)《金陵十三釵》——用身體說話
《金陵十三釵》是根據嚴歌苓同名小說改編,2011年張藝謀執導的戰爭史詩電影。講述1937年被日軍侵占的南京,在一座基督教堂里躲避著一群女學生、14個風塵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軍人和傷兵,一個充滿人道主義的美國人約翰,裝扮成神父,保護著整座教堂。然而尊重信仰對日本侵略者來說不過是一種虛偽的表演,這里的平靜并不長久。日本人要在中國的領土上舉行慶功會,強征女學生去慶功會為日軍表演節目,然而喪失人性的日軍怎么可能僅僅滿足于表演?女學生們不甘被日軍凌辱,準備集體自殺。一起避難的風塵女子們,盡管平日為女學生所不齒,但在關鍵時刻,她們勇敢地站出來,為了民族大義,為了保護祖國的下一代,主動代替女學生獻唱慶功宴,赴一場悲壯的死亡之約。十三釵和本文第一類女性一樣犧牲了自己的身體,但她們的犧牲不只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主動地承擔;她們的犧牲保護了有知識有希望的年青一代,保護了祖國的未來。她們以犧牲身體為方式為籌碼、為代價來捍衛自我的政治話語權。所以,她們的犧牲不單純是悲慘,令人同情;更多的是悲壯,令人敬佩,有一種大而無畏的陽剛之美——影片將近結束時,十三釵在戰火硝煙背景下,唱出一首柔婉的《秦淮景》,戰爭的殘酷與女子們柔美的歌聲形成強烈對比,展現出一種悲壯美。但這究竟是辛酸而屈辱的。從《浮出歷史地表》這本書關于女性與戰爭的關系,似乎可以得出一種結論——走向戰場的女作家們,她們留給后人最有價值的東西并不是革命的作品,而是她們在戰爭背景下的個人命運,謝冰瑩如此,馮鏗也是如此,她們自己身上承載著歷史的真實,她們在冰冷現實與熱烈理想中的掙扎似乎也在說明一個問題,女性想要獲得政治話語權的唯一出路便是各種形式的犧牲。
結語:
電影、文學和生活,三者存在著演繹和升華的關系,但是前兩者都來源于生活。電影中的女性話語權問題,也就是生活中、歷史中的女性話語權問題。自古以來,戰爭似乎只是男人的事情,女人既無權干涉也無心過問,只能被動地承受戰爭所帶來的各種災難。五四開始,女性從要求解放自我,擺脫男權的壓制;到要求參與政治,在政權的領地上占有一角,不得不說是個進步。但是當代女性參與政治,爭取話語權,似乎依然是以某種犧牲為代價。女性何時才能在政治上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對話權?何時才能不以犧牲其他利益來換取政治利益?何時才能真正占得歷史的半邊天?這恐怕還需很長時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