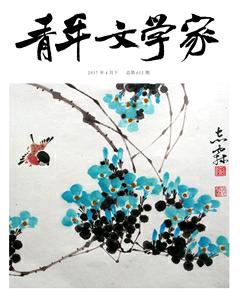庫切《內陸深處》的狂歡化色彩
摘 要:本文是運用巴赫金的狂歡理論解讀庫切的作品《內陸深處》,該作品顛覆了傳統的敘事模式和審美理想,通過怪誕的人物形象、粗野與優雅交織的敘事語言、顛倒錯置的時空秩序等具有狂歡化色彩的書寫展現了庫切對南非殖民歷史的反思和解剖。
關鍵詞:庫切;巴赫金;狂歡化;殖民
作者簡介:黃永文,湖南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2-0-03
巴赫金的狂歡化詩學理論是建構在歐洲古老的狂歡節文化基礎之上的。狂歡節文化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個世界和第二種生活,人們在這個世界中可以反叛權威、對抗等級,自由的對話與諧謔。而文學的狂歡化來源于狂歡化的生活感受和對狂歡節生活的真實再現,例如拉伯雷的《巨人傳》、塞萬提斯的《唐吉坷德》、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都直接展現了狂歡節生活的某些方面。這些小說中充滿了對神圣經典的諷刺模擬,對宗教儀式的滑稽演繹,對崇高形象的揶揄、挖苦、顛覆等。文明的逐漸發展,狂歡節在人們的生活中逐漸的邊緣化甚至慢慢消失,文學作品中的狂歡化色彩就主要體現在狂歡化的世界觀和思想方式上了。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樣:文學的狂歡化既然是由狂歡節生活的符號化和語言化而來,那么文學作品的狂歡化也就離不開狂歡節的種種儀式、結構、形象、語言、時空體等因素的滲透和影響。
庫切本人很推崇巴赫金的理論,在自己的文論中反復提到過巴赫金。在《陌生的海岸》這本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一書的。在該論文中,有一個章節專門介紹了巴赫金的復調理論。他認為“復調小說”的理論是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的作品時提出的一種文本分析理論,認為對話概念的優勢在于“沒有主導的、中心權威的意識,因此不會有任何一方聲稱是真理或權威,有的只是爭論的聲音和對話”[1]。同時,庫切在自己的小說創作中也融入了巴赫金的復調和狂歡化理論,他的小說中的人物經常在異于現實生活的“第二世界”中活動,人物大都有著相互矛盾的雙重人格。在想象的自由世界里,他們沒有任何束縛的對話,處于弱勢卻敢挑戰權威,《內陸深處》就是典型的代表。小說的基本情節是:從小失去母親的女主人公瑪格達與父親在一個農莊里生活,她與父親的相處并不愉快,而他的父親與農莊奴仆妻子的偷歡更加忽略了她的存在,瑪格達于是將父親殺死。小說的另一個線索是瑪格達與黑人男仆的復雜關系,體現了南非種族隔離時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緊張關系,以及殖民者在殖民過程結束后的孤獨和脆弱。整部小說運用第一人稱,通過266個小段落敘述瑪格達內心深處的意識,事實與幻想的交錯,大段大段的人物與自我對話的狂歡,混亂的邏輯和雜糅的語言讓這部小說風格具有濃厚的狂歡化色彩。
一、怪誕的人物形象
“狂歡生活是一種邊緣生活,狂歡生活中的人也是一種邊緣人。”[2]《內陸深處》的主要人物形象就是這種狂歡化的邊緣人物,瑪格達是一個具有雙重人格的形象。雖然是白人的后代,但她身世凄涼,性格孤僻,相貌丑陋,沒有任何人關心她,理解她,每天在陰暗的房間里自由的遐想。在幻想中她什么都做得出來,可以自由的發泄,去實現自己的欲望,成為自身的主宰。為了反抗父親的壓迫,她可以拿起斧頭砍殺父親和他的情人,拿起長桿搶射殺父親,看著血水汩汩而涌,想象著是讓尸體沉入水里還是埋在河床上;在幻想中她要實現自己的情欲,和別的女性一樣擁有男性的愛,“我將發愿對這樣一個人卑躬屈膝,也會比別的女人更低聲下氣,更賣力地為他做奴隸,對這樣一個人,我將每個星期六晚上為他寬衣解帶,在黑暗中行事免得嚇了她,要設法喚起他的情欲——”[3]而在現實生活中,她又盡心盡力的服侍父親,回到自己的房間寫商籟體詩,自己與自己對話,生活在自己臆想的恐怖氛圍中,每天都過著黯淡無光的日子,忍受著孤獨的折磨。
瑪格達的雙重性源于她的極度孤獨以及欲望得不到滿足,所以常年處于不正常的瘋癲狀態,思想游移不定,行為荒誕滑稽。雖身處困境,但她的內心世界充滿了對人生存在意義的思索和強烈生命的激情。這種復雜而矛盾,自由又瘋狂的精神狀態,充分體現了巴赫金所認為的交替更新的狂歡精神,“狂歡式世界感受的核心,是交替和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摧毀一切與更新一切的精神”[4]。瑪格達狂歡精神的高潮是她的弒父行為的發生,這是對社會秩序的反抗,以狂歡的姿態挑戰一切正統、嚴肅、官方的權威。父親對她的冷漠、忽視、專制讓她感到痛苦,殺死父親后她覺得自己能得到自由和解放。如果說,瑪格達的狂歡呈現為對自由生命欲望近乎迷狂與夢魘的追求,那么,小說中的另外一個人物形象——黑人亨德里克的狂歡則體現為復仇的快意。男主人在世時,他畢恭畢敬,任勞任怨,甚至忍受著主人對自己老婆的占有,在男主人死后,他完全換了一種姿態,穿上主人的服裝、帶著主人的帽子,兩手搭著臀部,敞著懷,在城墻上炫耀,甚至對女主人實施報復性強奸。這種場景的描寫,充滿了拉伯雷式的諷刺、挖苦、惡搞,巴赫金把這看作是在象征層面對國王的脫冕與罷黜,也是對權威和對壓迫的推翻。在后殖民時期,社會權力關系已經改變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顛倒過來了,曾經受壓迫的人變成了壓迫者,通過這種狂歡式的復仇,庫切深刻地揭示了南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復雜關系。
二、語言的狂歡化
在狂歡節的文化廣場上,充斥著粗俗不堪的臟話、下流語言,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可以肆無忌憚地狂笑戲謔,嬉笑怒罵,沒有任何界線。狂歡化的語言以狂歡節的廣場語言為范本,其特質在于其宣泄性、不加節制性,以及嚴肅與詼諧、神圣與卑俗、肯定與否定的混合。《內陸深處》的語言打破了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語言禁忌,以一種毫無顧忌的、眼花繚亂的、粗野與高雅交織的方式表達了主人公的真實的內心世界。
首先是作品中充斥著各種看似低俗的、骯臟的、咒罵式語言。瑪格達的內心獨白是綿綿不絕的怨恨、歹毒和惡言惡語,一切神圣的語言頃刻間下沉到身體下部,即肚子、身體器官和排泄系統。在瑪格達的父親中槍后,他沒有馬上死去,而是與蒼蠅、糞便、血污、惡臭在房間里呆了好幾天,作者以及其興奮又戲謔的筆調描述了蒼蠅在房間里的飛舞:“那些蒼蠅,該是沉浸在喜不自禁的歡樂之中,只聽那動靜就知道是在交歡。對它們來說,似乎沒有什么比這更美妙的了。它們兜了幾英里路,放棄了食草動物粗劣的糞便,像離弦之箭一般飛赴這個血污的盛宴。”[5]粗鄙的語言嵌套在優雅的文辭間形成了一種敘述張力,具有一種別樣的美。最能代表文學話語沖破本身所固有的邏輯和規則的是對父女倆大便的描述:
“每隔六天,在無花果樹后面的便桶里,我們會在對方屙屎后滿是惡臭的氣味中去把腸子里的糞便排泄出來,要么他在我的惡臭中,要么我在他的惡臭中,我們的周期六天一碰頭,他是兩天一次,我是三天一次。掀開木質馬桶蓋,我蹲跨在他那堆可惡的稀里嘩啦下來的東西上面(那些帶血污的要命的玩意兒倒是飛蠅的最愛),再覆上斑駁的色澤,我敢肯定,那些沒消化的肉食幾乎是囫圇地排出來了。”[6]
這種語言表達看起來荒誕滑稽,粗野又骯臟,但在這種描述中,父親的權力和威嚴被貶低化了,高雅和正統被粗俗化了,全都呈現到身體下部的功能中,展現的是生命本身的隨意性,是一種下意識的狂歡。
其次,語言的狂歡化還體現在夸張、戲謔的語言風格上。具體表現為語言節奏加快、紊亂,意象雜混、堆砌、變異,充滿含沙射影,語義極度膨脹,幾乎撐破了正常用詞和句法結構的界限。瑪格達不斷地在想象中與自我對話、又不斷地解剖自己,在她的獨白中暗含著對殖民歷史的憤慨和深深的悲哀。殺死父親后,她和亨德里克一起收拾的場景是小說中少有的明亮的氣氛。“我們真誠的汗水流淌在一起,懷著隱秘的激情。我們就像兩只白蟻。鍥而不舍在于我們堅定不移。我們從屋頂鋸到地面。我們把臥室鏟開。它慢慢升向天際,就像一艘船昂首駛向黑暗中的星辰。”[7]快速的節奏,短小的句子,混亂而富有詩意的邏輯,表達的是對權威顛覆后的短暫的自由、解放和歡慶。瑪格達希望和有色人種安娜做朋友,一起牽手去散步,她們的對話充滿了隱喻:
“告訴我,安娜,你怎么稱呼我?我的名字叫什么?”我盡可能輕柔地呼吸,“你心里是怎么稱呼我的?”
“小姐?”
“這沒錯,可對你來說我只是小姐嗎?我沒有自己的名字嗎?”
“瑪格達小姐?”
……
“不,小姐,我不能。”
……[8]
黑人女性一直都是沉默的,他們沒有自己的聲音,她們不敢叫白人的名字,她們自己認為她們就是奴隸,對白人就得畢恭畢敬。瑪格達總想融入到他們的世界中,但所做的努力總是徒勞,她們不接納她,排斥她,他們各自有各自的世界。在這里,庫切似乎在為沉默的黑人發聲,尋求溝通的可能,這段話暗示了阻隔在他們之間的歷史溝壑是不可能越過去的,他們始終無法理解,無法融合。
最后,作品中的自造新詞使小說充滿了狂歡式的調侃和幽默。在第251節至257節中出現了作者創造的西班牙語,是瑪格達用石頭拼出來的回應天空中“機器里的生物”的語言。“DESERTA MI OFRA—ELECTAS ELEMENTARIAS—DOMINE O SCLAVA—FEMM O FILLA—MASEMPRE HA DESIDER—LA MEDIA ENTRE(拒絕我的給予—最基本的選擇—奴隸和主人—女人或姑娘—但總想要—不偏不倚的)”[9]。譯者文敏曾請教過母語為西班牙語的人,庫切在小說中展示的語言是似是而非的“西班牙語”,是他的自創詞。這種斷斷續續、支離破碎的語詞打破了讀者原有的欣賞習慣,創造出奇特而全新的藝術效果。從這些碎片化的語詞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庫切對自由、正義的向往,渴望人們能夠互相理解和關懷。
三、時空體的顛倒錯置
巴赫金認為“文學中已經藝術地把握了的時間關系和空間相互間的重要聯系,我們將之稱之為時空體。”[10]傳統小說有著連貫的,符合邏輯的情節,按照時間的線性發展去講述故事,所描述的現實和幻想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界線。《內陸深處》在敘事結構上打破傳統小說的敘事格局和結構,讓現實與幻想相互交織,避免了單一敘述視角的片面性,具有顛覆性的狂歡化特征,體現了巴赫金狂歡化的時空體特性。
《內陸深處》的故事情節是通過瑪格達似真似幻、瘋瘋癲癲的邏輯思維描述出來的,各種瑣碎的獨白、臆想、意識流在變幻的時空中上演。首先是現實與幻想轉換無常,作者開篇寫道父親帶著新娘子回家了,對新娘子作了繪聲繪色的細致的描述,隨后瑪格達覺得自己的處境受到威脅而砍殺了他們兩個,砍殺過程的細節以及對尸體如何處理的思考也寫的非常真實,讓讀者以為是真實發生的事情,而到了第36節“畢竟他不會那么輕易地死去”時讀者才會恍然大悟,原來前面都是瑪格達在頭腦中的臆想啊!《內陸深處》主要關注的是瑪格達內心恣意流淌的意識,人物的外部行為僅僅為文本提供了一條相對明晰的線索。這些意識反映出她的無盡的孤獨和脆弱,不斷審視自己又顛覆自己。其次,正是因為瑪格達的瘋癲錯亂的思維,整個故事的過去、現在、將來的時間秩序被隨意的置換。在接下來的故事中,瑪格達講述了自己如何伺候父親,男仆亨德里克把他的新娘帶回家,隨后又開始描述到亨德里克來這里找工作的情形。他的意識跳躍在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現實中,在不同的時空內自由穿梭,展現出意識的廣袤性與虛無感。最后,是對同一件事情的多次描述,但在敘述中又有些許差異。在205、206、207這三小結中都描述了亨德里克對瑪格達的強奸,在206節中寫道:“插著腿把我扯倒了。他的骨盆緊緊貼著我的身子。‘不要!我喊道。‘要的!他在我耳邊一英尺的地方嘀咕道,‘要的!……要的……”[11],在207節中作了同樣的描述,但又有些許的改變,“他插著腿把我壓在地板上,骨盆緊緊地貼著我的身子。‘不要!我喊道。‘要啊!他喊道,‘要啊!……要啊!……”[12]重復描寫一件事體現的是這件事在記憶深處的深刻性和不可磨滅性,以及對這一事件的不可理解,瑪格達幻想異性的愛,幻想自己變成女人,而亨德里克的性虐待讓她感到羞恥和無法理解。在權利關系的變更中,她只能是一個無辜的替罪羊。在小說中,“敘事者”的漂浮不定,敘事視角的不斷轉移,帶來小說時空切割的緊張、變動狀態。同時,理性規則、因果聯系、邏輯關系的消解,創造出一個獨特的時空體,遠離嚴肅正統的官方生活,具有明顯的狂歡化特征。
綜上所述,在 《內陸深處》里,庫切通過對人物形象的降格、對崇高話語的解構、對時空體的顛倒翻轉,完美地體現了巴赫金所說的狂歡化“小說精神”,即“無情的批判精神,清醒和揶揄”。它消除了對所描述對象的敬畏,不斷地拆解、重置、顛覆、診斷,直到顯現出其表層下面的東西。透過庫切狂歡式的敘述方式,我們看到了他對一切權威和規范的反抗姿態,客觀的見證歷史與現實,尋求不同膚色人種之間的理解和關愛。同時,這種顛覆和批判的方式,也為當代小說文體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創作和解讀空間。
參考文獻:
[1]J.M.Coetzee,Strange Shores Essays 1986-1999,London:Vintage,2002,p.144.
[2]王建剛. 狂歡詩學: 巴赫金文學思想研究[M].上海: 學林出版社,2001: 58.
[3]庫切.內陸深處[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63.
[4]夏忠憲.巴赫金狂歡詩學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68.
[5]庫切.內陸深處[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116—117.
[6]庫切.內陸深處[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47.
[7]庫切.內陸深處[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122—123.
[8]庫切.內陸深處[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152—153.
[9]庫切.內陸深處[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198—199.
[10]王建剛. 狂歡詩學: 巴赫金文學思想研究[M].上海: 學林出版社,2001:166—169.
[11]庫切.內陸深處[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156.
[12]庫切.內陸深處[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