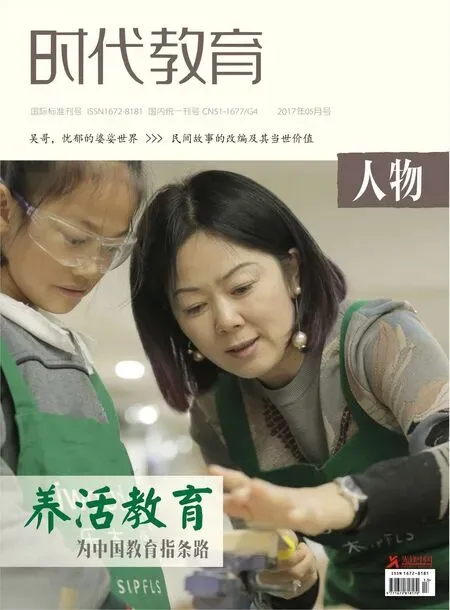“路上行人欲斷魂”是什么意思
文_錢佳楠
“路上行人欲斷魂”是什么意思
文_錢佳楠

錢佳楠,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作家協會會員,著有短篇集《人只會老,不會死》,譯有《粉紅色旅館》,目前就讀于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坊。
有一天,吃完午飯和同事散步回辦公室,或許是聊起清明節有沒有出去,我忽然問他:“‘路上行人欲斷魂’究竟是個什么意思呢?”
這個對話發生在兩個中文系畢業生之間顯得有些諷刺(幸而我們都不是主修古典文學,不然真是丟臉),同事的古文基礎扎實,立馬告訴我傳統注本(其實就是《唐詩鑒賞辭典》)的兩個解釋:“斷魂”意指內心凄苦,第一個解釋是說:清明是舉家踏青掃墓的時節,這個行人卻孤零零地走在路上,又沾上雨水,因而感到惆悵;二是清明節路上的行人因思念過世的先祖而感到悲傷。
他給出這兩個解釋后和我一樣直覺地感到這兩個傳統的腳注是站不住腳的。我們都感到唐代的清明節應當沒有后來那種念及先祖,涕淚沾襟的意思。我的古文基礎不如他,我的感覺是從周作人的散文里來的,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寫道:“清明時節,正是‘踏青’的好時節……不料,在元代異族統治下,這里的人民被視為南宋遺民,貶為最下等的‘南人’,婦女竟被剝奪了‘踏青’的權利,人民借掃墓之名,進行變相踏青,清明節就變成了掃墓節。”不僅如此,杜牧詩里的原話是“清明時節”,而非特指“清明節”,因掃墓而“斷魂”很可能是今人的意會。
再者,如果按照傳統的解釋,詩人的邏輯也未免太“任性”了一點。前面還念及先輩而黯然神傷,一下子就要向牧童借問喝酒助興的去處了。雖然行人孤零零落得要去喝酒解悶似乎勉強還通,但如這樣解釋,后兩句“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就失去了本應有的自在和逍遙。
無論如何,解開疑團的關鍵首先在民俗,于是我們就查,果然早有學者做過研究。有一篇1993年發表在《文學遺產》上的文章很有洞見,作者名叫張慶捷,他給出兩條洞見,第一,清明節和寒食節雖然時間上接近,但習俗迥異,寒食上墓,清明則踏青,兩個節日引起的情致殊乎不同,不可混淆為一。這是其次的結論,同事和我通過搜索各種民俗學的論文都得到這一論斷,有民俗學者補充道,清明時節的這場雨是名副其實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不少地方志有“是日雨主豐年”的記載,更是讓“行人本就孤苦伶仃,加之沾上了雨,內心更感凄苦”的解釋不攻自破,既然是豐收之兆,應當大喜才對,何至于到“斷魂”呢?
張慶捷先生給出的第二條洞見才真正見其本事,他說,“詩中由‘雨紛紛’而引起的‘行人欲斷魂’情緒,既可以體會為悲愁,也不妨說它是歡娛。宋代詩人陸游就有‘遠游無處不銷魂’之句。”他這樣一解釋,這首詩忽然就讀通了,因為一場細雨引起了賞玩的興致,于是任由興致高漲,想去喝酒,很有古人的風貌。
但這畢竟是他的推測,是否真的如此,還須看“斷魂”二字能否作“銷魂”解。我檢索了《全唐詩》,“斷魂”多作內心怛怛之解,但也不是沒有例外,如宋之問的《江亭晚望》:
浩渺浸云根,煙嵐出遠村。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斷魂。縱情猶未已,回馬欲黃昏。
此處的“斷魂”似更近于“銷魂”,是一種陶醉在景色中流連忘返的姿態,那么張慶捷先生的解釋當是通的。
同事和我讀了文章,便好奇此人是誰,結果發現這是一位知名考古學者,歷史學出生,主要的著作都與山西境內的考古發現有關,我疑心是同名同姓。同事比我善于搜索,搜出一條這位先生昔日的同窗對他的評價,說他在大學里讀歷史的時候就對文學頗感興趣,常常在圖書館翻文學書“怡情”。
人家的興趣愛好,讓我們這些科班出生的人無地自容。
而后同事又有發現,源于我們想搜尋唐詩專家對此詩的解讀,結果突然想起《唐詩三百首》竟無此詩,另也發現學界認為此詩系偽作,非杜牧所作,同事覺得兩者或可互相印證,清人應該就考慮到此詩有偽作的嫌疑,故不收入。
午間的游歷最終,因我們的職業習慣使然,我們感慨學科的討論課應當這樣來上,就讓學生們去探索“路上行人欲斷魂”的意思,用個把月的時間,引導他們從各自的路徑去找,每堂課從不同的路徑展示,這句詩本身的意思已經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學生沿著不同路徑尋覓,自然會摸到民俗、考證、小學或其他方面的敲門磚,至少也覺得思索大有意思。前幾日有條新聞:美國四個中學生做一份題為“尋找身邊的歷史英雄”的課后作業,結果發現了一位“女版辛德勒”,大家都在感慨這位女性的善良和偉大,而我在感嘆這份有趣的歷史作業。
這當然是理想的課堂了,也算是吃飽飯瞎想。
P.S.朋友在重讀《宋詩選注》,按照錢鐘書先生的注解,宋代清明時節依然是踏青習俗占據上風。《清明》這首詩最早和杜牧聯系在一起是在南宋末年的本子里,如果南宋依舊踏青習俗占上風(如果周作人說的元代才發生以掃墓為名實則踏青的變異),那么張慶捷先生的解釋應當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