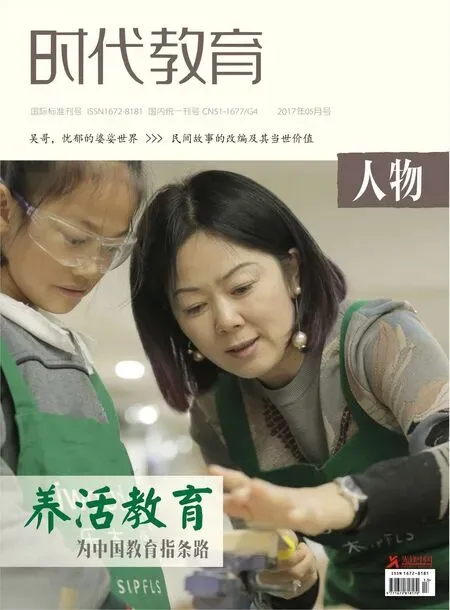古人為什么“折柳相送”?
■萬(wàn)物啟蒙學(xué)堂
古人為什么“折柳相送”?
“折柳送別”暗藏著一條“借物起興”形成意象的隱秘邏輯:藉由對(duì)自然萬(wàn)物的體認(rèn),到器物的生活傳承,靠歲月堆積成漢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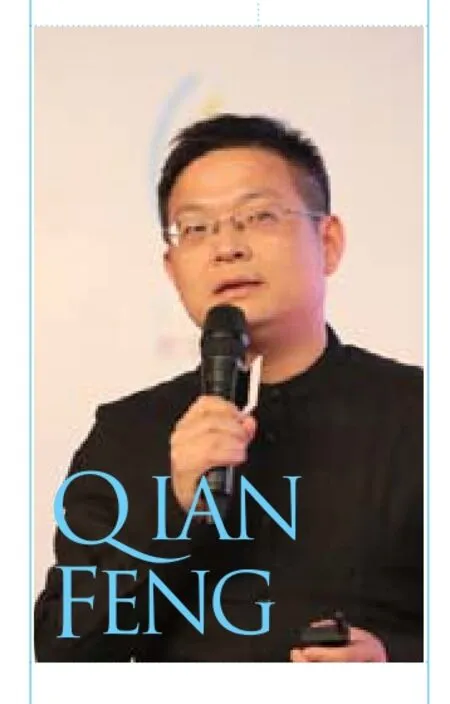
錢(qián)鋒:上海協(xié)和教育集團(tuán)課程研究院院長(zhǎng)。專注于兒童通識(shí)教育。“萬(wàn)物啟蒙”教育創(chuàng)始人,中國(guó)萬(wàn)物地圖公益計(jì)劃發(fā)起人。全人教育獎(jiǎng)提名獲得者,多家刊物封面人物,著有《重讀經(jīng)典課文》《萬(wàn)物啟蒙課程系列讀本》。
“折柳相送”是中國(guó)古代一個(gè)著名的送別習(xí)俗。人們?yōu)槭裁雌x擇了“柳”,而不是其他植物呢?
民間習(xí)俗與文學(xué)傳統(tǒng)關(guān)聯(lián)緊密。潘富俊先生在《草木緣情》一書(shū)中對(duì)“柳”出現(xiàn)在古代詩(shī)詞中的頻率做過(guò)統(tǒng)計(jì)。僅《全唐詩(shī)》就出現(xiàn)了3463次。回溯經(jīng)典詩(shī)文,“柳”是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文學(xué)意象。
說(shuō)起“柳”的詩(shī)詞,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這一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lái)思,雨雪霏霏。
詩(shī)句中的“楊柳”是指“柳”的通稱?還是“楊”和“柳”兩種植物呢?金文中的“楊”是這樣的:
顯然,這和“陽(yáng)”關(guān)系密切,意味著這是一棵朝向陽(yáng)光生長(zhǎng)的樹(shù),北方常見(jiàn)的落葉喬木,多數(shù)分布在長(zhǎng)江以北地區(qū)。挺拔高大,沒(méi)有下垂的樹(shù)枝,葉片寬大,北方稱為“鬼拍手”。那么,柳呢?這可真是植物界的勞模,隨栽隨活,高溫不怕,鹽堿不怕,旱地不怕,濕地不怕,所以,柳是全中國(guó)分布最廣的植物,遍布大江南北。
正是柳樹(shù)這種不拘環(huán)境,隨處生長(zhǎng)的特性,作為古人贈(zèng)別好友的信物,再合適不過(guò)了。我們都希望親朋好友遠(yuǎn)離家鄉(xiāng),能夠適應(yīng)環(huán)境,隨處生長(zhǎng),落地生根,枝繁葉茂。折一根故鄉(xiāng)柳,在異鄉(xiāng)的土地上一插,澆點(diǎn)水,便能撐起小小的綠蔭,隨處可見(jiàn)一片鄉(xiāng)情綠意。
清明前后,正是東風(fēng)徐來(lái),細(xì)柳抽芽的陽(yáng)春。所以,除了扦插,民間還延伸出“清明插柳”的習(xí)俗。插在哪兒呢?有插少女頭上的。“清明一霎又今朝,聞得沿街賣(mài)柳條。相約比鄰諸姊妹,一枝斜插綠云嬌。(清,楊韞華《山塘棹歌·插柳枝》)
清明是祭祖的節(jié)日,也是三大鬼節(jié)之一。“清明不戴柳,紅顏?zhàn)凁┦住!贝笕瞬幌M⒆邮苄八钋謹(jǐn)_。還有插在門(mén)上、屋檐上、井水邊的。《齊民要術(shù)》講:“正月旦取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井井有條”這個(gè)成語(yǔ)即來(lái)源于此習(xí)俗。可見(jiàn),柳成了民間百姓護(hù)佑平安的植物。
柳是不是真這么靈驗(yàn),自是民間的信仰,但是現(xiàn)代醫(yī)學(xué)也確實(shí)從柳樹(shù)中提取到了一種成分,專門(mén)用于清熱鎮(zhèn)痛,這就是著名的阿司匹林,倒也佐證了《本草綱目》關(guān)于柳的各部位皆可入藥的記錄。
如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折柳相送”首先和“柳”植物本身有密切關(guān)系。清代褚人獲曾在《堅(jiān)瓠廣集》提出這樣的疑問(wèn):“送行之人豈無(wú)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xiāng)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為之祝愿耳。”折柳送行,亦包含著為離別者祈福康泰的美好祝愿。
現(xiàn)在,回過(guò)頭我們可以看看“柳”這個(gè)字的金文了:

這個(gè)字從木從卯。如果再往前追溯柳字,卯在木的下方,意指一扇木門(mén)。說(shuō)起“卯”,我們會(huì)想到“榫卯”。在沒(méi)有鐵釘螺栓的古代,這種包含著中國(guó)人民古老智慧的建筑部件連接結(jié)構(gòu)叫做“榫卯”。無(wú)需五金件或膠水,通過(guò)各種嵌套結(jié)構(gòu)就可以把木制零件牢牢固定在一起。這是一種有溫度的聯(lián)結(jié)方式。中國(guó)古人善治木,家門(mén)口最常見(jiàn)的木材之一就是柳樹(shù)。很多人認(rèn)為柳木疏松,不宜做家具。柳樹(shù)種類繁多,有一些柳木結(jié)實(shí)、耐用、不易變形,且紋路清晰,制作家具既實(shí)用又美觀,尤其一些生活小器物。砍伐柳樹(shù),一般不大會(huì)連根拔起,而采用“頭木作業(yè)”。就是當(dāng)柳樹(shù)長(zhǎng)到一定高度的時(shí)候,把它的上半部分截掉用以做家具材料。截掉以后新枝就能從旁邊開(kāi)始抽芽,形態(tài)更加美麗,柳枝也越來(lái)越茂盛。所以這個(gè)“留”,就是留住下面的樹(shù)干,把根留住。這也許柳與“留”相關(guān)聯(lián)的真正原因。
正是這種不需要任何介質(zhì)就能緊密連接的結(jié)構(gòu),體現(xiàn)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至深情誼。無(wú)論此行一別,相隔多久,我們的關(guān)系是不會(huì)改變的。他日天涯再相逢,兩人依舊可以把酒言歡論英雄。
“卯”還會(huì)讓我們想到“卯時(shí)”。這是中國(guó)古代十二地支中的一個(gè)時(shí)間。
卯時(shí)是凌晨五點(diǎn)到七點(diǎn),一天的日出時(shí)間,又名日始,初陽(yáng)漸升,大地復(fù)蘇。而從月份對(duì)應(yīng)看,卯對(duì)應(yīng)的是仲春,即農(nóng)歷二月,這也正好是一年之中萬(wàn)物生長(zhǎng)之時(shí),方向?qū)?yīng)正東方,五行屬木。卯木,正是灌木或柳樹(shù)(部分柳樹(shù)也屬于灌木)。古時(shí)有寅時(shí)點(diǎn)兵、卯時(shí)上陣的習(xí)慣,大概這一時(shí)間精神充沛,朝氣蓬勃吧。
如今我們?cè)倏赐蹙S的《送元二使安西》,便會(huì)心生疑惑:為什么是“渭城朝雨”呢?為什么是“柳色新”呢?王維選擇的送別時(shí)間正是仲春的某日卯時(shí)。大概是希望友人打起精神,“早點(diǎn)”出發(fā),就能“早點(diǎn)”到達(dá)落腳點(diǎn),抑或“早點(diǎn)”回家。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看,古代人折柳送別還真是不尋常。
《送元二使安西》也作《渭城曲》,后來(lái)改編成著名的送別曲,又叫《陽(yáng)關(guān)三疊》。我們知道漢之后送別都送到“陽(yáng)關(guān)”。“陽(yáng)關(guān)”是怎么來(lái)的呢?
陽(yáng)關(guān),始建于漢武帝年間,在黃河西“列四郡、據(jù)兩關(guān)”,兩關(guān)就是玉門(mén)關(guān)和陽(yáng)關(guān)。“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fēng)不度玉門(mén)關(guān)”。兩關(guān)作為通往西域的門(mén)戶,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關(guān)隘,是古代兵家必爭(zhēng)要地。漢代多走南路,過(guò)陽(yáng)關(guān)。西漢起,統(tǒng)一西域長(zhǎng)史府之后,就需要派人駐守。出陽(yáng)關(guān),即是茫茫大漠。
北朝樂(lè)府《鼓角橫吹曲》中就有《折楊柳枝》:“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李白《春夜洛城聞笛》詩(shī)句:“此夜曲中聞?wù)哿稳瞬黄鸸蕡@情。”劉禹錫《楊柳枝詞》:“長(zhǎng)安陌上無(wú)窮樹(shù),唯有垂楊管別離。”便都直接點(diǎn)到了這首曲子。竊以為,自漢到唐,《折楊柳枝》曲子應(yīng)該是帶著濃郁西域風(fēng)情的羌笛吹奏的。
那么,漢唐送別的起點(diǎn)在哪里呢?相傳為李白所寫(xiě)的《憶秦娥》交代得很清楚。
簫聲咽,秦娥夢(mèng)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lè)游原上清秋節(jié),咸陽(yáng)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fēng)殘照,漢家陵闕。
王國(guó)維評(píng)說(shuō)《憶秦娥》“西風(fēng)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guān)千古登臨之口。”“千古登臨之口”就是“灞陵”,位于西安城外,是漢孝文帝的墓,邊上有一座古老的灞橋,始建于春秋秦穆公時(shí)期。西安作為唐以前十三朝古都,送別大事,都在這座城外的灞橋上,“灞橋折柳”相襲成俗,至唐朝,還設(shè)了驛站。
王國(guó)維認(rèn)為《憶秦娥》氣象格局很大,是借用折柳,將人與人的送別,擴(kuò)大到更大的時(shí)空。一座灞橋,見(jiàn)證了王朝的相送。在歷史變更的長(zhǎng)河中,“灞橋柳”把“秦、漢、唐”三個(gè)強(qiáng)盛王朝的黯然銷魂者都凝結(jié)于一處。不過(guò),宏大盛世,仍敵不過(guò)一根柳條的柔腸寸斷。
因此,歷代詩(shī)文,提到“灞橋折柳”的典故最多。其中有這樣一首:楊柳含煙灞岸春,年年攀折為行人。好風(fēng)若借低枝便,莫遣青絲掃路塵。
(李益《途中寄李二》)
李益是唐代著名的邊塞詩(shī)人。家在隴西,位于河西走廊的要地,中原和西域的交界地,對(duì)陽(yáng)關(guān)送別應(yīng)該感同身受。隴西出了一個(gè)著名的李氏家族,李淵認(rèn)定隴西是郡望所在。連李白也認(rèn)為“家本隴西人”。在唐人蔣防的傳奇小說(shuō)《霍小玉傳》中,將李益描繪成一個(gè)負(fù)心才子,科舉及第之后,入贅太尉府,拋棄了離亂之時(shí)結(jié)識(shí)的紅顏知己霍小玉,小玉含憤而死。湯顯祖后來(lái)將此改編成著名的戲劇《折柳陽(yáng)關(guān)》。用以諷刺李益自己寫(xiě)的“楊柳徒可折,南山不可移。”所以,折楊柳,不僅是男兒壯行的信物,也是女子斷腸的繞指柔。
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wèn)行人歸不歸。西城楊柳弄春柔,動(dòng)離憂,淚難收。傷見(jiàn)路旁楊柳春,一重折盡一重新。楊柳何時(shí)歸,裊裊復(fù)依依。垂柳萬(wàn)條絲,春來(lái)織別離。……
這一折,一直到近代李叔同家喻戶曉的《送別》:“晚風(fēng)拂柳笛聲殘,夕陽(yáng)山外山。”收了古典情懷的尾聲。連新月派的徐志摩離開(kāi)康橋的時(shí)候,也念念不忘那河畔的金柳,離別的笙簫。不管是舊文化還是新文化,這就是中國(guó)文化的密碼。
自《詩(shī)經(jīng)》始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經(jīng)歷代的吟誦,一根柳條上映射著千百年來(lái)文人默契推動(dòng)形成的這一浩蕩風(fēng)景。“折柳送別”暗藏著一條“借物起興”形成意象的隱秘邏輯:藉由對(duì)自然萬(wàn)物的體認(rèn),到器物的生活傳承,靠歲月堆積成漢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
我們這個(gè)民族,曾經(jīng)是如此高貴地生活在萬(wàn)物化育的精神世界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