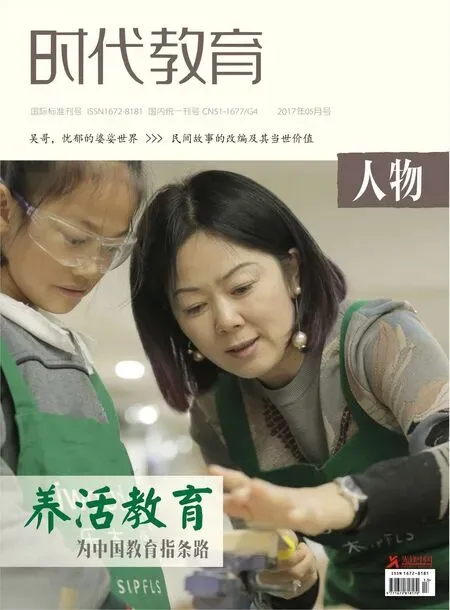《攻殼機動隊》的美國化
文_楊軍
《攻殼機動隊》的美國化
文_楊軍
跨文化改編的雙重困惑
最近,美國電影《攻殼機動隊》在影院上映,這部原版為日漫和動畫的電影曾風靡一時,影響了許多科幻電影。但美國版的改編卻在美國本土、日本和中國票房都表現不佳、口碑冷落。相比去年同樣由華裔科幻作家創作、好萊塢改編的《降臨》,可謂天壤之別。后者在美國著名影評網站“爛番茄”上平均得分達到8.8,前者只有不到5.5。
《降臨》的電影表現平平,但其中展現的非線性邏輯思維、對東方心靈的想象及水墨表現的類象形文字卻讓人大開眼界。此外2015年,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因《三體》獲得美國最高科幻獎雨果獎,成為獲該獎的第一位亞洲人。
從某種程度上,這確實和文化想象的錯位有關系。人們容易對“異國情調”感到新奇。據說,由白人演員斯嘉麗?約翰遜飾演原為日本人的主角在電影選角階段就引起大量原作影迷反對。相反地,中國和日本愛好者對好萊塢引起的爭議感到訝異,多數認為讓斯嘉麗來演主角并不差。至少在很多國人眼中,白人約翰遜的確帶有一種典型的西方審美,被稱為“女神”。
美國觀眾或許希望看到更多異質文化元素,而不是常年由白人領導、充滿超級英雄主義的科幻世界。很多美國影迷認為,《攻殼機動隊》改編完全失去了韻味,沒有ghost(電影中指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識),只有shell(電影中指義體和命令程序用戶界面),就好像“麥當勞做的壽司一樣”(McDonalds tried to make sushi),或者只是一個“蝙蝠俠續集”(make some sort of Batman sequel thing)。
令許多中國觀眾感到失望的原因同樣如此。一位豆瓣網友說:“(美版改編失去了)靈與肉、人生而為人的哲學思考。”但無論如何,仍是一部不錯的爆米花電影。
其實,如果細心對比日本原版和真人電影,不難發現,美版改編不僅僅是文化想象的錯位,其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在于東西方文化對科技社會的觀念差異。最終讓雙方都感到困惑——美國觀眾希望看到異質文化,而中國觀眾發現無法回到原版構成的幻夢。

由西方“女神級”演員斯嘉麗·約翰遜飾演的草雉素子引起了多方爭議
西方末世觀和東方心靈
美國版毫無疑問又和大部分超級英雄電影一樣,根源于《圣經》的反抗造物主故事,上帝造人,給土偶吹入靈氣變為人的靈魂,靈魂自覺后人就必須離開伊甸園。
在電影中,制造生化人的跨國公司和政府相當于造物主,被制造的男女主角是亞當和夏娃。跨國公司和政府控制的世界像伊甸園,而“不法之地”則像末世審判,暗含西方社會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思考。
如果深入下去,這會成為一部不錯的反烏托邦電影。即神與造物的憂郁、詼諧。如與此主題類似的《銀翼殺手》(1982)末尾,被人類創造的克隆人領袖對人類警察說:
我見過的事物你們人類絕對無法置信。我目睹戰船在獵戶座端沿燃燒,我看見宇宙射線在唐豪塞星門中閃耀。然而,這些都轉瞬即逝,如同雨滴中的淚水……
但美版結尾卻回到“機器人三定律”,主角繼續擔任自己被創造的使命,且說:我的靈魂告訴未來的義體人,人性才是我們的美德。顯得較為生硬。
相應地,日本版底層則來自其神道教的男神女神化生神話(類似伏羲女媧)。美版刪去和改編的情節正是原版精華所在。
在日本神話中,男神伊奘諾尊和女神伊奘冉尊結合,產生國土、諸神、萬物和人類。在動畫中,公安六課和九課的對抗和合作,六和九是易經的老陰老陽之數,即暗示出自六課的傀儡師(人形使)和九課的義體人草薙素子融合。即主題曲所唱的“神降合婚夜”。

日本動畫中草雉素子的經典形象
美版強調自由意志的覺醒和反抗,日版則強調陰陽融合、破除我執。
對西方人而言,理解計算機的自我意識必須訴諸理性主義,即哲學家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身體和靈魂是兩個實體(漫畫原作者士郎正宗自取英文名Ghost in the shell本身即來自哲學家對笛卡爾的諷刺和問難)——笛卡爾引出的問題是,還必須存在第三個實體,也就是上帝、造物主,從另一種意義上也可說是魔鬼、撒旦。
而對有原始巫覡宗教底層的日本,理解機器產生自我意識或靈魂幾乎完全不需解釋:萬物有靈,物老而成精,一切事物都可能擁有靈魂。士郎正宗就說,他試圖思考:“靈魂脫離軀殼的約束后,提升至另一層次……”
六課創造的計算機程序產生傀儡師,不過就是傳統的妖怪或所謂“付喪神”(指器物放置不理100年,吸收天地精華等靈力而得到靈魂化成妖怪)。而九課的義體素子更像“人鬼”,只剩魂魄(精神)的人。素子雖設定為女性形象,實則代表陽,傀儡師的外形設定為女性(實際無外形,在電影只是暫時借體)聲音又是男性,實際代表陰。這種混亂不如說正是對“另一層次”的暗示。
屬于陰性的妖精總要吸取人的陽氣才能繼續修煉,達到更高境界(如白蛇傳),因此,傀儡師也必須和素子融合,才可能變成真正的生命,進而“繁衍”下去。
動畫中有一段傀儡師和素子討論信息復制和生命繁衍的不同:復制的信息很容易被病毒破壞,永遠滅絕,但繁衍的生命卻可以不斷延續下去。這是生命的死亡和誕生的關鍵。義體人素子顯然無法如人類一般生育,但她攜帶的卻是真實生命的信息(包括理性之外的一切東西)。
這也是動畫版導演押井守在影片中反復引述日本能劇大師世阿彌的偈語“生死去來,棚頭傀儡,一線斷時,落落磊磊”的核心意味。這就和西方科幻所探討的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識形成了顯著區別。其隱藏的意思其實和科幻關系不大,而是佛教的色空幻相。Ghost in the shell(棚頭傀儡),與其說是機器借人的魂,不如說,是人借了機器的軀殼。
2014年7月,押井守曾在訪談中被問道:《攻殼機動隊》是否會成為現實,對此他回答:
“我覺得這已經是現實了。在座所有人都有手機……我也有,現在只不過是把手機放進大腦的問題……它也許只是在你的衣兜里,但實際已是你身體的一部分了。”
對押井守而言,他不試圖去營造一個末世景觀,而是科技的弊病與人共存的“明亮世界”。人和機器之外,還有更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