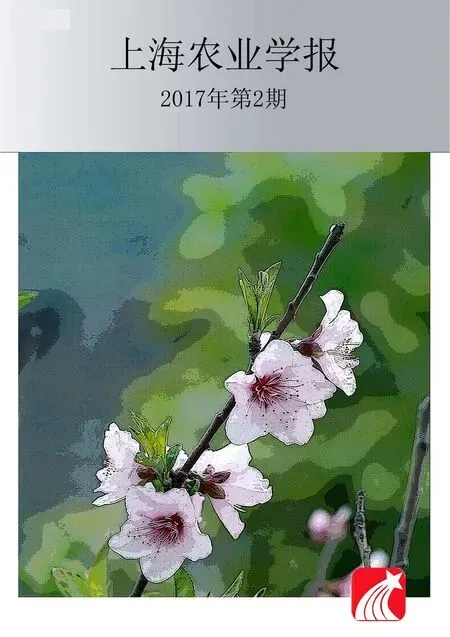生物耕作對崇明芋艿養分吸收及其分配規律的影響
李雙喜,何七勇,鄭憲清,張娟琴,袁大偉,張翰林,呂衛光
(上海市農業科學院生態環境保護研究所,農業部上海農業環境與耕地保育科學觀測實驗站,上海市設施園藝技術重點實驗室,上海市農業環境保護監測站,上海 201403)
生物耕作對崇明芋艿養分吸收及其分配規律的影響
李雙喜,何七勇,鄭憲清,張娟琴,袁大偉,張翰林,呂衛光
(上海市農業科學院生態環境保護研究所,農業部上海農業環境與耕地保育科學觀測實驗站,上海市設施園藝技術重點實驗室,上海市農業環境保護監測站,上海 201403)
通過田間試驗,研究了生物耕作(接種蚯蚓)對芋艿N、P、K、Ca、Mg吸收及在體內分配的影響。結果表明:不同耕作方式下,芋艿植株不同器官對N、P、K、Ca、Mg等元素的吸收和分配規律是一致的。與傳統機械耕作(CK)相比,生物耕作(T2)可以大幅促進N、P、K、Ca、Mg等元素在芋艿體內的積累(P<0.05),幼苗期以及發棵期(出苗后60 d)的N、P、K分配均為葉柄>葉片>根,Ca、Mg分配為葉片>葉柄>根;發棵期(出苗90 d)以及球莖膨大期的N、P、K主要分配在球莖中,子芋和孫芋中N、P、K含量最高,Ca素和Mg素則主要分布在子芋和葉片內,其他器官較少。在傳統的農業生態系統中,培育土壤有益動物(生物耕作)可提高養分利用效率,對實現芋艿產業可持續生產具有重要意義。
生物耕作;蚯蚓;芋艿;礦質養分;吸收分配
芋[Colocasia esculenta(L.)schott]是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國長三角地區典型的特色蔬菜之一,具有較高的營養價值和保健價值。香酥芋在崇明縣有較長的栽培歷史,肉質細膩,煮而不糊,是崇明縣十大特色農產品之一,深受上海市民喜愛。目前,上海崇明地區香酥芋的栽培面積有166 hm2左右,由于其具有較好的效益,種植面積逐年增加。前人關于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種質資源分布、品種劃分、遺傳多樣性分析、營養成分分析、芋艿繁殖以及相關傳統栽培技術等方面[1-5],關于芋艿的養分利用及分配研究較少,如宋春鳳等[6]研究了傳統栽培條件下萊陽孤芋的氮磷鉀養分吸收狀況。目前芋艿栽培全憑農戶的傳統經驗,由于長期連作栽培,芋艿田出現了連作障礙問題[7],研究人員發現生物耕作(釋放蚯蚓)可以有效緩解芋艿的連作障礙問題(另文發表)。為此,本試驗比較了不同耕作方式下芋艿對N、P、K、Ca、Mg等礦質養分的吸收分配規律,以期為優化崇明地區芋艿的生產方式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試驗區設置在上海市崇明縣三星鎮西新村,試驗區所在的崇明島地處北亞熱帶,具有顯著的季風氣候特征。年平均氣溫15.3℃,降水量1 003.7 mm,日照時數2 104 h,日照百分率47%,全年無霜期229 d。試驗田主要的蔬菜茬口為芋艿-花椰菜模式。生物耕作接種的蚯蚓為‘滬地龍’,為威廉腔環蚓,每條鮮重4 g左右,接種蚯蚓為15條/m2。蚯蚓種源由上海富年藥材有限公司提供[8]。
1.2 試驗設計
供試芋艿材料為崇明本地種香酥芋。試驗設機械旋耕(CK)、免耕(T1)以及生物耕作(T2)3個處理,每處理重復3次,小區面積134 m2,隨機排列。免耕即不采取任何機械耕作措施;機械旋耕深度為15 cm;生物耕作接種蚯蚓為15條/m2。為了防止蚯蚓由接種小區向其他處理小區遷移,小區之間開有水溝做天然屏障[8]。試驗小區所用肥料為練科牌商品有機肥(N+P2O5+K2O>5%),基肥施用量為30 t/hm2。試驗跨度為6個月(2014年4—10月),采樣從5月持續到10月。
1.3 調查及取樣方法
芋艿出苗后每隔30 d取樣1次,每次取5株,重復3次。樣品洗凈后,按葉、葉柄、根、母芋、子芋、孫芋等器官分開,105℃殺青15 min,在75℃下烘干至恒重。將干樣磨碎過篩后,用凱氏定氮法測全氮,鉬銻抗顯色法測全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測全鉀、全鈣、全鎂[9]。
1.4 數據處理
使用Excel 2007和SPSS 16.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P<0.05為差異顯著,P<0.01為差異極顯著。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耕作方式下芋艿植株不同器官氮素積累及分配特點
不同處理下,芋艿植株不同器官對氮素的吸收和分配規律是一致的。隨著生育期的進程,氮素在葉片、葉柄、根、母芋、子芋以及孫芋中的積累量逐步增加。但在不同時期,各器官氮素的分配有一定的差異,表現為:幼苗期,葉柄>葉片>根;發棵期(出苗后60 d),葉片>葉柄>根;發棵期(出苗后90 d),子芋>葉片>葉柄>母芋>根>孫芋;球莖膨大期,子芋>孫芋>母芋>葉片>葉柄>根。
生物耕作(T2)各個時期植株不同器官中氮素含量與機械耕作(CK)均有顯著差異。與免耕處理(T1)相比,在發棵期(出苗后90 d),生物耕作大幅促進了孫芋對氮素的吸收和分配,差異呈極顯著。從表1可知,在發棵期,超過50%的氮素分配到芋艿葉片中,在球莖膨大期,地上部(葉片和葉柄)氮素分配率逐漸減少,子芋和孫芋含量逐漸增加,CK、T1、T2處理地上部(葉片和葉柄)氮素分配率依次為21.7%、21.8%和22.1%,3種處理芋球莖中氮素占植株氮素的比例依次為76.3%、76.33%和76.42%。生物耕作(T2)促進了芋艿對氮素的吸收和分配,可能是因為蚯蚓活動增加了包括土壤氨化和硝化細菌在內的微生物數量[10-11],土壤中氨化細菌數量的增加,使更多不能被植物所利用的有機含氮化合物轉化為可給態氮,也為植物及其他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動創造了良好的營養條件[12]。此外,氮素是葉綠素的重要組成成分,芋艿發育前期葉片進行光合作用滿足代謝需求,因而發棵期(苗后60 d)之前都是葉片中含量最高;隨著生育期的過程,葉片生長基本穩定,生長重心轉移到地下部(子芋和孫芋),氮素等營養元素轉移運輸到生長最旺盛的部位,因而造成在球莖膨大期氮素分配的差異。

表1 不同耕作方式對各個生育期芋艿植株各器官氮素(N)養分分配的影響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tillage ways on nitrogen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taro organs at different grow th stages mg·株-1
2.2 不同耕作方式下芋艿植株不同器官磷素積累及分配特點
芋艿植株對磷素的積累及分配與氮素有相似之處。磷素是細胞核的主要組成部分,同時參與植物生長所需的各種酶的組成。磷素首先向生長中心運輸和轉移,并且具有較大的移動性[13]。如表2所示,隨著生育期的過程,不同處理磷素在葉片、葉柄、根、母芋、子芋以及孫芋中的積累量逐步增加。但是在不同時期,各器官磷素的分配有一定的差異,表現為:幼苗期,葉柄>葉片>根;發棵期(出苗后60 d),葉柄>葉片>根;發棵期(出苗后90 d),子芋>葉柄>葉片>母芋>孫芋>根;球莖膨大期,子芋>孫芋>母芋>葉片>葉柄>根。

表2 不同耕作方式對各個生育期芋艿植株各器官磷素(以P2O5計)養分分配的影響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tillage ways on phosphorus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taro organs at different grow th stages mg·株-1
生物耕作(T2)各個時期植株不同器官中磷素含量與機械耕作(CK)均有顯著差異。與免耕處理(T1)相比,在發棵期(出苗后90 d),生物耕作大幅促進了子芋對磷素的吸收和分配,差異呈極顯著。從表2可知,在發棵期(出苗后60天),超過50%的磷素分配到芋艿葉片中,在發棵期至球莖膨大期,地上部(葉片和葉柄)磷素分配率逐漸減少,子芋和孫芋逐漸增加,說明生長中心下移,磷優先運往地下部位;球莖膨大后期葉片衰老,葉中磷素開始外運,尤以球莖膨大期(出苗后150 d)T2處理的子芋磷素增加幅度最為明顯,分別比CK和T1處理多46 mg/株和22 mg/株,這是因為生物耕作增加了土壤中無機磷分解菌的數量[11],促使土壤中的不溶性無機磷轉化為可溶性磷鹽,從而促進了磷素被植物吸收[14]。
2.3 不同耕作方式下芋艿植株不同器官鉀素積累及分配特點
鉀是植物生長所必需的一種成分。植物通過根系從土壤中選擇性地吸收土壤中的水溶態鉀離子,鉀元素比較集中地分布在植物代謝最活躍的器官和組織中。如表3所示,隨著生育期的進程,不同處理鉀素在葉片、葉柄、母芋、子芋以及孫芋中的積累量逐步增加,根中的鉀素積累量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特點。但是在不同時期,各器官鉀素的分配有一定的差異,表現為:幼苗期以及發棵期(出苗后60 d),葉柄>葉片>根;發棵期(出苗后90 d),葉柄>子芋>葉片>母芋>根>孫芋;球莖膨大期,孫芋>子芋>葉柄>葉片>母芋>根。
生物耕作(T2)處理除球莖膨大期(出苗后150 d)根中鉀素差異不顯著外,其他時期以及不同器官內鉀素含量均與機械耕作(CK)差異顯著。由表3可知,鉀素在幼苗期以及發棵期(出苗后60 d)多分布在葉片和葉柄中,以葉柄為主,占全株鉀素含量的60%以上。隨著生育期的延長,尤其是發棵期(出苗后90 d)子芋中鉀素急劇增加,至球莖膨大期,孫芋中鉀素含量最高,分配最多,生物耕作(T2)處理表現的尤其明顯。

表3 不同耕作方式對各個生育期芋艿植株各器官鉀素(以K2O計)養分分配的影響Table 3 Effect of different tillage ways on potassium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taro organs at different grow th stages mg·株-1
2.4 不同耕作方式下芋艿植株不同器官鈣素積累及分配特點
鈣是形成果膠鈣的主要成分,在作物體內果膠鈣有助于細胞壁的發育,能促進作物體內細胞的分裂,并對碳水化合物的轉化和氮素代謝有良好效果。如表4所示,隨著生育期的進程,不同處理鈣素在葉片、母芋以及子芋中的積累量逐步增加,葉柄、根以及孫芋中的鈣素積累量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特點,均在出苗后120 d達到最高。不同時期各器官鉀素的分配有一定的差異,表現為:幼苗期以及發棵期(出苗后60 d),葉片>葉柄>根;發棵期(出苗后90 d),葉片>葉柄>子芋>根>母芋;球莖膨大期(出苗后120 d),葉片>葉柄>子芋>孫芋>母芋>根;球莖膨大期(出苗后150 d),葉片>葉柄>子芋>母芋>孫芋>根。
在球莖膨大期生物耕作(T2)處理葉片中鈣素基本保持不變,而免耕(T1)和機械耕作(CK)呈增加趨勢,在球莖膨大期(出苗后120 d)生物耕作處理葉片中的Ca含量最高達到419 mg,顯著高于T1和CK處理;此外,從出苗后30 d到成熟期,芋艿吸收的鈣素有45%以上分配在葉片中,其次分配在葉柄中,子芋比母芋和孫芋分配的多。
2.5 不同耕作方式下芋艿植株不同器官鎂素積累及分配特點
鎂是葉綠素的主要成分,能促進磷酸酶和葡萄糖轉化酶的活化,有利于單糖的轉化,因而在碳水化合物代謝過程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如表5所示,隨著生育期的進程,不同處理鎂素在子芋和孫芋中的積累量逐步增加,葉片、葉柄、根以及母芋中的鎂素積累量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特點,均在出苗后120 d達到最高。不同時期各器官鉀素的分配有一定的差異,表現為:幼苗期以及發棵期(出苗后60 d),葉片>葉柄>根;發棵期(出苗后90 d),葉片>葉柄>子芋>母芋>根;球莖膨大期(出苗后120 d),葉片>葉柄>子芋>孫芋>母芋>根;球莖膨大期(出苗后150 d),子芋>葉片>孫芋>葉柄>母芋>根。

表4 不同耕作方式對各個生育期芋艿植株各器官鈣素(Ca)分配的影響Table 4 Effect of different tillageways on calcium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taro organs at different grow th stages mg·株-1

表5 不同耕作方式對各個生育期芋艿植株各器官鎂素(M g)分配的影響Table 5 Effect of different tillagewaysonmagnesium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taro organs at different grow th stages mg·株-1
在各個時期,生物耕作(T2)處理芋艿各個器官的鎂素含量與機械耕作(CK)均有顯著差異,而與免耕(T1)處理差異不顯著。芋艿吸收鎂素主要分配在葉片中,收獲期子芋中分配比葉片多,生物耕作能夠大幅提升芋艿各個器官對鎂素的吸收和積累。
3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顯示,在不同的耕作方式下,N、P、K、Ca、Mg等元素在芋艿不同器官內的含量和分配隨生育期的延長有很大變化。與傳統機械耕作(CK)相比,生物耕作(T2)可以大幅促進N、P、K、Ca、Mg等元素在芋艿體內的積累與分配,促進芋艿的生長發育。
就分配特點和規律而言,3種耕作方式處理下N、P、K、Ca、Mg等元素的分配規律是一致的。但是不同器官的分配規律有一定的差異,葉片、葉柄、母芋、子芋以及孫芋的N、P、K養分含量保持增加趨勢,但是不同生育期Ca和Mg差異較大。幼苗期以及發棵期(出苗后60 d)的N、P、K分配均為葉柄>葉片>根,Ca、Mg分配為葉片>葉柄>根;發棵期(出苗90 d)以及球莖膨大期的N、P、K分配主要表現為地下部>地上部,根系分配最少,Ca素含量則表現為地上部>地下部,Mg素則主要分布在子芋和葉片內,其他器官較少。
合理的耕作措施可以提高土壤的養分,調節土壤pH、水分等,對植物的生長有很大促進作用[8]。前期的研究顯示,釋放蚯蚓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活性、酶活性等,土壤酶積極參與土壤中氮、磷等礦化過程,從而促進其吸收利用[15-16]。釋放蚯蚓(生物耕作)后,它的代謝產物與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促進氮素的轉化吸收和利用,Ca素和Mg素的吸收與氮素有很大的相關性,本研究也證明了生物耕作(T2)處理下芋艿各器官的Ca素和Mg素含量均高于T1和CK處理。因此,釋放有益土壤動物(蚯蚓)進行生物耕作,可以更高效地利用土壤養分,改善傳統芋艿生產過程中養分利用效率低下的問題,從而實現芋艿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1]黃新芳.中國芋種質資源研究進展[J].植物遺傳資源學報,2005,6(1):119-123.
[2]沈鏑.芋種質資源的耐藏性調查[J].長江蔬菜,2002(12):37-38.
[3]李慶典,楊永平,李穎.中國芋種質資源的遺傳多樣性及分類研究[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30(5):424-428.
[4]IRWIN S V,KAUFUSIP,BANKS K,et al.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taro(Colocasia esculenta L.schott)using RAPD markers[J].Euphytica,1998,99:183-189.
[5]CAILLON S,QUERO-GARCIA J,LESCUREIJP,et al.Nature of taro(Colocasia esculenta(L.)schott)genetic diversity prevalent in a Pacific Ocean island,Vanua Lava,Vanuatu[J].Genetic Resources and Crop Evolution,2006,53:1273-1289.
[6]宋春鳳,徐坤.芋對氮磷鉀吸收分配規律的研究[J].植物營養與肥料學報,2004,10(4):403-406.
[7]杜紅梅,黃丹楓.芋艿品種退化的原因及解決途徑[J].中國蔬菜,2002(6):58-60.
[8]李雙喜,鄭憲清,袁大偉,等.生物耕作對菜田土壤理化特性、酶活性及青花菜生長和品質的影響[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2,20(8):1018-1023.
[9]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理化分析[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62-142.
[10]胡鋒,王霞,李輝信.等.蚯蚓活動對稻麥輪作系統中土壤微生物量碳的影響[J].土壤學報,2005,42(6):965-969.
[11]李雙喜,鄭憲清,袁大偉,等.生物耕作對菜田土壤微生物區系及細菌生理類群的影響[J].華北農學報,2012,27(增刊):339-344.
[12]BILAL R.Associative of nitrogen-fixing plant growth promoting rhisobacteria(PGFPR)with kallar grass rice[J].Plant and Soil,1997,194:37-44.
[13]白寶璋,田紀春,王清連.植物生理學[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6.
[14]CHEN Y P,REKHA P D,ARUN A B,et al.Phosphate solubilizing bacteria from subtropical soil and their tricalcium phosphate solubilizing abilities[J].Applied Soil Ecology,2006,34:33-41.
[15]CECCANTIB,GARCIA C.Coupled chemical and biochemicalmethodologies to characterize a composting process and the humic substances[M]∥Senesi N,Miano T.Humic substance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nd its implication on human health.New York:Elsevier,1994.
[16]胡佩,劉德輝,胡鋒,等.蚓糞中的植物激素及其對綠豆插條不定根發生的促進作用[J].生態學報,2002,22(8):1211-1214.
(責任編輯:閆其濤)
Effects of biological tillage on nutrient absor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hongm ing taro
LIShuang-xi,HE Qi-yong,ZHENG Xian-qing,ZHANG Juan-qin,YUAN Da-wei,ZHANG Han-lin,LYUWei-guang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Plant Protection,Shangha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Shanghai Scientific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ation for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Land Conservation,Ministry of Agriculture;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rotected Horticultural Technology;Shangh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nitoring Station of Agriculture,Shanghai201403,China)
The effect of biological tillage(earthworm)on N,P,K,Ca,Mg absor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aro plant[Colocasia esculenta(L.)schott]was studied by field experimen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bsor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N,P,K,Ca,Mg in different organs of taro plant were similar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ways.Compared with CK,biological tillage(T2)could greatly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of N,P,K,Ca,Mg in taro plant(P<0.05).In seedling stage and tiller stage(60 days after emergence),the distribution of N,P and K were petiole>leaf>root,Ca,Mg were leaf>petiole>root.In tiller stage(90 days after emergence)and corm expansion stage,N,P and K were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orm,the content of N,P and K were the highest in the first grade taro and the second grade taro;Ca and Mg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first grade taro and leaves,less in the other organs.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system,cultivation of soil beneficial animal(biological tillage)c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utrient utilization,which was has important in realiz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 of taro industry.
Biological tillage;Earthworm;Taro;Mineral nutrition;Absorption and distribution
S632.3
:A
1000-3924(2017)02-037-06
10.15955j.issn1000-3924.2017.02.07
2015-11-04
上海市農口青年成長項目[滬農青字(2014)第1-25號];上海市長三角國內合作項目(14395810602);上海市科技興農推廣項目(滬農科推字(2013)第4-1號);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2010BAK69B18)
李雙喜(1986—),男,在讀博士,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生態農業、設施農田土壤障礙研究與防治工作。E-mail:lsx198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