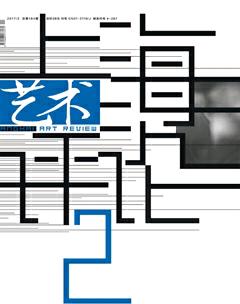詩與思的對話
周計武
上海是中國當代抽象藝術發展的策源地之一。1932年,龐薰琹、倪貽德等藝術家在上海成立決瀾社,莊嚴地喊出了中國抽象藝術的宣言:“用狂飆一樣的激情,鐵一般的理智,創造色、線和形交錯的世界。”1這種抽象的沖動經過林風眠、林文錚等人的倡導,趙無極、朱德群等留法藝術家的創造性實踐,為中國當代藝術播下了種子。改革開放以來,李山、余友涵、陳箴、周長江、丁乙、馮良鴻等上海抽象藝術的先鋒人物,在繪畫、雕塑、觀念與裝置等藝術領域進行了大膽而可貴的探索。這些探索形成了一種潛移默化的藝術氛圍,為李磊的抽象藝術實驗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從1997年的《禪花》系列開始,到2007年創作《海上花》系列,再到2016年的《天女散花》系列,李磊一直以前衛精神的沖動,不斷在媒介、語言與觀念上進行抽象藝術的實驗。本文旨在以李磊的抽象畫為例,闡釋中國抽象藝術的獨特魅力及其潛在的文化邏輯。
抽象與抽象藝術
抽象藝術是一個來自西方藝術界的概念。在西方現代主義的語境中,它至少具有三個層面的意思。
首先,抽象藝術是創造性精神的感性顯現。沃林格的《抽象與移情——對藝術風格的心理學研究》(1907)和康定斯基的《論藝術的精神》(1910)是抽象藝術合法化的理論基礎。康定斯基認為,抽象是一種創造精神,是人類靈魂由內而外的呼喚。抽象藝術遵循“內在必需”原則,有鮮明的個性印跡,因為“精神的呼喚是形式的靈魂。呼喚使形式獲得了生命,且由內而外地發生作用”。2沃林格則用李格爾(Alois Riegl)的“藝術意志”概念來解釋藝術創造的心理本原。藝術意志是一種先于藝術品而存在的創造沖動。它包括兩種沖動:移情沖動和抽象沖動。“移情沖動是以人與外在世界的那種圓滿的具有泛神論色彩的密切關聯為條件的,而抽象沖動則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內心不安的產物。”3移情沖動是主體在審美活動中賦予情感以形式,用充滿生命力的線條、色彩與造型表達理想的自足性,以此喚醒對有機生命的感知和形式的愉悅感。抽象沖動是主體在審美活動中順應內在精神的需要,通過直覺創造,賦予不確定的表象世界以永恒的形式,以此擺脫人類存在的偶然性,實現精神的自足與純粹。無論移情還是抽象,都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形式化沖動,旨在從空間中拯救碎片化的形式,賦予其永恒的意義。我們的藝術傳統傾向于“移情”,通過“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來表達內在精神的自足與圓滿,盡美盡善;西方的藝術傳統傾向于“以物觀物”,通過形式化的純粹造型來探索宇宙的本原和人類的精神,求真求實。不過,中國藝術也有抽象的因素,西方藝術也有移情的基因。
其次,抽象藝術是藝術創造的方法論。作為方法論,抽象藝術本質上是一種審美創造與升華的過程。一是抽離,把外在的物象“從變化無常的虛假的偶然性中抽取出來”,凈化一切瞬間易逝之物,“使之永恒并合乎必然”。4二是造型,遵循內在的聲音,通過形式化的構圖,尤其是點的重復與交疊、線的張力與方向、色的平涂與暈染,實現圖與底、線與面、形與色的平衡。三是升華,把自由的主體精神貫注于形式的表達之中,通過視聽的聯覺作用,把線條、色彩等獨立的聲音組合成整體的和聲,使生命的律動與造化自然的規律相和諧,實現靈魂的激蕩與共鳴。在方法論上,抽象與寫實的邏輯對立是片面的,因為二者都是藝術造型的手段,寫實藝術中可以有抽象,抽象藝術中也可以有寫實。如同寫實強調透視、解剖、明暗與色彩漸變的造型原理一樣,抽象認可神秘的即興品質以及對點、線、面進行抽象操作的能力。差異在于,抽象藝術并不描述可見之物,而是表征不可表征之物。它堅持審美的自主性,竭力從構圖中摒棄三維空間,消除再現性、形象化和描述性的東西,轉而以平面表現為主。5
再次,抽象藝術是內在于西方現代主義思潮中的一種風格。從廣義上來說,它源于塞尚、梵·高、高更以來對藝術再現傳統的質疑及其個性化形式化的探索。文藝復興以來的藝術再現傳統之所以受到質疑,是因為它把藝術的進步等同于再現自然的技藝,一切累積起來的再現科學——線性透視、明暗漸進法、解剖學原理與大氣色彩變化的知識,在對大自然的描繪中已經逐漸失去了回應人類激情、表達深邃思想的力量。若要激發藝術家的想象力,就要切斷藝術中單純再現的因素,在自然形式的變形、無規則的簡化和抽象的構圖中確立表現形式的根本法則,呈現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and expressive form)。6在藝術造型中,線條、色彩與平面的韻律是根本性的品質,而再現則是第二位的。從狹義上來說,它特指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馬列維奇、紐曼等人開辟的抽象藝術傳統。它強調藝術形式的純粹性,主張一幅藝術品的價值就在于它的線條、顏色、形狀及其形式的韻律感。不過,如夏皮羅所言,不存在純粹的抽象領域,抽象藝術同樣受制于經驗與非審美的關切,帶有社會心理和審美趣味變化的烙印。7
綜上所述,抽象藝術在西方具有明確的觀念、方法與風格,具有審美自主性與形式實驗性的雙重特征,旨在打破文藝復興以來的藝術再現傳統,重新激發藝術家的想象力,喚回藝術家的創造性激情和藝術形式的生命力。一言以蔽之,西方具有抽象藝術的傳統,是由內而外、自然而然產生的。與之相比,我們的抽象藝術是再生性的,是從西方藝術界借用來的概念。那么,我們是否擁有屬于自己的抽象藝術?
對此,學術界有兩種極端的聲音,一是主張中國自古就有抽象藝術,二是宣稱中國沒有抽象藝術。前者認為,形的抽象能力是一切藝術的邏輯前提,中西方皆然。8早在新石器時代,抽象的幾何紋飾通過點、線的重疊、回旋、交錯,尤其是線的粗細、長短、曲折、橫豎的有規則排列,就開始大量出現。由于偏重主體情感的表現、書法美學的早熟和書畫工具的同源,中國藝術形成了以線條勾描、色彩暈染為特色的筆墨語言和傳神寫意的傳統;由于側重再現物象的具體質感與肌理,西方藝術在線性透視和三維空間的營造上獨樹一幟,形成了如其所見的再現傳統。后者認為,我們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抽象藝術。9西方抽象藝術與數學、量子物理學、色彩心理學等現代科學原理緊密相連,旨在顛覆三維空間的視錯覺,讓繪畫回歸平面性,以理性主義精神探索宇宙的內在本質。從康定斯基的抒情抽象、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義和馬列維奇的至上主義開始,歷經構成主義、抽象表現主義、光效應藝術、色域繪畫、硬邊抽象,一直到極簡主義藝術,西方抽象藝術走到了自身邏輯與歷史的終點。
上述兩種聲音之所以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判斷,是因為兩者的邏輯前提和立意基礎不同。前者是在方法論意義上討論抽象藝術,旨在強調藝術創造的共同本原——形的抽象能力;后者是在歷史目的討論意義上討論抽象藝術,旨在突出西方抽象藝術的內在意志——求真向實(truth)。換言之,在前者的話語體系中,抽象藝術是一個規范性的邏輯概念,旨在闡釋抽象藝術的一般屬性;在后者的話語體系中,抽象藝術是一個風格化的歷史概念,從康定斯基的抒情抽象開始到極簡主義結束。因此,二者所言的概念不同、對象不同,結論迥然有異也就不奇怪了。
與上述兩種觀點不同,我們認為存在一種中國式的當代抽象藝術。它不同于康定斯基、波洛克等人表現的“抒情抽象”,也不同于蒙德里安、馬列維奇等人創造的“幾何抽象”,而是汲取傳統藝術的筆墨情趣與西方藝術的抽象形式,創造一種中西融合的當代抽象藝術。對于它的核心特征,朱青生稱其為“第三抽象”,10一種在筆墨語言的形式傳統中寄托抽象化的情思與曠達的人生境界;黃篤命名為“超逸”,11一種不拘泥于法度、虛實相生、詩思和諧的格調;高名潞概括為“極多主義”,12一種通過“過程”“重復”“散點”“隨機”等中式視覺語言,反對自我表現與意義泛濫的中式解構主義或現代禪。它雖然沿用“抽象藝術”之名,但它的話語體系、表達習慣與精神旨趣都深刻地打上了中國藝術精神的烙印。
詩意與節奏
李磊的抽象畫是從1997年的《禪花》系列開始的。觀其抽象畫,如看懷素的字,彌漫在整個畫面上的線與色,充滿著內在的張力與節奏感,酣暢而寂靜。畫中有詩,詩意激蕩在流動的空間中;畫中有樂,韻律凝固在氤氳的色域中。在此意義上,批評家稱其為“詩性抽象”。龔云表從畫面中感受到豐富的音韻、旋律和節奏,“這是一種用筆觸和圖式構建的詩的語言,幻化出獨具魅力的詩的意蘊,傳遞出富有詩歌內涵的審美境界,一個詩意的世界。”13孫周興也認為,它是“一種用色彩鋪張出來的詩意”。14那么,什么才是畫中的詩意?詩意是通過何種方式加以建構的?詩意何為?
自北宋以來,詩畫相通相融的看法就不絕如縷。如清代葉燮所言:“畫者形也,形依情則深;詩者情也,情附形則顯。” 15好的畫與好的詩一樣,是情與形、意與象、動與靜的交融。顧名思義,詩意就是詩情畫意,是情趣與意象的契合,是氣韻靈動的意境。詩意的營造依賴于以下三種方式。
一是直覺的創造。與蒙德里安的幾何抽象不同,李磊的繪畫具有即興表現的氣質。飛舞靈動的線條、大膽率真的用色、豪放粗糲的筆觸,使整個畫面元氣貫通、生氣勃勃,充滿了視覺語義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源于內在情趣率性而自然的表達。當然,它也與波洛克式的無意識繪畫不同。各種夢境般的形象與色塊與其說是無意識地表達,不如說是對具體表象的直觀把握。直觀是對形式的凝視和玩味,旨在把握形式中最富有意蘊的特征,目擊而道存。李磊在創造《憶江南》時,一改早期過于圖示化的形式,僅僅抓住江南山水中那些讓自己內心感動的經典意象來表征詩化的自然。“第一個感覺是整體上的調子是綠;第二個特性是水,江南的水,在我的畫面上我去尋找一種流動性的東西;第三個是‘彌漫,就是造型的不確定性。通過這三個元素的組合來尋找我心目中的人文江南。”16觀看是一種選擇行為。當藝術家觀看風景時,他的觀看方式受到傳統圖式與個人素養的影響,那些與他的慣用手法相匹配的景象會躍然而出,成為視覺注意的中心。因為“藝術家的傾向是看到他要畫的東西,而不是畫他所看到的東西。”17換言之,藝術家傾向塑造與他們的風格及修養相契合的對象。這表明文人畫的寫意傳統深刻地影響與改造了李磊的抽象畫風格。
二是憑虛構象。李磊畫面中的象源于天地自然,比如,反復出現的花、水、樹等形象。一方面,這些形象受到藝術家情趣的影響,已不是眼中之物,而是藝術家運用想象創造的意象,是情與景、意與象的融合。另一方面,這些形象經過藝術家的簡化與變形,已經幻化為流動的色塊、朦朧的輪廓與抽象的造型,似花非花,似水非水,皆浮動于形與色的平衡構圖之中。這些構圖將特殊的肌理融入光色的視覺表現之中,處處可見書法的飄逸、水墨的玄妙與音律的節奏。在油畫《禪花》中,片片花瓣幻化成星星點點的色域,均勻地分布在不同顏色構成的矩形框架內,形成一種內斂、肅穆而憂傷的視覺心理。大面積平涂的底色往往由深綠、淺藍、黑灰等冷色調構成,與矩形畫框內紅黃藍綠等五彩繽紛的暖色調形成對比,強化了“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陸游《卜算子·詠梅》)的視覺效果。如果說《禪花》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那么《海上花》系列中的意象完全是內心營構之象,是直覺的、想象的、情感的。畫面很難依據相似性原則,讓觀看者聯想到具體的物象。除了絢麗燦爛的色彩、回旋往復的線條、虛實相生的空間,畫框之內一無所有。這種抽象的形式既具有酣暢飽滿、蕩人心魄的力量,又具有枯寂虛無、令人遐思的美感。
三是明快的節奏。節奏是指畫面中交替出現的有規律的強弱、長短、緩急等現象。李磊的抽象畫之所以具有使人趨于平和、寧靜的精神感召力,是因為其內在的節奏可以讓想象自由持續地活動。繪畫善于用空間中并列的形體和顏色,表達生命中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空間賦予精神以永恒的形式,而節奏則使空間“時間化”,讓有意味的形式在精神的想象活動中綿延。這種節奏感主要表現在筆觸的輕重緩急、線條的曲直長短、色彩的明暗冷暖、墨色的枯潤濃淡、布局的縱橫欹側等內在的變化與張力上,從而形成了康定斯基所言的“內在的聲音”。這種富有節奏的語言明顯受益于中國書法的點畫結構與意、蘊、氣、勢,受益于點墨無痕、骨法用筆的寫意畫傳統。當然,這種視覺的音樂性相比音樂與詩歌來說,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李磊本人所說:“節奏和音符都是預設的,而繪畫的音樂性,或者說‘刺激點則完全視乎作者和觀者的境界,你究竟是先看到哪一片色彩哪一個線條,每個觀者的經驗都是不一樣的。抽象畫的音樂性和‘刺激點更加本質,更少干擾,因為它沒有寫實畫那樣的故事情節、形象線索的制約與攪擾。”18
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李磊的抽象畫之所以充滿詩意與樂感,是因為力透畫面的情感與想象讓形式獲得了永恒的“意味”,是因為在視覺語言中寄托了形而上的思考與感悟。
禪思與張力
畫為心聲,李磊的抽象畫是對生命的直觀體驗。在點、線、面、色的動態組合與運思落筆中,既有對現實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與情感體驗,也有對方生方死之命運的禪思與感悟。無論是早期的《禪花》《道》,還是最近的《海上花》《天女散花》,都不過是畫家尋求自我超脫、自我修行、表達靈魂自由的媒介。
李磊的藝術生涯是在不斷的探索與實驗中前行的,先后經歷了具象、變形、抽象、多元四個發展階段。1986年到1990年的絲網版畫屬于具象階段,《太陽鳥》形式稚拙、粗糲,以包裹在僵硬結構中的自畫像和鳥的隱喻,來暗示孤獨、壓抑、掙扎的存在境遇。1991年到1996年屬于變形階段,《我愛小小鳥》(1991)、《止觀》(1992)、《月亮蛇》(1996)等油畫以簡化和變形的方法,呈現了三足太陽鳥、人面蛇身的女媧和月亮蛇等遠古神話中的形象。這些形象介于具象與抽象之間,以簡潔的幾何形構圖和色調的均衡對比,實現了內在精神的和解。1996年到2016年屬于抽象畫階段,粗疏曲折的線條、交錯回旋的色域、彌漫畫布的空間,形成了它特有的格調。《禪花》雖然殘留具象的痕跡,但他獨參畫禪,引為玄悟,筆法細膩,命意深遠。畫面依類象形,虛實結合,色塊規整,層次豐富,具有一種內在的張力和獨特的意蘊。從《天堂的色彩》作品系列開始,李磊的精神自省開始又一次心靈的突圍。他師法自然,澄懷味象,怡情于山水之間,在向詩情畫意的回歸中,實現了情與理的中和、形與色的平衡。在《憶江南》《意象武夷》《醉湖》等“人文山水”系列中,他筆意簡淡,傳染有度,蒼勁圓潤,時有逸氣,已得“詩性抽象”之真諦。《海上花》系列(2007-2015)是李磊又一次果敢的精神實驗。他穿行在上海都市的人流中,以悲憫的情懷打量行色匆匆的人群、琳瑯滿目的商品和勾人心魄的奇觀。這是一座在欲望與焦慮中漂流的都市,激情撞擊出纏綿,幻化為漫天飄舞的花瓣。李磊用色大膽,不拘繩墨,筆情縱恣,意趣生動,以光怪陸離的色塊為我們表征了無根的花之海。這種充滿激情與張力的視覺結構,用筆觸與色彩表達了都市的喧嘩與躁動、靈魂的饑餓與渴望、生命的掙扎與吶喊。2016年至今,屬于多元實驗階段,李磊在《天女散花》中廣泛采用雕塑、油畫、裝置等多種媒介、材料與技術手段,延續了《海上花》“介入”社會的觀念與立場,表達了對生與死、靈與肉的拷問。
縱觀李磊的藝術生涯,他對存在境遇的反省、造化自然的詩化和都市奇觀的拷問,莫不在充滿道與禪的詩意結構中表達了情與理、實與虛、有與無的辯證統一。如果要用一個概念概括這種視覺結構的特點,那么非“張力”莫屬。
什么是張力?按照康定斯基的闡釋,藝術是以激蕩人類靈魂這一內在需要原則為基礎的。色、線、形等造型語言是內在精神和諧的形式因素,而語言內在的運動、張力等特質則是形式的內容或“內在聲音”。這些元素的聲音在再現藝術中是被遮蔽的,而在抽象藝術中得到自由、完整的表達。繪畫的元素是運動的實際結果,它有兩種形式:張力與方向。因此,作為視覺動態結構的一部分,張力是“元素的內在力量”。19
力的介入使畫面中的每一個元素都具有自己獨立的聲音和內在的色彩,從而成為活的元素。張力主要表現為藝術構圖中的對比原則。筆的輕重、疾徐,色的冷暖、明暗,點的疏密、張弛,線的粗細、曲直,面的虛實、動靜,這些都與藝術家試圖表現的內在情感與冥思相呼應,為觀者營造了一種詩意的境界。
以《戀曲》(2008)為例,畫面是兩條水平線與兩條垂直線構成的長方形色域。底(ground)為單一的藍色,深邃、寧靜;圖(figure)為紅、黃,熱烈、奔放。冷暖對比使畫面中的圖形閃爍著勃勃的活力。畫面上半部分的底被圖部分遮蔽,層層細涂的白黃紅浮動其上;而下半部分圖底交錯,藍色的正方形從表層錯落有致的暖色調中凸顯出來,與紅黃藍綠白等漸變的色調形成內在的韻律。粗細均勻、張弛有度的直線形成了趨暖的離心力,與藍色塊面趨冷的向心力,形成一種動態的張力結構,交錯婉轉,為觀者奏響了一曲溫暖而寧靜的戀曲。
再以《心不止,水常流1》(2015)為例,黃、綠兩種冷暖對比鮮明的色彩交錯暈染、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種內在的節律。底色的線描以水平線為主,如水中的漣漪,表現出冷峻而寧靜的基調。層層漸進的黃色從底色中脫穎而出,形成大小比例不同的五個類圓形色域,明媚而溫暖。每一個不規則的圓形都是內傾的、向心的;而圓形與圓形之間卻形成了一種離心的力。冷與暖、明與暗、離心力與向心力的相反相成,如夢如幻,形成了一種多聲部的和聲,熱烈而又寧靜。它可視、可聽、可感,足以激發觀者無盡的遐思與想象。
總之,精神的呼喚是形式的靈魂,走向抽象藝術的步伐必然伴隨著巨大的緊張與情感上的激動。它以內在對比的原則,讓形式的元素在動態的張力結構中發出美妙的旋律,形成了意蘊深遠的意境。這種意境超越了中國書畫傳統的寫意圖式和西方幾何化的抽象體系,進一步發展了趙無極、吳冠中、朱德群等人所開拓的詩性抽象。它以色彩與造型的和諧建構了一個純粹的精神世界,而這個精神世界又深深地植根于自我及其周圍世界的關系之中,帶有這個社會“不斷變化著的物質和心理條件的印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