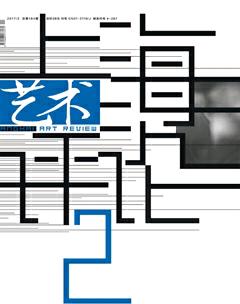快門開放的攝影 慢速觀看的藝術(shù)
盧茨?科普尼克+石甜+譯
一
對攝影的批判研究,很大程度上沿著加速軌跡而來,把快門的加速作為一種有效工具,剪輯時間的精彩瞬間,將過去時刻從遺忘之力中拯救。傳統(tǒng)主流觀點認為,技術(shù)成熟后,攝影師們突然對時間線性發(fā)展感到震驚;鏡頭快門的速度被用來打斷歷史的連續(xù)性,為了永恒而記錄單個時刻;通過捕捉關(guān)鍵時刻,抓住歷史轉(zhuǎn)瞬即逝中的痛苦暴力,卷入并戰(zhàn)勝時間的現(xiàn)代壓縮與加速。1936年,作為八種攝影理論之一,前包豪斯成員莫荷利·納吉(Laszlo Moholy-Nagy)提出,“將一段時間的疾速運動固定下來,實現(xiàn)慢速觀看;例如,夜間汽車從一條路上開過,車燈形成的發(fā)光軌跡:延時曝光。”莫荷利·納吉是現(xiàn)代節(jié)奏的激烈辯護者,他并沒有詳述攝影師怎樣實踐慢速觀看的藝術(shù),打破攝影的現(xiàn)代話語咒語、以關(guān)鍵時刻為基本原則。莫荷利·納吉把攝影作品從現(xiàn)代史的理論中解放出來,作為線性時間和關(guān)鍵時刻的辯證合一,正如他指出的,接受慢下來的可能性,作為現(xiàn)代主義審美實踐本身的一個合法基礎。
本文通過探索兩位當代攝影師的作品,探討莫荷利·納吉關(guān)于慢速觀看的理論,他們的作品不僅依靠延長曝光時間,而且追尋捕捉后工業(yè)時代的遠景,交通、速度、移動和燈光等工業(yè)主義文化的核心要素。在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和邁克爾·韋斯利(Michael Wesely)兩位攝影師的作品中,快門打開技術(shù)的恰當運用(曝光時間從幾分鐘到幾年),提出了本質(zhì)問題,關(guān)于我們?nèi)庋塾^看模式、攝影的本質(zhì)、攝影師身份的限制,攝影作品中運動、空間、時間銜接等內(nèi)容。雖然致力于捕捉不同物體和人群,兩位攝影師關(guān)注攝影的標志特征,我們見證的不僅僅是人類肉眼所不能看到的事物,而是攝影轉(zhuǎn)化為表達不同時間邏輯和矛盾持續(xù)體驗的一種藝術(shù)。
二
在最近150年里,關(guān)于時間體驗標準化的最重要體現(xiàn),除了工廠汽笛和流水線生產(chǎn),電影院和火車旅行很可能脫穎而出。19世紀下半葉,在歐洲和北美,鐵路線不斷增加,帶來巨大壓力,要求甩開地方時間,在固定的運行時刻表和同步時鐘的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1900年左右,移動畫面的技術(shù)構(gòu)造并沒有要求電影必然會在幾十年內(nèi)變得對觀眾有意義;早期拍攝條件還是相當即興的。到了上世紀20年代后期,“聲畫同步”征服了電影院,電影本身正規(guī)化,一部電影應該持續(xù)大約90至120分鐘,并應該以標準幀率放映。正如讓·呂克·戈達爾(Jean Luc Godard)的名言,電影當然是每秒24幀。它能夠娛樂、分散注意力、揭示、拯救,并產(chǎn)生洞察力,尤其因為電影的畫面和聲音對觀眾來說是可預測的,而且從這個方面來看,還是線性時間形式。
可預測性和標準化的某種感覺,似乎也促使日本攝影師杉本博司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拍攝不同國家的電影劇院內(nèi)部。所有這些攝影圖片都是由同一理念所激發(fā):在一整部電影播放過程中,勾勒出屏幕;更精確地說,描繪一部電影的整個過程,從而產(chǎn)生關(guān)于大銀幕的攝影圖像——由于燈光的不同強度、持續(xù)不斷地反射——最終會變成一片空白;盡管有神秘的熾熱,還是一片空白。留白,但仍然塑造一種“太多了”的感覺。杉本所拍攝關(guān)于電影院的鏡頭,無論是在洛杉磯、紐約或東京拍攝,絕大部分都是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豪華影院殿堂里:這些建筑殘存是電影消費經(jīng)典時期的建筑,電影從無聲到有聲;去電影院看電影,仍然有一種面對機械復制圖像奇跡的快感。所有鏡頭都是從一個中心視角所拍攝。除了少數(shù)以外,大部分攝影圖片中,屏幕發(fā)光部分不會超過圖片空間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這樣,我們還可以欣賞影院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這些宮廷繁復紋飾往往看似反射屏幕的白光,但同時作為一個框架,讓這種白光發(fā)散出來。在這些攝影圖像中,我們看不到任何觀眾身影,任何被現(xiàn)代娛樂業(yè)的迷人窗口所吸引的任何觀眾。
杉本博司拍攝的那些華麗影院中,經(jīng)典敘事電影對觀眾來說似乎是一扇透明的窗口,讓我們體驗別人的生活,成為其他人,夢想著另一個現(xiàn)實,經(jīng)歷我們英雄的命運。但它也試圖把觀眾的時間體驗融入到電影的有效編排敘事動力中,在以角色為中心的故事因果鏈中,通過重建我們對時間的感覺,沒有留下任何空間讓我們?nèi)ゾ幙椬约旱墓适拢胂蟛煌臄⑹虏ㄕ郏蛑皇窍硎芘既弧⒉豢杀容^的景象。杉本博司總是把我們留在電影的黑暗之中,他的鏡頭轉(zhuǎn)變成神秘發(fā)光矩形的那種黑暗,我們想要觀看別人的生活、夢想和痛苦,屏幕讓我們沮喪。然而,在這些攝影作品中,屏幕的光韻——令人驚訝的此時此地,亮度的此時此刻——源于杉本博司完全熟練技術(shù)操作、企圖推翻布列松所謂的獨特和重大時刻。這一系列的攝影作品,剛開始出現(xiàn)是深奧和費解的,杉本博司的作品中不可能沒有理論推動、邏輯嚴謹和精確度。在瓦格納的《帕西發(fā)爾圣杯》(Parsifal)中,時間似乎變成了空間,但不應讓我們認為,我們像擁有物體一樣能夠擁有空間化的時間,像獎杯一樣把它裝進我們的口袋帶回家。空間是且仍像時間流一樣難以對付。
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在1926年說過,杉本博司的攝影作品帶回了我們渴望的電影院,“優(yōu)雅的表面光彩,是這些大影院的標志。像酒店大堂,是愉悅培養(yǎng)的圣地;它們的魅力在于熏陶。”2正是現(xiàn)代愉悅被提到崇拜和迷信的高度,像克拉考爾繼續(xù)討論的那樣,主流商業(yè)電影會搶走它的有意義和潛力的現(xiàn)代娛樂,即讓觀眾認識到在世俗化、時代異化和碎片化的切身體會。在克拉考爾看來,這些高度風格化的內(nèi)部就像圣殿;他們邀請對娛樂產(chǎn)業(yè)的現(xiàn)代迷戀進行朝圣,20世紀文化產(chǎn)業(yè)如何經(jīng)營這些完全是自我介紹的鏡頭,如何承諾將我們從日常生活的平庸中拯救。
上世紀80年代初,克里斯蒂安·麥茨(Christian Metz)指出,攝影比電影更適合成為迷戀偶像,它把似乎擁有神奇性質(zhì)的物品擴散,要求我們無條件熱愛,讓觀眾參與到替代的誘人過程3。根據(jù)麥茨的說法,原因有三:首先,由于攝影相對較小,無需持續(xù)一段時間的前序認知,攝影圖片讓觀眾的目光揮之不去,隱秘地把觀眾當作欣賞行家,因此——不同于電影的強迫觀看時間——讓他們?nèi)谌牒捅粏蝹€細節(jié)所打動;第二,電影讓觀眾沉浸在動感中,而攝影的代表邏輯本質(zhì)上是靜止和沉默的,削弱永恒感,與無意識和記憶相媲美;第三,攝影定義了框架(frame)和非框架空間的界限,從根本上不同于電影,電影與可見和不可見有關(guān)。電影的非框架是實質(zhì)性的,即有某種出現(xiàn),形成我們的知識和識別;攝影的非框架是巧妙的,拒絕進入到拍攝對象中,也不理睬。作為連續(xù)設計和鏡頭動作系列,電影讓我們看到可見的世界,是正在進行的連接、故事和變化。另一方面,因為不能去掉時間中非框架空間一開始就有的排斥,攝影捕捉了過去的存在,似乎保存了隨死亡而消失的記憶。正因為攝影圖片抵抗變化和重構(gòu)策略,我們會珍惜它,就像一個魔力庫、一個超自然物體,代替我們感知和記憶的普通機制。
杉本博司關(guān)于影院的攝影作品,把觀眾“懸掛”在攝影的靜止、陰郁、一成不變,與電影強調(diào)的活力和變化之間。這樣一來,這些攝影作品讓我們重新思考機械復制和迷戀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雖然高度關(guān)注框架問題,杉本博司的長曝光作品讓觀眾重新考慮屏幕框架的力量,它主宰了攝影作品的中心。杉本博司的慢速結(jié)構(gòu)同時關(guān)閉和打開。攝影融入電影中,就像電影似乎有助于推動攝影超越自身的表現(xiàn)邏輯。因此,這些攝影作品基本上修訂了接收和解讀的不同時間,它們分別與攝影和電影的媒介有關(guān)。杉本博司的攝影作品在一個看似靜止圖像的空間中,引出整部電影的時間,讓我們擺脫任何想把攝影或電影當作由單向時間邏輯所組成。攝影將影片當作一種極其緊密和神秘超驗的媒介,而電影以這樣一種方式激活攝影作品:它超越自己的潮流,成為一種崇拜。如果說主流攝影的時態(tài)是過去完成時,堅持一些行為在過去已完成;如果說敘事電影的時態(tài)是現(xiàn)在完成時,將過去的一部分積極地進入現(xiàn)狀;那么,杉本博司的影院作品則區(qū)分不同時間軌跡和物質(zhì)性,當它們表現(xiàn)了什么和我們?nèi)绾斡^看時,我們沒法當作一個單一時態(tài)。不是探索一個已經(jīng)了結(jié)的世界,也不是不耐煩地把我們推進未來,杉本博司的攝影作品把過去的存在作為一個擴展的當下,在它的空間中,現(xiàn)在我們可以享受正常時間感逝去的樂趣。1910年,布拉加利亞關(guān)于打字員和大提琴手的打開快門攝影中,以疾速未來之名抹去當下;在時間流逝中,杉本博司慢下來,為了說明不同時間和方向相遇于我們所說的當下,作為基礎去定義我們之所以為當代。
三
邁克爾·韋斯利出生于1963年,在慕尼黑美術(shù)學院(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Munich)學習,為了反映后冷戰(zhàn)生活的建筑,他通過重新調(diào)整攝影器材、練習改裝相機,想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流逝的時間與當下景觀的關(guān)系。韋斯利的作品包括在羅馬宮殿(1995)和東德景觀(2002-1004)的狹縫(slit-lens)鏡頭照片,把自然和人造環(huán)境變?yōu)槌橄蟮摹⑺胶痛怪钡纳珟В?0世紀著名建筑師們在他們作品前或在他們辦公室前的肖像照,由于長曝光時間,無法識別具體的身體特征;諸如20世紀90年代柏林大規(guī)模重建的波茨坦廣場,2001-2004年間紐約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改造項目等建筑工程的照片,韋斯利通過打開好幾年的相機快門,創(chuàng)造一種舊與新、靜止與動態(tài)的復雜層次;以及整個比賽期間的德國、歐洲和南美足球場(2005),顯示出尖銳焦點(sharp focus)中的建筑結(jié)構(gòu),看臺上的球迷作為模糊色帶,而球員正在球場上跑動,因而變得從視野中消失了。
具有韋斯利理念的作品中,或許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作品:用打開快門拍攝德國、奧地利和東歐火車站的系列作品。這個系列的基本理念相對簡單;它的現(xiàn)象學、美學、政治意義卻非常復雜。在這些作品中,攝像機被固定在各個火車站站臺(布拉格、柏林、慕尼黑、漢堡、漢諾威),它的鏡頭對準離開火車,就像在某人的眼里,這個人正在跟一輛車上的朋友道別。不過,不是把發(fā)車的關(guān)鍵時刻獨立出來,韋斯利的相機快門一直打開,直到五、七或十小時后火車到達預定目的地:布達佩斯、林茨或慕尼黑。韋斯利的長曝光效果是驚人而不可思議的。我們看到了,通過前景中旅客身影看過去,長椅清晰可見,上面還有旅客等待的微弱痕跡。我們看到了,在曝光時間內(nèi)許多路過的火車所留下的、左右光影模糊的條帶。我們看到車站的鐘,其數(shù)量在完美的焦點中展示,由于持續(xù)的運動,指針完全看不見了;我們看到靜止的到達標志,表明了攝影師所在位置,移動的離開標志沒有顯示任何目的地,因為它們從來沒有足夠的時間,在韋斯利的慢速底片銀鹵化物鹽上留痕跡。我們看到布拉格和漢堡火車站令人印象深刻的結(jié)構(gòu),甚至柏林火車站至少都細節(jié)豐富,它們是紀念碑,表明了高度工業(yè)化怎樣運用玻璃和鐵這樣的人工材料,來適應持續(xù)流動性的現(xiàn)代路線。盡管很好,然而因為這些圖像的長曝光時間,我們辨認不出是白天、黎明或黃昏。無論我們是乘坐火車度過夜晚或白天抵達,韋斯利的火車站總是沐浴在相同的光線下,彌漫的、無名的,完全均勻的光亮。
除此之外,在韋斯利所有攝影作品中,我們看不到離去的火車本身,它的離開引發(fā)快門按下,它的離開給這些攝影圖片標注名稱和坐標。通過對同一張圖像中不同動作和持續(xù)時間的分層,開放式快門攝影成為一種減法藝術(shù)。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被看作是從緩慢和慢速中減去快速和激情。更準確地說,它把時下交通與連接的風馳電掣融入到持久與永恒經(jīng)緯中,不是為了支持后者而隱藏前者,而是為了提高我們的意識,辨別在鐵幕結(jié)束之后形成解散景觀的速度和時間。正如我們在20世紀初布拉加利亞的圖像動態(tài)化中看到的,開放快門攝影無疑可以走向抽象,以不變和原型的名義,去消除偶然性和流動性的標簽,韋斯利關(guān)于火車站的攝影作品,揭示了過去、現(xiàn)代和未來,此處與彼處的奇妙同在,其影響來自柏林、布拉格、布達佩斯、慕尼黑等城市在歷史轉(zhuǎn)型時期,作為物質(zhì)和象征交換新網(wǎng)絡的一部分。似乎缺乏特殊時間,才是這些圖像的精確時間和歷史指標。時鐘消失的指針是歷史的日晷,喚醒的既不是工業(yè)城市、也不是國家或冷戰(zhàn)時政治集團提供界限定位,可以確定當下的日常生活安排。所有的數(shù)字都無法告訴我們這個時間,韋斯利的神秘時鐘見證當?shù)馗艚^觀念的歷史時刻——統(tǒng)一身份,劃定地區(qū)和特別體現(xiàn)——這些都不再出現(xiàn)了,因為在前蘇聯(lián)解體后,作為交流、合作和文化生產(chǎn)的主流結(jié)構(gòu),網(wǎng)絡的開放和快節(jié)奏形式出現(xiàn)了。
20世紀90年代初,邁克爾·韋斯利的快門打開攝影作品,探索了當代失調(diào)過程,并不是呈現(xiàn)它的基本癥狀,而是作為審美體驗和正式試驗的催化劑。韋斯利的攝影作品并沒有完全否認當下強制連接的窒息速度,而是鼓勵觀眾同時融入/被融入到全球的去疆域化中。失調(diào)成為一種美學策略,揭示多種速度、持續(xù)時間和時間性的活躍共存;推動攝影媒介走向甚至超越它的限制。韋斯利攝影作品的出現(xiàn),是一種深刻的擴大,從把“流動性”僅僅定義為直線運動的動力中拯救出來。激發(fā)這些攝影作品的是它們的探索,正在位移的運動和行為多大程度上構(gòu)成我們對地方和位置的理解;沒有“遠”,就沒有“近”,任何“現(xiàn)在”都是未來的過去式,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過去和現(xiàn)在,未來也永遠不會來。韋斯利的攝影作品記錄了“空間”作為離開、通過和到達的開放式動態(tài)。如果我們不考慮任何特定時刻是獨立的(雖然各種的軌跡和路線穿過它),是一個自洽的時間靜止片段;這樣的話,漢堡有跟慕尼黑一樣的潛力。韋斯利展示了空間作為不同動作和過程的一種異質(zhì)性,作為混亂開始、沒有結(jié)束和正在進行故事所構(gòu)成的動態(tài)形貌。與冷戰(zhàn)的意識形態(tài)相反,這個空間永遠不能被定義領(lǐng)土邊界和有限國家敘事的手段占有。它不再形成一個完整的同步性,即排除不可預見的鏈接,松散的線索和令人驚訝的禁忌(某種編織節(jié)點的失敗)后,定義并建立所有的關(guān)系和連接。在韋斯利的打開快門攝影中,空間反而出現(xiàn),用多麗·馬西的話來說,作為“動態(tài)的同步性,不斷被新來者斷開,時刻等待被新關(guān)系構(gòu)建的確定(因此總是不確定)。它因此,總是被制造,某種意義而言,它是未完成的(除了‘完成并不是目標)。”4
韋斯利的攝影作品中,局部模糊促使我們注意到逃出我們視線的東西。它使我們慢慢觀看,從而擴大我們的當下,不是脫離強烈過去地方認同和懶散時間表的懷舊渴望,也不是為了身體與世界分裂、帶我們?nèi)ヒ苿由砩眢w和感官經(jīng)驗。相反,在一個無限連接的世界,“緩慢速藝術(shù)實踐”指的是,認識到感知身體已經(jīng)有了一些基本的技術(shù)基礎;相機不是把生理身體提升到幻影(apparatical)或渲染幻影自然的高度,而是通過讓有機體與時空環(huán)境之間產(chǎn)生新的連接,幫助拓展人類的經(jīng)驗;因此,在我們快速改變和信息加速的時代,對當下延伸的虛擬,不僅僅是某種特殊效果的產(chǎn)物,而是可以成為唯一可見的,因為虛擬化行為是我們身體經(jīng)驗的組成部分,以我們通過/在時間中的移動為開始5。韋斯利的攝影作品,成功擴大當下的空間,不是因為他們用人類去交換機器人的眼睛,相反,它依賴的事實是,人類具體化不能不(秘密或直接)熟悉當下網(wǎng)絡交織中的時間互動和虛擬重疊。如果沒有這個事實,我們永遠不會完全在家里,在一個靜態(tài)的當下,可以占有像物體一樣擁有我們的身體。事實上,我們只是我們生理身體的監(jiān)護人,因此需要考慮我們感官系統(tǒng)在時間中的位置,僅僅作為多種時間體驗的一個交匯點、一個媒介6。
四
杉本博司和韋塞利的攝影作品系列中,讓我們用一個開放問題提問,他們怎么看人的身體和能動性的地位。杉本博司和韋斯利的慢速觀看藝術(shù),確實可能導致傳統(tǒng)人文學科的邊界瓦解。一個蓄意技術(shù)操縱和概念干預的作品,旨在提高或調(diào)整生理身體與外在器械的某些操作,讓我們感知視力所不能及的事物。尤其在把特殊效果當作工具,可以重新訓練人類的感官知覺、增加生理經(jīng)驗新形式方面,杉本博司和和韋斯利的慢速美學打開一扇窗口,以更豐富、更不同的感官面對我們周圍可見和不可見的世界。他們作品所追求的慢下來,把觀眾從任何單一維度的進步和融合中拯救出來,幫助我們探索感覺經(jīng)驗的開放、時常模糊時期,后者形塑了我們當下的視野。慢下來,遠不是從攝影圖像中抹去人類具體性、重復晚期資本主義物化傾向,而是提供了一種開放的、具體化交織中的交叉,我們可以在真正當代性的模式中體驗當下,也就是那些原本模糊、多樣性和無法控制的,使我們認識到感官不確定性,是特殊和自由的引擎。
杉本博司和韋斯利的慢速觀看技術(shù),無疑導致記憶的有機形式進一步解體。但是,他們的作品同時讓我們直接凝視我們自己的開放當下,它鼓勵觀眾積極地問自己——帶有一絲猶豫和考慮——我們可能會想把怎樣的過去帶入未來,我們高興留下怎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