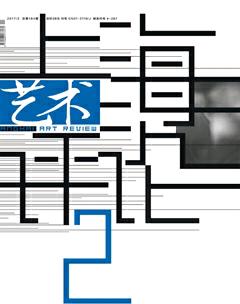《畢業會考》:后冷戰時代東歐中產階級的心理癥候
王昕
《畢業會考》是羅馬尼亞導演克里斯蒂安·蒙久1第三部在戛納電影節獲得重要獎項的影片。在《四月三周兩天》摘得金棕櫚(2007年),《山之外》榮獲最佳編劇、最佳女演員(2012年)后,他又憑借此片拿下了最佳導演獎(2016年)。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獲得生產藝術電影等級的戛納的再三肯定,蒙久依靠的不只是羅馬尼亞新浪潮的“電影語法”,2更是他不斷變換的題材——既維持在西歐視域中想象和曝露羅馬尼亞問題的距離,也在復雜性的遞進中與更普遍的歐洲關切發生共振。
《畢業會考》正是蒙久頗具智慧的題材與敘事選擇的最新版本,不同于《四月三周兩天》嚴酷歷史情境中的墮胎故事、《山之外》里有異于城市的修道院空間,《畢業會考》坐落的時空與情境都更接近于影院觀眾的日常經驗。故事的起因是一個羅馬尼亞中產家庭的女兒在畢業會考前遭遇了未遂的性侵襲擊,手臂受傷的她可能無法按時寫完答卷,而能否獲得9分以上的平均分是獲得英國大學獎學金的條件。而影片的核心事件則是女孩的父親(醫生羅密歐)違反原則幫助需要肝移植的副市長在等待名單上“插隊”,以此換取副市長向考官“打招呼”(在改卷時對做記號的試卷加以照顧)所引發的系列問題。
當我們對影片進行這樣的概括,凸顯出的人情、原則、考試/升學等要素,不免讓人聯想到中國。平日里恪守原則、敢于擔當的父母,一旦面對子女的升學問題,便可能陷入人情與原則的天人交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父親因為小四只考上建中夜間部希望復查試卷而與人爭執不下,2016年的金馬獎最佳影片《八月》里“不能低下高貴的頭”的父親為了兒子能上心儀的中學而與母親一起托關系宴請了學校負責人。子女的升學在這些情境里寄托著一個家庭對于未來的想象,它是一個標識個體成長的明確形式(畢業、錄取),也以清晰的等級(學校的好壞)預言著希望的多寡。然而不同于這類具有普遍性的“望子成龍”,《畢業會考》中的考試被賦予了遠為決絕的含義。父親羅密歐所期盼的是女兒伊萊扎通過這場考試(基于此的獎學金)斬斷與家鄉羅馬尼亞的聯系,拋棄這個在他看來已無可救藥的國家,去“更加文明”的英國展開自己的人生。換言之,羅密歐將這場考試視作女兒逃離羅馬尼亞的唯一機會,而羅馬尼亞也被他指認為一個必須要逃離的國家。在影片的發展中,觀眾則獲得了反思這種心理癥候的機會。
逃離與回歸
事實上,逃離羅馬尼亞尋找理想的彼岸并非什么新鮮的話題,保加利亞電影學者亞歷山大·亞納基耶夫指出在冷戰時代“離開巴爾干地區的想法整日縈繞在許多人的腦海中。他們希望在遠離熟悉的本國本土的另外某個地方找到一切事物都完美并受祝福的天堂。”3《畢業會考》中伊萊扎的父母就是在齊奧塞斯庫統治時期逃離羅馬尼亞的,他們一直在國外生活到羅馬尼亞發生劇變后的第二年(1991年),在那個冷戰終結塵埃落定的時刻才決定回國生活。然而這場后冷戰時代的回歸,卻在如今被羅密歐稱為“一個糟糕的決定”。曾經懷有萬丈豪情,想要在羅馬尼亞力排眾難、讓事情有所轉機的羅密歐,如今認定自己什么也沒能改變。出于最深的絕望,他要求女兒將自己的人生經歷當做教訓,并對她發出了“逃離”的指令。
羅密歐對羅馬尼亞的絕望程度堪稱一名堅定的“已完黨”,在一次談話中他對女兒說,“相信我,但凡有任何能用來改變這個國家的方法,我都會極力勸你留下來為之奮斗,但我們留下來就夠了。” 在他的心目中作為彼岸的英國有著比本地更強的真實性——“當你置身肯辛頓公園,有小松鼠和你追逐嬉戲的時候,這里的一切都會顯得很縹緲了,你還會懷疑它是否是真的。”
如果說冷戰時代的逃離,是基于兩大陣營對壘的國際國內形勢,是一種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選擇,那么在資本主義陣營大獲全勝、失敗者擁抱勝利者邏輯的后冷戰時代,又為什么需要如此決絕的逃離?影片通過主要情節設計和細節交代,給出的理由是這是一個不遵守秩序、無法公平競爭、依靠人情和關系網絡運作的社會。與這個理由恰可以形成對話的是同屆的金棕櫚得主《我是布萊克》,肯·洛奇講述的故事正好發生在《畢業會考》設定的“彼岸”英國,在這個羅密歐想象中更加文明的國家,辛勞工作了一生的木匠因為不容人情、商業化的繁瑣行政程序而被踐踏了尊嚴與生命。
作為編劇和導演的蒙久對于羅密歐懷有的彼岸幻想的欺騙性也有著一定的自覺,當羅密歐把女兒遭受襲擊的原因歸結于本地社會時,他的警察朋友提醒他這是一個意外,在其他地方也會發生。而他的母親與妻子也都不贊同他將“出國作為萬靈藥”的執念(母親更是直言“你以為別的地方和這里有什么區別嗎”)。然而影片總體上還是依照絕望的羅密歐的心理圖景建構了問題叢生的社會環境。影片開頭被砸碎的窗玻璃、開車路上撞到的狗、汽車被擺弄過的雨刷、砸壞的擋風玻璃以及女兒遭遇的襲擊事件,這些不知何人所為和突然發生的暴力,與晃動的手持攝影一起形塑了影片不安全和不穩定的環境氛圍。而汽車內的手機鈴聲、警局背景音里不間斷的電話鈴聲、副市長辦公室和考試委員會主任家里的鈴聲,這些大多數時候不被接聽卻充斥著整個聲軌的音響,更營造了一種心理層面的持續焦慮。
這種視覺與聽覺上的壓力,能讓觀眾在邏輯并不充分的情況下接受以正直自詡的羅密歐不惜舞弊也要讓女兒通過考試的行為。而在更深層的文化邏輯中,《畢業會考》所調用的還是后冷戰時代所延續的冷戰結構。冷戰雖已結束,但戰勝與戰敗的陣營仍然清晰,社會觀念中形成的文化等級依然明確,作為戰敗國的成員想前往戰勝國獲得更好的生活是那樣的“自然與合理”。
然而不同于因為對本國失望、而退回到冷戰邏輯中的父親,伊萊扎想要做出的是自己的判斷與選擇。她是會重復父母冷戰時代的逃離,還是堅守父母冷戰終結時的回歸,影片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在經歷了昏暗影調籠罩的全片后,一種撥云見日的光亮出現在了最后的段落,并且不只灑在伊萊扎一個人的身上。
失控與成長
羅密歐之所以會有這樣內在的絕望,還聯系著他作為掌控者和承擔者的身份。在和影片四個主要女性角色(女兒、妻子、母親、情人)的關系中,他都居于父權結構派定的權力位置,也因此背負著這份權威肩頭的全部苦楚。為了擔起家庭責任,反感羅馬尼亞社會邏輯的羅密歐,不少時候卻是這種邏輯的執行者。
在勸說女兒給試卷做記號前,羅密歐與妻子先在廚房進行了一場談話。當妻子坐在餐桌旁、面對觀眾背對丈夫表示,自己明白公平坦蕩需要承擔代價、而她情愿承擔這代價時,在后景倚靠洗碗池站立的羅密歐反駁到,對方承受得起只是因為他處理好了每件事。當羅密歐的母親因病摔倒、伊萊扎闖入父親情人家中將他帶走為祖母急救后,在羅密歐母親家的衛生間里,羅密歐與威脅不再參加考試、情緒激動的女兒進行了另一場談話。“處理好每件事”被更直白地表述為“你甚至想象不到,為了讓你像這樣生活,我們不得不做些什么”。而當女兒表達了和母親相似的意見時(“如果是不對的,你就不應該去做。”),羅密歐則給出了最圖窮匕見的回答,“‘你不應該去做這句話說出來多容易。如果你沒有去上這些私教課,或是沒有參加這些比賽,你能去英國讀書嗎?”當羅密歐點明高等教育不過是一種階級秩序再生產的方式,英國這個彼岸是要靠一系列金錢和特權的堆積才能抵達的,他也就是在一種最實用主義的層面上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為了自己的家人能生活得“更公平”,只能參與這個不公平秩序的建構。那么也許影片中被砸碎的玻璃與車窗,并非是毫無緣由的。
為“從來沒要求幫助”的親人做好每件事,卻無法獲得她們的理解。羅密歐與家人情感上的疏離,從開車送女兒時兩人分坐的前后排,到與妻子在醫院和家中分隔的距離都有著清晰的展現。在和親人的關系中,他所依賴的是對物質生活和外部事件的掌控,而為了獲得這種掌控,就難免進一步卷入本地的人情網絡,因而某種自我仇恨也生產著或混雜在對羅馬尼亞的絕望中。
而影片的有趣之處在于它描繪了這個需要掌控力的男人喪失控制力的整個過程,并讓這種“失控”成了超越個人執念、獲得反思的契機。在影片的開始,襲擊事件讓羅密歐對女兒的未來規劃遭遇了失控的可能。面對這一情境,羅密歐在尋找挽救方法的同時,也拒絕將襲擊事件當做意外,這固然是出于一種“羅馬尼亞應該為一切糟糕事情負責”的心態,但更重要的是意外的存在是對自己能夠完全把握生活的否定。自己去追查監控、展開調查,是期盼能用一種有跡可循的方式重新獲得掌控。然而試圖舞弊的事件卻讓羅密歐的生活滑向了更加不可控的方向。也如他一直隱瞞的母親病情(對母親和家人都加以隱瞞),這些他基于利弊考量為別人做出的決定,一旦爆發都將導向失控的升級。
當檢察官告訴羅密歐他們一直在監聽副市長的通訊、知道舞弊事件,想以此換取對病人的訊問時,作為醫生的羅密歐拒絕了這種要求,同時也拒絕了警局朋友打聽試探的建議(“不要讓事情變得更復雜”)。而在他僅憑監控視頻里相似的衣著,就斷定女兒的男友在襲擊發生時在場卻沒有挺身而出,他與女兒的矛盾也徹底激化。在影片接近尾聲的部分,羅密歐喪失了對情人、妻子和女兒關系的全部掌控,“一切都是為了你們好”的獨裁終于難以為繼。而這種徹底的失控,卻也讓他從渴望解決所有問題卻不得的自我仇恨中解放出來,終于可以聆聽和尊重情人和女兒自身的意愿。“什么都沒能改變”的絕望背后是一種對全能自我的期許,而羅密歐的母親早已給出了反駁——“你已經改變了能改變的”,每個人也都只需改變自身能改變的。
當副市長心臟病發作去世,檢察官們第二次來到醫院時,羅密歐的助手用匈牙利語祝他好遠,匈牙利族是羅馬尼亞的少數族裔,而畢業會考(Bacalaureat)這個詞語的匈牙利語翻譯(歷史與未來
《畢業會考》中除了羅密歐與女兒、妻子的關系,最為重要的兩組人物是他的母親和他的婚外戀情人及其兒子。這兩組人物恰好攜帶著不斷在處理當下問題的羅密歐極為匱乏的歷史與未來。在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極右翼領導人勒龐在法國擁有高支持率的當下,對歷史的拒絕和對未來的絕望,是身處西歐、美國的中產階級與羅密歐這樣的東歐中產階級分享的心理癥候。而這導向的可能不僅是一人的逃離,也可能是一國的逃離,或對文化傳統、立國信念的背叛。
因為伊萊扎將要去英國讀書,祖母翻箱倒柜地尋找到了塵封著家庭歷史的相冊。不同于希望伊萊扎忘記家鄉的父親,祖母一點也不贊同孫女離開,而是希望她能夠在克盧日讀書。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羅密歐看望母親離開時,母親對他的請求和囑托——“把墓地的雜草清理一下,抹點水泥,那樣干凈些”,在對話中我們知道這是他之前就已經答應卻并不想做的事。這個只出現在對話中有待清理的墓地,透露著一段有待清理的歷史債務,以及一份仍被念茲在茲的歷史遺產。羅馬尼亞社會主義的歷史以及對這段歷史的葬埋,無疑留下了許多有待清理的墓地。2010年對墓地有爭議的齊奧塞斯庫夫婦所進行的開棺驗尸,所打開的重新討論和評價社會主義歷史的空間(例如2013年的羅馬尼亞電影《我是共產主義老太婆》),可能便是這種清理最為形象和極端的形式。
羅密歐父親的不在場(有待清理的墓地)、羅密歐自身婚姻的破裂和他婚外戀情人作為單親媽媽的身份,都凸顯了缺失的父親,而在父權制社會里這本就是某種歷史的缺失。影片在結尾的段落里,通過讓羅密歐照顧情人的兒子馬泰填補了這種缺失。而也正是在羅密歐與馬泰的相處中產生了幾個全片最值得玩味的場景。
在影片的前半段中,羅密歐是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做出給副市長打電話請求幫忙的決定的。而在影片的結尾當他帶著情人的兒子重新來到這個公園,有著語言障礙的馬泰卻把石頭扔向了不遵守規則的別的孩子。而在羅密歐與檢察官第二次交談結束,帶著馬泰走到醫院的樓梯口時,馬泰在一幅社會主義時期遺留的壁畫前望向了羅密歐,在畫中捧著書本、拿著試管的青年男女身上,男孩看到了醫生羅密歐的影子。而已經先走下樓梯的羅密歐,回轉頭來從馬泰的臉上辨認出他曾經懷抱的希望,而畫中的青年男女也仿佛和男孩有著相似之處。
在這一影片最為明亮的場景中,已經淪為壁畫/背景的社會主義歷史(羅密歐曾經認為葬送了就能迎來美好生活的歷史)好像在凝眸著他們。那段背負債務的歷史中蘊含的創造新人和新社會的力量也仿佛同時被激活。也就是說,這個想要達成送自己的女兒離開羅馬尼亞的任務的男人,在不擇手段卻屢遭挫折的過程中,透過女兒和男孩的目光依稀重新望見了自己曾有的目光,而那一目光也來自于歷史的深處。可以說整部影片都鑲嵌在該場景縱橫交錯的目光網絡中。
而絕望后重燃希望的羅密歐能否和這些孩子一起療愈問題叢生的本土社會,東歐乃至整個歐美世界的中產階級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歷史與未來,仍是一個有待打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