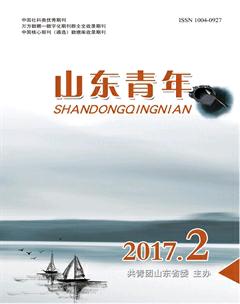中國情法之辨
郭于會??
摘要:前些年,“親親相隱”制度引起學界大討論,被當成封建糟粕為人們所詬病,但這種以倫理道德為基礎的價值規范不正彰顯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之處嗎?本文試圖從“親親相隱”制度談起,通過分析“家國同構”的忠與孝,延伸至現代社會,探討當今社會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
關鍵詞:親親相隱;道德;法律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以情為本的國度,一切皆離不開情:“人之常情”是情,“盛情難卻”是情,“通情達理”是情,“風土人情”也是情……而眾多情中,親情里的“親親相隱”制度源于先秦,貫穿我國法律發展的始終。先秦有“子為父隱”,漢代有“親親得相首匿”,民國有“對親屬不得提起自訟”等規定,“親親相隱”作為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而有別于西方之法。然而,法律的第一原則——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揭示了法律作為剛性的、鐵面無私的“規矩”,要求人們公平、公正、公開地對待人和事。那情與法到底該如何取舍呢?許多學者的觀點不一而足,因此情法之辨在我國一直經久不衰。下面來談談我國語境下的情與法。
一、“情”與“法”之涵義解析
首先,“情”指人之常情,也即倫理道德,涉及人的內心向度。在我國,“情”某種程度上更傾向于“家國同構”中的“家”,如對長輩的孝敬之情,同輩間的手足之情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此情的表現。擴展至整個社會,“情”更多通過道德行為外化出來,“道德是非強制性地調節社會關系的規范”,以善惡為評價標準,主觀性較強,因為善惡沒有具體的準則來衡量哪種行為是善,哪種行為是惡;也沒有具體規定某一行為到哪種程度屬于善,到哪種程度就變成了惡。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開篇所說,“每種技藝與研究,同樣地,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①他把善作為行為的目的,而我們把善作為評價行為的尺度。后又提到“幸福作為最高善”,那關于什么是幸福,又沒有具體的標準。“不同的人對于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也把它說成不同的東西……”②并且他不遺余力地列舉各種屬于善(德性)的東西:勇敢、節制、慷慨、誠實
……最后說:“善事物有兩種:一些是自身即善的事物,另一些是作為他它們的手段而是善的事物。”③由此可知,善并非無定論,但要界定善與惡,把握“適度”卻很難。因此,如何衡量“情”,如何判定親人間的“情”合乎人之常情的“親親相隱”,又是難上加難。
其次,“法”即法律,是國家機構制定的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外化為具體的條文規范,以強制性措施來規定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有明顯的導向性。“法”毋庸置疑就是“家國同構”中的“國”。“法”時常給人以冷冰冰的印象,內容多是禁止性規范,多以否定口吻來規定人們不準做什么,為人們設置了一個框架,框架內的行為合法,越界的行為非法,明確指出對與錯的邊界。
由此看來,“情”與“法”在形式或內容上都難以達成共鳴,甚至針鋒相對:道德以人內心的主觀信念為出發點,外在形式多為社會習俗,是軟性規定;法律以社會普遍意志為出發點,外在形式多為客觀公正的規章制度,是硬性律法。然而無論是不講情面的“法”,還是人之常情的“情”,本質上都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具體來講,情理上的“善”其實就是價值判斷中的“應該”,“惡”就是價值判斷中的“不應該”。而法律把哲學上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融為一體,即“對”與“應該”是同義的,“錯”就等同于“不應該”。因此“情”與“法”就統一了。
二、“情”與“法”之關系辨析
從古至今“情”與“法”并非水火不容。但在古代,道德法律化趨勢更明顯。傳統社會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道德中的“親親相隱”制度。
漢董仲舒推行“獨尊儒術”措施,開始了儒家倫理和傳統法律融合的進程。“情”在先秦時期,表現為孔子提倡的“仁”,主要重視人與人相處的規范。“先秦倫理主要是一種宗法倫理、家庭倫理,但也初步顯示政治倫理的色彩。”④兩漢時期,“情”最突出表現為“孝”,極大促進了“親親相隱”制度的發展。統治階級提倡以“孝”治天下,推行“舉孝廉”制度,且不論這種將“情”硬化為“法”的做法對子女而言有道德綁架之嫌,單講其后果就危害極大。在此影響下,以法令形式頒布養老令,孝文化促使子女極度維護父權,進而使父母擁有極大的權力,以致最終形成親親得相首匿法。以情入法,以孝制法,顯然將“情”極端化了,說明“情”對傳統法律產生的影響之大。“法”是“情”的實現形式,這里的“情”已經異化。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情”主要表現為“禮”,情法融合的特色就是以禮入律。晉律首立喪服制度,對違反喪服制度尊卑之間的行為進行量刑。由于統治階級多為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緣故,對長不孝即為對國不忠,這樣就把禮與法交融起來。在這種融合中倫理道德與傳統法律是不對等的狀態,“情”居于主要地位,對“法”有深刻的影響,一定程度上涵蓋甚至吞噬了“法”;而傳統“法”居于弱勢地位,淪為維護封建道德的工具,被動受到“情”的熏陶。至此,“道德法律化”、以“情”為“法”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由于這種源于血緣的“情”重于源于公理的“法”,因此“親親相隱”制度也就順理成章地盛行直至近代。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情”與“法”轉變為高要求與底線的區別——道德是教導人做好事,法律是要求人不作惡。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里的“人人平等”就暗含著“法不容情”的意味,不論是陌生或熟悉,不論敵人或親人,都必須拋棄一切“情”按照事先制定好的制度來依“法”行事。加之作為四端之情的惻隱之心似乎越來越缺乏,人們變得越來越冷漠。施韋澤曾說“道德的大敵是麻木不仁”。2010年河北省高院研究通過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中關于親人舉報即可減刑的規定雖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但從側面說明了“法不容情”已經到了一種極端地步。由此看來,當今“法”的地位高于“情”,“法不容情”優勝于“親親相隱”。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不斷變化發展。人是有感情有溫度的,滿足正當情感需求是必要的,因此不可能存在不容情的“酷法”。法律是底線的道德,隨著人們道德素質的提升,法律道德化是必然趨勢,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三、“情”“法”沖突之我見
法律關注的是人的行為后果,道德更多關注人的內在追求與主觀動機。因此二者必定會存在一定的沖突。劉云林老師曾在《公民情感的法律確認》中指出,“人的本能要求人們以家庭和親情為重,信賴家庭,依賴親情。”⑤而法律卻規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面對這兩難境地,該如何抉擇?
在我看來,道德與法律應該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法律必須是有人情味的法,而非冷冰冰的條令;道德應該作為法律的基礎和補充,為法律指明方向,凈化人的內心世界。二者都是維護公平正義,“親親相隱”為了家庭和睦,是人的本性要求;“法不容情”為了社會正義,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因此,在構筑法治社會時,要高度重視倫理道德的應有地位,處理好“親親相隱”與“法不容情”的關系,使“硬性的法”內化為“軟性的情”。
[注釋]
①亞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譯注:《尼各馬可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頁.
②同上,第9頁.
③同上,第15頁.
④劉紹云:“儒家倫理思想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影響”,《理論學刊》,2003年第6期,第33頁.
⑤劉云林:“公民情感的法律確認:立法倫理的應有視域”,《倫理學研究》,2007年第4期,第39頁.
[參考文獻]
[1]劉云林.公民情感的法律確認:立法倫理的應有視域[J].倫理學研究,2007(4).
[2]劉紹云.儒家倫理思想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影響[J].理論學刊,2003(6).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