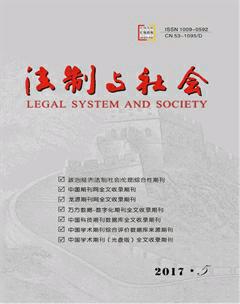論受賄犯罪的域外考察與取消為他人謀利的要件
摘 要 一方面,該要件的設置不僅在法理上存在爭議,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認定難的弊端。另一方面,該要件的設置也提高了受賄罪的入罪門檻,客觀上不利于構建清廉的社會風氣。因此,本文擬通過對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并結合國外相關理論規定進行對比,最后結合我國相關理論和司法實踐需要提出對策即取消該要件。
關鍵詞 受賄犯罪 域外考察 謀利
作者簡介:渠永超,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干部,研究方向:刑事法學。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004
一、域外關于受賄犯罪的規定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每個國家或地區對受賄罪的規定都不盡相同,在該罪的構成要件上大致有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將“為他人謀取利益”設置為受賄罪的入罪要件。此類規定僅存在于個別國家的立法當中。如俄羅斯、蒙古、巴基斯坦和意大利等少數國家。例如,俄羅斯刑法第290條關于受賄罪的規定:“公職人員為了行賄人或其被代理人的利益而實施屬于其職權范圍內的行為(不作為),因而親自或通過中間人收受金錢、有價證券、其他財產或財產性質的利益等形式的賄賂的,處……”。 該規定中“為了行賄人或其被代理人的利益”即是“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除此之外,蒙古、巴基斯坦、意大利等國刑法關于受賄罪的規定中也有“為了自己或任何其他人”、“為了行賄人的利益”等要件的設置。
除了上述部分國家將“為他人謀取利益”納入受賄罪構成要件以外,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從受賄犯罪的本質特征和建設清正廉潔的政府目標出發,在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中并未設定該要件,此舉使受賄罪的入罪標準設定的更低,客觀上卻起到了使公務人員更加廉潔自律的目的。例如日本、德國、美國、瑞士、丹麥、新加坡、奧地利、韓國、法國、匈牙利、泰國等大部分國家和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如《匈牙利刑法》第251條規定:公職人員利用自己職務上的地位索取或收受賄賂或接受賄賂的承諾,構成受賄罪。《日本刑法》第197條也規定:公務員或仲裁員,關于其職務實施不正當行為或不實施應當實施的行為,收受、要求或約定賄賂,是受賄罪。 此外,我國香港地區的《防止賄賂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在入罪標準上也沒有設置“為他人謀取利益”。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立法上,“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沒有被納入到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中。
有所不同的是,大部分國家的受賄罪構成要件中雖然并未將“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納入其中,但是其中一些國家和地區將受賄罪根據行為方式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劃分,分為受賄并實施了違反職務要求的行為和受賄但沒有實施違反職務要求的行為。在刑罰設置上,兩者相比,前者的行為方式處罰的更重一些,這種定性不定量的立法模式,使得受賄罪的規定更加精細和便于操作。如韓國刑法規定:現職公務員或者仲裁人實施與其職務相關的受賄行為的“處五年以下勞役或者十年以下停止資格”。對于即將擔任公務員或仲裁員而實施與其職務相關的受賄行為的“處3年以下勞役或者7年以下停止資格”。 綜上所述,從世界范圍內來看,降低受賄罪的入罪門檻,提高對公務人員的廉潔性要求已經成為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主流做法,這既是受賄罪發展的趨勢,也是建設公正、清廉的政府的現實需要,同時也與現代刑法中關于受賄犯罪的理論相符合。
二、筆者建議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
(一)使受賄罪的法益能夠更好的得到保護
首先,受賄罪的本質特征在于公權力和私利的交換,通過這種交換雙方實現了彼此對利益的追求。在權力和私利對價交換的過程中,行為人收受賄賂的行為就已經侵害了自身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并且此種侵害具有不可逆性,之后受賄人實施的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承諾或者行為只是既遂后的結果而已。因此,受賄罪保護的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保證其不受侵害,而不是保護請托人所欲求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對先辦理請托事項,之后再經過一段時間或者很長時間收受賄賂的受賄犯罪行為進行有效的規制,否則實施或者許諾辦理請托事項的行為與收受賄賂的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將因時間的久遠等因素變得無法認定。
其次,國家工作人員作為公權力的行使者、法律的執行者,本身并無權力可言,只是天然的履行公權力賦予的職能和代為執行法律規定,因此,其理應廉潔自律,為人民服務。在此原則下,任何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在刑法上都是禁止的,都侵害了其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因此,無論是“先拿錢,再謀取利益”,還是“先謀取利益,再拿錢”,本質上都是公權力和私利的一種“等價交換”,都是為刑法所禁止的。此外,行為人收受賄賂時,無論客觀上是否有為請托人辦理請托事項的行為以及該事項所代表的利益屬性是否合法、還是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辦理請托事項的意圖或者打算都只能反映受賄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并不能改變收受賄賂的行為已經對該罪的法益造成侵害的既成事實。 所以,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賄賂的行為,即已完成了對法益的侵害。至于該要件存在與否,對行為人的行為定性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最后,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也能有效規制和威懾現實中存在的諸多的隱性賄賂,如所謂的“感情投資”、“禮尚往來”、“過節費”等現象。這類行為具有長期性、隱秘性,并且在行為當時并不當即提出請托事項,但是其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腐蝕卻是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因此,取消該要件能夠更好的打擊各類新型受賄犯罪行為,能夠更好的保護受賄罪的法益。
(二)使法律邏輯體系更加完善
從法律內部統一性的角度看,《刑法》第385條第1款關于受賄罪規定了索賄和收受型受賄兩種行為方式。在索賄的情形下,構成受賄罪只需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即可,明確排除了“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該行為入罪的要件。同時,在《刑法》第385條第2款規定的收受型受賄犯罪中卻沒有設定“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但是對于第385條第1款規定的具有相似行為方式或者相同本質的受賄行為,其構成要件卻增加了“為他人謀取利益”,這種雙重標準明顯縮小了受賄罪的法益,更模糊了對其保護的一致性。相反,如果取消這一要件將其作為量刑情節,則能夠使三種行為方式得到有機統一,使其保護的法益范圍也具有一致性,從而實現受賄罪規定的內部統一。
(三)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
從上述分析可知,“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著認定難以及對隱性賄賂難以規制的弊端,因此,取消這一要件能夠很好地解決這一現實問題。當然,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并非簡單的取消了之,還應當照顧社會的一般人情禮節,確保國家工作人員合法、自由地接受贈與、饋贈的權利。具體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從饋贈雙方之間的關系進行判斷
通常情況下,正常的、合法的饋贈基本上是出于饋贈人和受贈人之間的親屬關系或者深厚的友誼,兩者之間通過這種正常的來往以實現加強彼此之間情感或友誼的目的,這種正常的贈予、饋贈與雙方的身份、職務并無必然聯系,并且不會有謀取利益行為的出現。相反,賄賂行為則是雙方基于利益關系,即國家工作人員所具有的身份職務和職權與請托人所謀求的利益之間具有的實質性聯系所實施的“權錢交易”、“權物交易”,并且這種往來會隨著行為人身份職務和職權的變化而變化,甚至逐漸淡化或消失。因此,對于此種來往,要從贈與行為與受贈人在職務上是否具有關聯關系進行甄別,最后再結合收受財物的行為進行判定。
2.從饋贈的行為方式來判斷
一般情況下,在饋贈、贈與行為中,贈與物的價值與贈與人、饋贈人自身的經濟條件和當地的風俗相適應,其行為方式大多數情況下是非隱秘性的。而受賄本質上是公權力和私利的“等價交換”,請托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賄賂物的目的就是期待對方在當下或者以后提出辦理請托事項的時候,行為人能夠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提供幫助或者是為了酬謝行為人已經為其辦理的請托事項。由于受賄行為為刑法所禁止,雙方為確保安全,通常會選擇隱秘的方式或場所來實施。在此情形下,司法機關應當在準確把握犯罪構成的基礎上,對合法的贈予、饋贈進行區別,通過對行為方式的公開性、雙方關系的遠近和饋贈、贈予數額的合理性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最終判定該行為是否為受賄。
注釋:
張理恒.受賄若干疑難問題認定之解析.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6).8.
張明楷.論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政法論壇.2004(9).4.
劉勇.淺談受賄罪的立法完善.學術前沿.2011(5).3.
李潔.為他人謀取利益不應成為受賄罪的成立條件.當代法學.2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