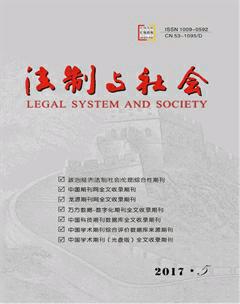淺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適用
摘 要 2011年2月25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被列入《刑法修正案八》,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行為自此可上升為刑事犯罪。“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放在刑法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罪部分,因此,該罪犯的是公民的財產權,準確地說侵犯的是勞動者的財產權。同時,“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又因妨礙了正常的勞動用工關系,其又侵犯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本文以裁判文書網的大數據和龍巖地區的案例為樣本,擬淺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適用。
關鍵詞 勞動報酬 立法 主體認定 審理模式 行政前置程序
作者簡介:邱媛媛,福建金磊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四級律師。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009
一、“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立法背景和立法過程
隨著經濟的發展,用工需求不斷增長,傳統的工人階級已經無法滿足我國的用工需求,我國特有的工農聯盟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又一次發揮強大作用,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產生“農民工”這一特色詞匯。1983年社會學家張雨林教授首次提出“農民工”概念,2003年溫家寶總理為重慶農婦熊德明討回了包工頭欠她丈夫的工錢,“農民工”成為社會熱點,而農民工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到工錢,即保障他們的勞動報酬權,這是一個民生問題,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非常重視。因此,如何切實保障民生,保障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拿到應有的勞動報酬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熱點,運用國家強制力就提上臺面。
傳統觀念認為,欠薪僅是民事糾紛,沒必要上升為刑事犯罪。然而處理此類民事糾紛,一般是通過協商、調解予以解決,或者通過行政責令方式解決,終極武器是提起勞動仲裁直至法院終審,然后由法院強制執行。民事法律途徑能夠解決部分欠薪問題,但難以解決惡意欠薪問題,特別是在錯綜復雜的用工關系下,往往無法得到有效解決。而且,勞動者的維權成本太高,往往不愿意走正常的民事法律途徑,漫長的維權路讓勞動者失去信心,對老板失去耐心,甚至懷疑政府,直至產生“壞心惡心”;最終產生信訪、堵路、圍堵政府,爬電線桿、跳樓、喝農藥等“犯罪式維權”、“自殘自殺式討薪”。
惡意欠薪能否上升為刑事犯罪?從法益保護說來看,惡意欠薪妨礙了正常的勞動用工關系,侵犯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也侵犯了勞動者的財產權,也就是說惡意欠薪已經觸犯了刑法的保護底線,應當處以刑罰,因此將部分欠薪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是行之可能的。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進行了調整,在破壞生產經營罪的基礎上,增加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其一般構成為:“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同時定義了用人單位犯罪:“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同時為了達到立法的目的,有效督促用人單位或個人履行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義務,保障勞動者的合法勞動報酬權,又作了罪輕規定:“有前兩款行為,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在提起公訴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并依法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至此,針對“欠薪”里讓勞動者比較無助的“惡意欠薪”,在勞動者采取一般民事法律途徑前,可通過刑事定性加以干涉;在強大的國家強制力面前,“惡意欠薪者”變得“乖張”起來,從而有效地震懾并解決了部分“惡意欠薪”。
為了有效地適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對外發布了《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3號)(以下簡稱司法解釋(法釋〔2013〕3號))。
2014年12月23日,為進一步完善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制度,進一步加大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切實有效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公安部根據《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國務院2001年第310號令)及相關規定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查處銜接工作的通知》(人社部發〔2014〕100號),《通知》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查處、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違法犯罪案件做了細致、可行的規定,同時也完善了勞動保障監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聯動配合銜接機制。
至此,“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從刑法到司法解釋,再到執行部門協調上有了較為完善的規定。全國范圍內“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新聞時有報道,“欠薪”成為高壓線,有效地抑制了“欠薪”勢頭,有力地保障了職工的勞動權利,切實維護了社會穩定。
二、自本罪實施以來的,法院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情況(以裁判文書網公布的案例為分析樣本)
第一,全國法院截止2017年2月22日共審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3208件,其中2011年1件,2012年6件,2013年96件,2014年840件,2015年727件,2016年1529件,2017年9件。
第二,福建法院截止2017年2月22日共審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144件,其中其中2011年0件,2012年0件,2013年2件,2014年30件,2015年28件,2016年84件,2017年0件。
第三,龍巖法院截止2017年2月22日共審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12件,其中2011年0件,2012年0件,2013年0件,2014年3件,2015年3件,2016年6件,2017年0件。
第四,通過以上數據,拋開2017年的數據,可以簡單地得出案件在逐年上漲的結論。很顯然,這不是因為這類犯罪基數在增長而導致法院審理案件增長,而是因為針對這類犯罪案件的打擊力度在加強,相關規定在完善,使得“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能夠有效地處予刑罰。在2013年最高院司法解釋出臺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例非常少,特別2011年全國法院在裁判文書網上僅有1例,到了2012年全國法院在裁判文書網上有了6例,到了2013年在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支持下,全國法院審結了96件“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但在福建仍然非常少。到2014年,“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突然呈現“井噴”,全國法院從2013年的96件突增到2014年的840件,福建法院從2013年的2件突增到2014年的30件,龍巖法院也在2014年完成了“0”突破。
三、在復雜的用工形式下,如何正確適用“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以達到其刑法目的
(一)本罪主體的認定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即單位也可構成該罪的主體。一般理解,該罪犯罪主體為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定義的用人單位;同時,針對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分包、轉包現象,存在大量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單位和個人違法用工情況,法釋〔2013〕3號司法解釋和人社部發〔2014〕100號通知也明確了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單位和個人也可以構成本罪的犯罪主體,其中最典型就是建筑領域的“包工頭”。同時本罪有“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前置程序,因此對于加工承攬關系和勞務關系中的用工主體,因政府有關部門無法介入,故無法用本罪予以調整 。
案例一:2014年6月,孫某甲向龍巖市某建筑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承包龍巖市月山小區C區標段地下7—8區模板工程。7月,孫某甲從某公司領取工程款254802元后,未支付其雇傭的73名工人工資223280元。龍巖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依法送達了《勞動監察限期整改通知書》,要求孫某甲于2014年12月10日前支付所拖欠工資。2015年1月11日,公安人員在貴州一賓館抓獲逃匿的孫某甲,龍巖市新羅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孫某甲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計人民幣223280元,數額較大,其行為已經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并處罰金二萬元。孫某甲認為自己不符合本案的犯罪主體,未追究公司責任,提起上訴。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本案孫某甲是否符合本罪的主體,公司將部分模板業務發包給了沒有用工主體資格的孫某甲,且向孫某甲支付了勞動者全部的勞動報酬,但孫某甲未向勞動者支付,龍巖市勞動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按照《關于加強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查處銜接工作的通知》第一條第三款之規定,向孫某甲個人下達限期整改指令書是正確的,人民法院僅對孫某甲作出刑事判決,而未對公司作出刑事判決也是正確的。
案例二:龍巖市某茶葉有限公司將業務全部發包給柯某,雙方約定:承包期間生產、銷售、品牌等所有業務都由柯某承包,工人工資也由柯某支付。2015年6月,承包合同未到期,公司張貼布告,以“柯某未交清承包費”為由,收回所有業務。6月30日,公司通知41個工人放假半個月,并承諾,放假在家待崗期間發放最低工資。放假時間到期后,公司告知要延長放假時間,直至10月,41個工人向龍巖市新羅區勞動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監察大隊投訴,承包期間,柯某拖欠2個月工資,收回承包權后,公司未支付最低工資。后龍巖市新羅區勞動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欲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公安機關認為柯某不符合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主體構成要件,且其無能力支付非有能力不支付,決定不予受理。
本案柯某是否符合本罪的主體?公司具備用工主體資格,沒有實際支付工人工資,柯某沒有用工主體資格,卻是實際用工者。筆者認為:根據《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單位或者個人,違法用工且拒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之一的規定,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追究刑事責任。本案,柯某是不具備用工資質的個人,其行為是違法用工,但其仍需承擔給付工人工資的義務,因此柯某符合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主體構成要件。
(二)本罪的行政前置程序
本罪構成的前提是“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如何理解“政府有關部門”?普遍認為“政府有關部門”是指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實踐中基本也是由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擔負該責任,人社部發〔2014〕100號通知也明確了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對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違法犯罪案件查處、移送以及刑事司法銜接的規定,因此狹義的“政府有關部門”是指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但筆者認為《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沒有排除包括各級信訪、住建等政府部門,因此廣義的“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包括所有在用人用工關系上負有監管義務的政府有關部門。
這里還涉及到“責令”的送達問題,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四十條規定“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在宣告后當場交付當事人;當事人不在場的,行政機關應當在七日內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將行政處罰決定書送達當事人”和《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關于期間、送達……,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不論該“責令”是行政法律文書還是民事法律文書均適用《民事訴訟法》的送達規定。對此,司法解釋(法釋〔2013〕3號)第四條第二款也明確規定:行為人逃匿,無法將責令支付文書送交其本人、同住成年家屬或者所在單位負責收件的人的,如果有關部門已通過在行為人的住所地、生產經營場所等地張貼責令支付文書等方式責令支付,并采用拍照、錄像等方式記錄的,應當視為“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
上述案例一,孫某甲在一審判決后不服上訴,其上訴辯稱:勞動監察部門沒有依法送達《勞動監察限期改正指令書》,原判作為定案依據錯誤。二審法院經查,龍巖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出具的《關于孫某甲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情況說明的函》,證實孫某甲在勞動監察部門組織的協調會上當場表示拒絕支付工人工資,隨后孫某甲離開龍巖返回貴州老家,后該局在孫某甲的辦公場所以張貼形式送達《勞動保障監察限期改正指令書》并以拍照形式留存,應當視為依法送達《勞動保障監察限期改正指令書》。因此,二審法院認為孫某甲該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三)本罪的審理模式
筆者檢索中國法院網裁判文書網案例,發現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屬刑民交叉案件,審理模式有三種類型:“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和“邊民邊刑”,而對刑民交叉案件采用不同的審理模式會出現不同的司法效果。
案例三:“先刑后民”,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2嘉平刑初字第59號)僅對被告人黃某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判決,對民事部分拖欠農民工的工資未作判決。
案例四:“先民后刑”,安徽省銅陵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4銅中刑終字第00075號)審理查明部分寫明,銅陵市郊區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60份民事判決書證明原判認定柯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24萬余元的事實有誤,應為21萬余元,本院予以糾正。故判決:一、撤銷安徽省銅陵市郊區人民法院(2014)郊刑初字第00021號刑事判決;二、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柯某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三、責令柯某立即支付拖欠的60余名員工工資21萬余元。
案例五:“邊民邊刑”,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浙03刑終1404號)判決:一、維持溫州市鹿城區人民法院(2016)浙0302刑初1066號刑事判決第一、二、三項,即被告單位溫州市阿黛爾鞋業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單處罰金人民幣20000元;被告人吳子義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被告人吳建春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二、責令被告單位溫州市阿黛爾鞋業有限公司退賠員工工資474033.35元。
通過上述案例三、四、五,我們可以了解到全國各地做法不一,也沒有建立統一的標準。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處理的普遍模式是“先刑后民”,筆者經辦的一起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早在2014年農民工就找到筆者希望給予法律援助,經辦過程中,市勞動監察大隊認為,該案涉嫌刑事犯罪,已移送公安機關,正在偵查,不能配合調取證據材料。因無證據2014年農民工無法申請勞動仲裁或提起訴訟。2016年,刑事案件判決后,經辦法官告知工人,可憑刑事案件證據、判決書要求被告人支付工資。而在民事部分審理時,又遇到了種種困難,市仲委以承包關系為由不予受理。區法院雖受理該追索勞動報酬糾紛,但由于刑事案件審理時主要以部分證人證言、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籠統不具體)為依據,所以部分農民工的主體資格及被拖欠的具體金額受到了質疑。
筆者認為,應當采用案例五邊刑邊民的模式進行。采用邊刑邊民的模式更符合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立法目的。從立法目的上看,增設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遏制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的問題。如果采用先刑后民的方式不利于勞動者及時追索被惡意拖欠的工資,邊刑邊民的模式,無疑會減少訴訟時間,減少農民工的維權成本,也便于審理法官查明事實。
(四)本罪立案標準
司法解釋(法釋〔2013〕3號)第三條規定,拒不支付一名勞動者三個月以上的勞動報酬且數額在五千元至二萬元以上的,或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且數額累計在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數額較大”。
其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研究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筆者經網絡檢索,發現江蘇省定義“數額較大”的標準是:拒不支付一名勞動者三個月以上的勞動報酬且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或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且數額累計在六萬元以上的;江西省定義“數額較大”的標準是拒不支付一名勞動者三個月以上的勞動報酬且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或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且數額累計在五萬元以上的。但截止到目前,筆者未在公開的信息中查找到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確定的福建省執行的具體數額,同時在裁判文書網上關于“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福建省的案例也未發現引用福建省的立案追訴規定,因此為便于執行,筆者希望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盡快確定福建省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如有也應當在其官網上公示公開。
綜上,筆者認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出臺有著廣泛的社會需求基礎,實踐中有效地遏制了惡意欠薪,乃至普通欠薪的發展蔓延勢頭,切實保護了正常的勞動用工關系,保護了勞動者的財產權,維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同時,筆者認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有別于其他罪名,其強調了政府的行政作為,在行政行為無效的情況下,才采取刑事措施以保障勞動者合法的財產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的正常經濟秩序。筆者希望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文明的不斷進步,惡意欠薪不再發生,“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能夠退出歷史的舞臺。
注釋:
江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犯罪主體認定.金融經濟.2013(4).75-77.
中國法院網孫某甲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二審刑事裁定書.(2016-09-26).http://wens 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1aea64ee-908a-467f-9ac8-3e522a3deca0.
黃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一審刑事判決書. (2015-01-08)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3146b814-eb2f-4628-ab31-a6bdc0b5d449&KeyWord.
柯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二審刑事判決書.( 2014-10-30)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aeb3f79f-6d3a-44b0-96c7-29b4f0e23332&KeyWord.
溫州市阿黛爾鞋業有限公司、吳子義等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二審刑事判決書. (2016-11-01)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ff793e6c- 97f8-4618-8abb- 9a19699d64cc&KeyWord.
毛立新.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審理的標準.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9(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