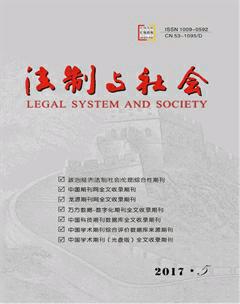我國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及行使規則研究
摘 要 本文著眼于我國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及行使規則展開研究。全文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討演繹作品的認定問題,即演繹作品之構成要件;第二部分主要圍繞演繹作品,尤其是侵權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問題展開研究;第三部分探討并試圖明確演繹作品著作權行使的規則及其界限;小結部分則就我國現行《著作權法》中有關演繹作品規定的欠缺之處略述己見。
關鍵詞 演繹作品 構成要件 著作權 歸屬 行使
作者簡介:何雪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2014 級法學專業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學。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027
演繹作品在我國《著作權法》的框架中是一種特殊的著作權客體。多元化的權利主體、多樣性的演繹形式及手段、演繹作品與原作品之間的復雜關系共同導致了其著作權歸屬及行使問題的復雜性。盡管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及行使規則研究難度頗大,但仍有章法可尋。 篇幅所限,下文之各項討論僅基于我國的現實情況展開。
一、演繹作品的認定
作為一個學理上的概念,演繹作品并未進入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內,但其含義、著作權之歸屬以及行使規則,在我國《著作權法》第12條中有所體現。學界有吳漢東教授觀點認為:“加工現有的作品以及材料亦即演繹作品的創作過程”。結合立法者意圖可知:演繹作品是指在已有作品的基礎之上,經過翻譯、改編、注釋、整理等手段加工而成的作品。
本文旨在探究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及行使規則。因此,首先需確定該項制度的客體及其涵括的對象。在此意義上,厘清演繹作品的構成要件尤為重要,筆者總結為如下兩點:
(一)須存在對原作品之利用,具有利用性
一般來說,演繹作品之創作乃基于原作品的基本表達之上,故必有對原作品之利用,集中體現為利用的對象及其程度。
一方面,利用的對象即演繹之內容,亦即借鑒原作品之部分;根據“思想與表達二分法”理論推導,演繹作品中的利用所及僅為原作品之表達,而非思想;另一方面,利用的程度即演繹者對原作品內容利用的多寡及比例。當然,判斷方法、標準以及比例需要在個案中須針對具體情況予以把握。
(二)須在原作之基礎上另有顯著區別之獨創
“獨創性”作為界定我國著作權法意義上“作品”的重要標準之一,對于演繹作品自不例外。演繹作品必須建立在采取某種演繹方式對原作品進行別樣展現的基礎之上,且須另具顯著區別于原著之獨創性。
演繹作品的獨創性意味著相較于原作品,新作在其基礎上至少具有最低限度的創造性,此間包含四個層次:
其一,演繹作品無須具備完全的獨創,只要其存在一定程度的創新,即視為一部新產生的作品。
其二,獨創性表達應立足于演繹作品的整體而言,其實質是以“整體轉換”的形式來滿足獨創性之要求,因而孤立、分割的眼光是不可取的。
其三,雖言只需一定程度之獨創,但這種獨創性理應高于一般作品,當為“實質性之區別”,而非“可識別之變化”。
其四,要排除因來自相同原作品而導致的相似性。
獨創性是演繹作品得以成為法律意義上規范作品的前提要件,利用性則是其有別于一般原始作品、被認作一種特殊作品類型的緣由所在。因此,利用性與獨創性作為演繹作品的兩大特征,亦共同組合為評定該作品類型的尺度與標準。
二、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
(一)作者即演繹作品的著作權人
演繹作品并非原作品的機械復制,而是建立在新的思想表達形式的基礎上對原作品之再現,這便需要演繹者正確理解與把握原作品之精義,并付出創造性之勞動。因此,其著作權理應由作者享有。
(二)侵權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
一項客體即便符合前文所述評定演繹作品的標準,也可能存在不規范的侵權行為,集中體現為侵犯演繹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但是,侵權因素作為表現而非實質,其本質并不妨礙著作權之歸屬,應當確立其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地位。
1.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來看
《著作權法》并未將作品之“合法性”作為其獲得著作權保護之要件。演繹者對于侵權演繹作品享有著作權,且自動產生,與原著作權人享有之著作權并無二致。
2.從著作權法的價值取向來看
為加速社會范圍內的知識共享與流動,侵權演繹作品中的侵權部分固為法不容,但因噎廢食的做法亦必不可取。換言之,侵權因素的存在對其著作權之歸屬并無實質影響,亦不妨礙演繹者對其獨創性部分的權利行使。完全不保護的做法不僅侵犯了原作品著作權人的權利,還有可能牽涉原作品著作權權益之行使,如此便違背了著作權保護的初衷。
3.從現實來看
現代科技迅猛發展,互聯網催化著作品的傳播,電子書、電子雜志、小說、漫畫、視頻剪輯等大量存在于相對開放的網絡空間,大大降低了逐一向原作者請求授權的可操作性。演繹作品乃原作者與演繹者共同的心血結晶,雙重的財產權利理應得到更為切實的法律保護。
在此需要明確一點,即筆者對于侵權演繹作品亦可取得著作權的肯定態度并不意味著認同給予其著作權完整保護的做法。在承認侵權演繹作品的著作權地位,予以保護的同時,也要施加一定限制以維護原作者的著作權。
三、演繹作品的著作權行使
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既已確認,緊隨而來的便是其著作權的行使問題。演繹作品據其屬類理應符合著作權行使的一般性規則,但由于其迥異于普通作品的特別性質,故行使規則自當獨具個性。
(一)行使演繹作品著作權的一般規則
演繹作品由原作加工而成,故演繹者對其作品享有的著作權自應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不得侵犯原作品之著作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演繹作品的利用應建立在演繹者與原作者共同許可的基礎上并各自支付相應報酬。
1.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
(1)兩者的著作權相對獨立。演繹者在行使其著作權時應擔負不得侵害或妨礙原作者著作權行使的消極義務,對演繹作品中只及于自己獨創之部分享有完整之著作權。如若僅使用新增的獨創性表達,則無需原作者之授權。
(2)原作品著作權限制著演繹作品著作權之行使。著作權作為一系列精神及財產權利的集合體,故對于演繹作品著作權之限制也應著眼于精神權利、財產權利兩方面展開討論。
在精神權利方面,主要是針對修改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作品為作者之第二人格,演繹者進行演繹活動時應注重對原作品作者人格之尊重與保護,擅自歪曲、抹黑原作者之真意應被視作侵害原作品之著作權,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在財產權利方面,法律未作特別限制,通常都允許權利人藉由合同的形式合意處分。這就要求雙方在確定各自的權利義務范圍時,須于合同條款中寫明,厘清雙方的權利及義務界限。
由此可見,演繹作品自誕生之初即獲得了有效的著作權保護,及至日常使用時始發生著作權行使之限制,形成一種相對獨立、部分制約的權利狀態。
2.使用演繹作品,應當取得雙重許可
結合我國《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可知:演繹作品的利用應建立在演繹者與原作者共同許可的基礎上并各自支付相應報酬。
由于演繹作品傾注了原作品作者與演繹者的共同心血,若賦予二者獨立的作品使用許可權顯然欠缺妥當。換言之,當且僅當作品利用者取得了原作作者與演繹者的雙重許可,其行為始為合法。
但在特別情況下,如確屬演繹者所獨創之部分,其利用無須經過原作者之許可。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對于演繹作品中新穎的獨創性表達,其著作權人可自由使用而不受他方制約。
(二)侵權演繹作品的著作權行使
根據作品侵權與否之性質可將演繹加工行為分作合法、侵權兩大類。縱然侵權演繹作品之著作權自其完成之時即宣告獲得,但與原作相關之使用權仍不可自行其是。如果對侵權演繹者不加限制,允許其對侵權演繹作品恣意利用,必然會對原作品作者之精神及財產利益造成難以估量之侵害,以致摧毀整個著作權激勵機制。
再者,從權利性質的視角觀之,演繹作品著作權作為原作品著作權之從權利,本由其衍生,故而如若行使侵權演繹作品之著作權,就必須要經過原作品著作權人的同意。
(三)根據已有作品制作的視聽作品的特殊規則
我國《著作權法》第15條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但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者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將戲劇、小說等文學作品改編成劇本,進而衍生出電影、電視劇等符合演繹作品構成要件之表達形式,實質上屬于演繹作品,因此可將上述規定視作演繹作品的特殊行使規則。
四、結語
相較于原作品而言,演繹作品同樣包含著演繹者的智力成果,對此法律應一視同仁地對二者給予平等之保護。然又考慮到演繹作品與原作品相互間的密切關系,這種作品之著作權固由演繹者所享有,但在實際運用該權利時,則必須兼顧原作著作權人與演繹作品著作權人的雙方利益。
重新審視我國演繹作品著作權歸屬及其行使規則,不難發現我國著作權法在一些表述上曖昧不明。譬如對于侵權演繹作品是否應當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問題一直未作明確規定,這使得在實際操作中,法官對相關案件的審理擁有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權。對于著作權法中演繹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及其行使規則之架構,乃至整個著作權法體系的完善,亟待我們的進一步努力。
參考文獻:
[1]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江姍姍.演繹作品的著作權保護研究.華南理工大學.2013.
[3]李明江.侵權演繹作品的著作權問題研究.北京化工大學.2012.
[4]黃鑫.西南交通大學.演繹作品保護研究.2015.
[5]袁博.改編演繹作品的授權規則.人民法院報.2013 年1月9日,第 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