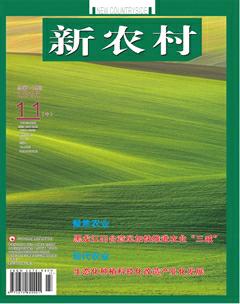從電影人格視角看周星馳電影的悲喜二重性
程壽慶
【摘要】 周星馳的電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電影的悲喜二重性,即既悲又喜,是悲劇與喜劇的統一體。而這種悲喜二重性根源于周星馳在生活現實與生命理想之間矛盾沖突的電影人格:從理想的角度自上而下地看現實就會形成悲性,而從現實的角度自下而上地看理想則會形成喜性,而且由于這種悲和喜源出于同一電影人格的同一矛盾沖突,因而它們相互之間又是一種交織纏繞、水乳交融的關系。
【關鍵詞】 周星馳;電影;電影人格;悲;喜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多年來,周星馳的電影以其天才的喜劇風格給人們帶來了無數的歡聲笑語。然而,周星馳喜劇電影的獨特之處(亦是成功之處)就在于,它在讓人開懷大笑的同時往往又會讓人有一種在看悲劇電影時的悲傷酸楚之感。因此,很多觀眾在看周星馳的喜劇電影的過程中都是喜一陣,悲一陣,甚至悲喜交加。可以說,周星馳的喜劇電影本身就是喜中有悲、悲中有喜,是悲劇與喜劇的統一體。這就正如周星馳自己所說的:“喜劇與悲劇是一體兩面”,“最好的東西是那種‘笑中有淚的”[1],要“把悲劇用喜劇的形式表達出來”[2]28。但筆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的喜劇電影為何會有這樣的悲喜二重性。近來,筆者終于略有所悟:這根源于他那在生活現實與生命理想之間矛盾沖突的電影人格。所以,本文就試圖從周星馳的電影人格的視角來分析他的電影的這種悲喜二重性。
一、為何悲?
中世紀的歐洲有一句諺語說:人,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這句諺語形象地表達了人性的復雜性,即人既不純然是動物,也不純然是神靈,換言之,人既是動物,又是神靈。動物僅僅具有感性,是單純感性的存在者,它只有感性的肉體需求;神靈則只擁有理性,是單純理性的存在者,他沒有肉體而只具有精神的形式。但人并不如此簡單,他既不同于前者,也不同于后者,他是二者的結合,是肉體與精神、獸性與神性的統一體。因此,人性是跨越兩界的,它一方面在現實的此岸世界,一方面又在理想的彼岸世界,它跨越于兩個世界之間。人性的這種雙重性恰恰使其具有不同于動物和神靈的獨特性和復雜性。
本來,人性的這種雙重性在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不足為奇。但是,一旦有人明確地意識到這種雙重性,并且不安于單純的感性方面的生活,以其中的精神或神性方面的生活為更高目標,追求一種精神或神性的生命,那么這種雙重性之間的矛盾就會暴露無遺了。而在電影中的周星馳正好就是這樣一種人格。一方面,他作為感性的存在者,必然擁有諸如七情六欲的感性欲求,因而他必須謀求金錢財富,以滿足肉體上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他又輕視肉體需求,決不以感性生活為最高目標,而是要超越于現實的感性生活之上,以精神或神性的生命為理想,以尋求精神生活的滿足。這樣,周星馳在他的電影人格結構中的矛盾沖突就在他的影片中尖銳地呈現出來了。我們看到,在《喜劇之王》中,龍套尹天仇一方面屢不得志,并導致生活拮據,甚至差點連飯都沒得吃,另一方面卻依然熱愛演戲,并苦心鉆研演技,一心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演員,在遭人奚落時還不忘反復強調“其實我是一個演員”來維持自己的自尊。在《少林足球》中,阿星一方面身處社會最底層,以拾荒為生,生活落魄,舉步維艱,另一方面卻仍癡迷少林功夫(與他的幾位師兄弟因為謀生而荒廢功夫形成鮮明對比),始終心懷發揚光大少林功夫的夢想,并在游說大師兄一起合作而他卻毫無斗志時鼓勵他說:“做人如果沒夢想,那跟咸魚有什么分別?……我心中的一團火是不會熄的。”一邊是慘淡不堪的生活現實,一邊是夢寐以求的生命理想,矛盾尖銳不言而喻。
如果僅僅看到矛盾,那么還不至于產生悲觀的態度和悲傷的情感,因為矛盾通常總有化解的辦法。但問題在于,生活現實與生命理想的矛盾完全不同于一般的矛盾,它從來都是難以化解的。因此,當人們跟隨著電影中的周星馳發現理想遠離現實、高不可攀,當人們跟隨著電影中的周星馳從遙遠的理想反觀現實,發現人心余力絀,無法達到理想的高度,理想與現實有著無限的距離,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巨大反差立刻就會讓人產生一種形如螻蟻的渺小無力之感,接踵而至的也就是悲從中來了。尤其是,電影中的周星馳常常使用夸張的手法來故意拉大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和反差,讓人在現實的不堪與理想的渺茫的強烈對比面前產生一種近乎絕望的悲觀態度。而且,在電影中他又一般表現為一種對理想極度認真甚至偏執的人格,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容不得絲毫妥協,并因此常常碰得頭破血流,這就更加增添了一種悲哀的氣氛。不管是在《功夫》中從小就幻想著成為武林絕世高手卻在現實中成了一個一事無成、無可救藥的街頭混混的阿星,還是在《喜劇之王》中一直醉心于演戲并夢想著成為真正的演員卻在現實中經常連跑龍套的演出機會都找不到而屢屢碰壁的專業演員尹天仇,都是在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中更加突顯一種悲涼氣息。周星馳的喜劇電影給人的一個啟示是,理想遙不可及,現實固若金湯,個體在無限的理想與有限的現實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之夾縫中時常只能成為犧牲品,而有限的個體的犧牲反過來又成全和彰顯了理想的無限性,在這種有限與無限兩極分化的強烈反差中悲情溢于言表。
二、為何喜?
然而,如果僅僅有悲情,那么這樣的電影充其量只會是單純的悲劇。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周星馳的電影同時是一種喜劇,人們也都習慣于把他稱為“喜劇之王”。因此,周星馳的電影是亦悲亦喜,悲中有喜,觀眾也常常在其幽默與搞笑之中爆笑不止。特別是當這種幽默與搞笑被他以一種夸張的無厘頭的方式表現出來時,其效果就更加顯著了。那么,這種喜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它在周星馳的電影人格的結構中又處于怎樣的位置呢?
上文已經指出,在生活現實與生命理想難以調和的矛盾中,如果從理想的角度自上而下地來看現實,那么人們就會著眼于現實的不堪和自身的有限性,從而形成一種悲觀的態度和悲傷的情感。但如果視角反過來,從現實的角度自下而上地來看理想,那么情況也將會顛倒過來,而形成一種樂觀的態度和喜悅的情感。原因在于,此時人們會著眼于理想的崇高與無限性,發現自己之所以有這樣崇高的理想乃是因為自己不只是肉體的存在,而同時還有思想的精神的存在,他可以在思想中超出自身而以無限的理想為目標,雖然立足當下現實,但卻面向未來理想,因而有希望。一個心懷希望的人必定是一個樂觀豁達、積極向上的“喜人”。所以我們才會在周星馳的諸多電影中看到,盡管出身卑微,即使身陷囹圄,電影中的周星馳永遠沒有絕望,即便有過自暴自棄的時候,但那只不過是人之常情,而不會是意志崩潰的徹底墮落。譬如在《喜劇之王》中的尹天仇雖然藝路坎坷,窮困潦倒,但卻依然信念堅定,堅持不懈,百折不撓。又如在《武狀元蘇乞兒》中的蘇燦雖然淪落為乞丐流浪街頭,而且武功盡失淪為廢人,但在短暫的沉淪之后迎來的是徹底的爆發。還有《九品芝麻官》中的包龍星,雖然自己身遭誣陷,但為了伸張正義而奮不顧身,歷經千難萬苦進京告狀,最終為戚秦氏洗清不白之冤。
當然,這種積極樂觀的“喜”在電影中往往并非被周星馳以一種通常的方式表達出來,而是被他表現為一種看似莫名其妙的無厘頭。所謂無厘頭,就是人在言語和行為中故意夸張地把一些表面上毫不相關的事物牽扯到一起,因而顯得毫無邏輯、思維跳躍,讓人感到古怪離奇、不合常理,從而達到幽默和搞笑的效果。在華語電影中,周星馳雖然不是無厘頭表演方式的唯一運用者,但卻是這種表演方式的開創者和代表性人物。例如在《國產凌凌漆》中,凌凌漆竟用總司令給的一百塊錢賄賂其部下而在槍口下逃過一劫,并且最后用一把殺豬刀打敗了金槍客,還有他那兩句經典的臺詞:“飛是小李飛刀的飛,刀是小李飛刀的刀”,“古有關云長全神貫注下象棋刮骨療毒,今有我凌凌漆聚精會神看A片挖骨取彈頭”。又如在《大話西游》中,斧頭幫幫主至尊寶率領眾匪欲擒拿蜘蛛精春十三娘,誰料眾匪在春十三娘的高強武藝面前竟丟下幫主逃之夭夭,后來當眾匪跪地向春十三娘求饒,至尊寶卻大喊著要跟她拼命,正當大家都以為他要殊死一搏時,他卻突然五體投地,趴地求饒,其見風使舵速度之快,厚顏無恥程度之深,都令人匪夷所思。還有在《唐伯虎點秋香》中那段被廣為傳頌的唐伯虎打小強的橋段。其實,在周星馳的諸多電影中,這樣的無厘頭真是數不勝數,不勝枚舉。它們在使人感到荒誕不經的同時又不會讓人一頭霧水、茫然不解,而是讓人覺得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并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喜逐顏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所有這些無厘頭底下都貫穿著一個原則,那就是對生活的樂觀態度。只有一個對自己的生活心懷樂觀態度的人,才有可能在自己生活的時時處處都表現出一種風趣橫生的超然境界。所以,周星馳的無厘頭其實并非了無章法,而是有跡可循,因而也并非全然無厘頭,而同時也是有厘頭。這種有厘頭的樂觀態度同時造就一種積極的情感,即喜悅的情感。
三、為何悲喜交加?
由此可見,在周星馳的電影中不僅有悲,而且有喜。這種悲和喜雖然在理論上(或者說在邏輯上)可以作為不同的層次被分析出來,但在現實中(或者說在時間中)卻并非水火不容地外在對立,相反,二者既對立又統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不可分離。王銀在其《悲喜渾成:周星馳喜劇電影中的悲劇意識探討》一文中評論道:“周星馳創造性地在喜劇電影中融入悲劇因素,將一種新的生命力注入喜劇之中,使其具有了一種新的審美價值。”[3]100應該說,這是一種很表面的外在觀點,仿佛周星馳的喜劇電影中的這種悲劇因素是從喜劇因素之外“注入”的某種“新的”東西,因而它既可取亦可舍似的。實際上,周星馳電影中的悲劇因素與喜劇因素、悲與喜正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樣,它們同時存在,相反相成,相得益彰,一方無法脫離另一方而獨自存在(參考本文開頭所引用的周星馳原話“喜劇與悲劇是一體兩面”)。因此,在周星馳的電影中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喜交加。
之所以這樣,乃是因為悲與喜二者在周星馳的電影中同時源出于同一個人格,即周星馳的電影人格。而且,這個人格是一個在生活現實與生命理想之間不可調和地矛盾沖突的人格。一方面,從理想的角度看現實,這個人格悲傷地發現具有凡胎肉體的自己非常有限,無法達到彼岸理想的高度,但反過來,也正因為這個理想高高在上,無法達到,它才是永恒不變的崇高東西,進而才能支撐著這個人格,而不至于讓它陷入絕望,因而既有悲又有喜,悲中有喜(有時表現為淚中有笑)。另一方面,從現實的角度看理想,這個人格喜悅地發現有限的自己同時又能主動地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而追求彼岸無限的理想,因而有希望,但反過來,也正因為這個理想是無限的,只是有希望去追求的,它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對這個人格而言又是虛而不實的東西,所以它又會心生失望與感傷,因而既有喜又有悲,喜中有悲(有時表現為笑中有淚)。所以,在周星馳的電影人格中,悲與喜發生于同一個矛盾沖突之中,二者辯證統一,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喜交加。尤其是當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矛盾沖突得以化解即理想與現實合一或者說理想變成現實時,這種悲喜交加會更加明顯、更加強烈。比如,在那部被周星馳稱為“實際上是一個悲劇”[1]的《喜劇之王》中,尹天仇一直連跑龍套的演出機會都找不著,最后落魄到差點連飯都吃不上,但沒想到突然否極泰來,被大明星娟姐相中并找去當電影的男主角,當娟姐問他意下如何時,尹天仇表情木訥呆滯,半晌才反應過來,弱弱地說了兩個字:“好啊!”我們可以想象到,當時尹天仇的內心中有著怎樣的悲喜交加的復雜情感才會產生這樣的表情和反應。
不過,在電影中周星馳所表現出來的這樣一種在生活現實與生命理想之間矛盾沖突的人格結構并非電影中的周星馳一個人所獨有的一種特殊的人格結構。相反,由于它植根于普遍的人性,它就在每一個人身上都或現實或潛在地存在著,因而它也是一種普遍的人格結構。因此,在電影中周星馳個人的悲其實是普遍的人性的悲,是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現實地擁有這種人格結構的人的悲,在電影中周星馳個人的喜其實也是普遍的人性的喜,是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現實地擁有這種人格結構的人的喜,他在電影中活出了人們已經活出、正在活出或者準備活出的生命。于是,在這一點上,他一個人就和其他所有的人都打通了,都相通了,所以對于電影中的周星馳的悲和喜,作為觀眾的人們也能感同身受,同情共鳴,進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喜歡和支持周星馳的電影,為什么他的電影能夠創造一個又一個華語影史的票房記錄和神話?這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細心的觀眾應該都會發現,周星馳在電影中的表演是一種本色表演,而非性格表演。也就是說,他在電影中所表現出來的人物的形態、性格和個性與他在現實生活中的形態、性格和個性是基本相同的,至少也是近似的(只不過電影中的他更加突顯了喜的方面,而現實生活中的他更加突顯了悲的方面)。因此,他在電影中表現的電影人格也可以說是他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格的藝術再現。我們看到,電影中的周星馳悲喜并存,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搏斗,而這也是現實中的他的真實寫照。他從一個多年默默無聞的影視龍套到一位享譽華語世界的喜劇大師的奮斗歷程眾所周知,但這只是他的內在生活的外在表現而已,并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內在生活中選擇了追求精神或神性的生命,努力想要尋找自己的本質和真相,因而呈現為一顆真誠而深刻的心靈。這顆心靈在數十年的苦苦摸索中逐漸柳暗花明,找到了自己的本質和真相,這個本質和真相就是——演員。這就正如周星馳在《長江七號》上映之后所說的:“直到遇到了《長江七號》,我才找回了那個久違了的我,所以,現在‘我真的很帥。我找到了自己,一個屬于我自己的真相——我就是一個演員。”[2]28所以,周星馳調侃權力,戲謔名利,一切都可以拿來調侃和戲謔,但唯有一樣東西他不但不調侃、戲謔,反而態度嚴肅認真,甚至嚴厲苛刻(這也是他得罪不少演藝圈人士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就是電影本身。因為他證明自己是一個演員的唯一方法就是演出卓越的電影,電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存在方式,離開電影,他就不存在,他就是什么也不是的“無”。在一次專訪中,當主持人問假如生活中沒有電影他會怎樣時,他回答:“那就什么都沒有了,什么都不是。拍電影的時候就感覺,我真的在生活,我是活著的。”[4]29
魯迅先生曾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5]35既然希望是虛妄不實的,那么人無希望,所以會悲,但既然絕望同時也是虛妄不實的,那么人又有希望,所以會喜。電影中的周星馳正是在這種絕望與希望之間演繹了一出又一出悲喜劇,也正是在這種悲與喜之間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經典。周星馳用電影的方式以其自身為標本探討著普遍的人性和永恒的生命,他表達了人們想表達而又未能表達的心聲,說出了人們想說出而又未能說出的話語。他以電影啟發著別人,也實現著自己。他為電影而生。
參考文獻:
[1]張英,萬國花,周密.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大師——周星馳專訪[N].南方周末,2004-12-23.
[2]周星馳.我是一個悲劇演員[J].東西南北,2009(09).
[3]王銀.悲喜渾成:周星馳喜劇電影中的悲劇意識探討[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15(04).
[4]阿諾,小七.周星馳專訪:拍電影時我活著[J].電影世界,2013(02).
[5]魯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