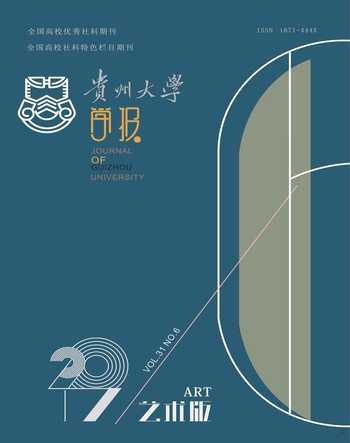再談華語電影
龔艷 魯曉鵬
學術主持人語:
“華語電影”這一概念在國內電影界引起的波瀾前后延續了十來年,《當代電影》《上海大學學報》等學術期刊都曾做過專題或訪談,在國內的幾次大型學術會議上國內外學者也就這一話題進行過交鋒,各自亮明過觀點。此次再做專題,既不想落人后,又很難出人意表,所以我們決定這一期的作者全部邀請海外華裔學者,希望提供更多闡釋角度。另外,除了第一篇訪談是對“華語電影”焦點人物魯曉鵬教授的訪談之外,另外兩篇是對“華語電影”這一概念的展開或者說是案例。香港電影是兩岸三地電影中最有特色的,它曾經的殖民地身份,后九七身份,以及商業和政治話語、西方和東方文化的交織都讓它呈現出不同于大陸和臺灣以及其他華語區域的特色。可以說華語電影成為了我們討論這些電影的通約數。匹茲堡大學錢坤副教授的論文《從悲劇英雄到黑幫罪犯:香港黑幫電影及其城市寓言》從類型的角度進入,兼顧和審視了香港身份問題,將香港社會和香港電影中的影像結合起來考察,我們之所以會討論香港問題,而不是討論一個北京電影或者沈陽電影,是因為香港電影在“華語電影”這個框架內是有效的。紐約州立大學珀契斯分校電影與媒體研究系助理教授張泠的《火山與礦山之歌:1930年代中國電影中的“南洋”想象/意象》以“華僑”“南洋”“故鄉”“異鄉”“他鄉”這些概念建構起了一個非常清晰的圖景:那些在中國本土之外的人、情、景。當作者將左翼和南洋連接起來,那個鄉土和他者,革命和遠方的投射變得更有趣。至少,“華語電影”是一個更有效的概念,能讓我們進入到那些差異化的又互相連接的華語區域電影的討論中。
中圖分類號:J9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444X(2017)06-0001-10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ysb.2017.06.001
時 間: 2017年4月1日
地 點: 美國匹茲堡大學
受訪人: 魯曉鵬教授(以下簡稱魯)
采訪人: 龔艷(以下簡稱龔)
覺得這個問題提出來有助于我們再去審視一些歷史的概念,其實它的外延和內涵可能就像您說的這個詞“旅行”,還在不斷的擴展、變化。我自己做邵氏的研究,我記得當時邵逸夫好像在新加坡建國的時候拍宣傳片的,這個關系就是很微妙的,他幫一個新興的脫殖的國家政府拍了個宣傳片,他又在新加坡、馬來亞這些地方做了大量的電影工廠,他的片場就在那里,拍大量的華語電影。你說怎么界定他?至少“華語”這個詞能突破國家、邊界等概念,可以涵蓋更多,有效性至今也是有的。
魯: 對。像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先生,是華人但他不會說漢語,他說英語,他在英國的制度下長大。后來他自己學華語,又鼓勵大家學華語。我在新加坡住幾天,打開電視發現,我要不看屏幕,以為是在中國。播音員的國語跟北京話差不多呀,沒有什么區別。這些問題是挺復雜。國族、語言、電影不能直接地劃等號,關系不對稱。有些同事寫東西自家人說自家話,但是如果大家換一個角度,換一個場所看問題,就可能有新發現。我是在北京長大的,所以我批評北京同事,也無所謂。假如你屁股坐在北京,坐在這個位置上,你就得這么說話。各種壓力下,你只能這樣寫,你換個方法和視角寫,可能還惹麻煩。中國非常大,比如上海各種人都有吧,有些上海學者看問題的角度與北京學者不太一樣。我碰到福建的學者,他們說,我們離中心很遠,我們有自己的看法。我并不反對北京的同事,我本人在北京長大,我不會說任何方言,只會說北京話,是我一生最遺憾的一件事。其實我的母籍是廣東番禺,我得自我批評。福建人說,我們這么遠,我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隔海就是臺灣呀,我們說閩南方言呀。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語言政治非常微妙。
前兩天我還問你萬瑪才旦的片子。他的情況很有意思,他是中國人民共和國公民,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機部分。但是他拍的藏語片,有極其個人化的東西。前兩年有一部藏語大片:《西藏天空》。雖然是藏語片,講藏人故事,但那是官方主導的一種拍攝方法。萬馬才旦的片子《塔洛》就不一樣啊, 很個人化。
龔: 是的。
魯: 電影剛開始,一個藏人背誦毛主席語錄,這給你無窮的想象和解讀。藏人跟中國政治的關系、那代人的經歷,非常有意思。
龔: 對。我當時和萬瑪才旦談這個片子的時候,我看過他以前的一些片子,不知道您看過沒有?我們當時在北京電影學院念書的時候有交往,他最早的短片是在北京電影學院放的,在一個學生電影節上,叫《草原》,很短又是藏語拍的,完全超越我們對少數民族電影的理解,他講的完全是他們那個宗教的邏輯,就是一個老太太要送上山去獻祭的牦牛丟了,村長就說我要幫你去找,然后鎖定了兩個嫌犯就去找這兩個人,他就讓這兩個男孩繞著嘛呢石轉,然后發誓說自己沒有拿,這個老太太最后說我不需要再去追查任何事情,因為如果你要懲罰人就有悖于我去做(祭神)這件事情。所以推動故事的構成或者說邏輯,不是漢族的邏輯了。但這就是我們希望或期待的東西。
魯: 就是呀。
龔: 我們當時覺得很不一樣,當時他年紀比我們大些,就在我們讀書的時候他早就已經寫小說寫詩歌了,本身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文藝青年,然后拍了電影。后來他就一直拍,為什么那天我約了他要談這個片子,因為我覺得《塔洛》里面有點急,有點很明確的那個意思。您知道那個片子講身份證丟了嗎?
魯: 少數民族身份,對不對?
龔: 是,而且這個片子一直沒有正式地放過,我在獨立電影節看的。我就問他,以前看你拍片子用心平氣和來形容,就很像他那個世界,或者說我們想象的那個藏族世界。他自己后來說有美化的成分在里面,他說我現在要拍這樣的你們看起來很用力的片子,我內心也在變化。因為他人特別溫和,非常謙和,說話聲音很小,漢語說得很好的一個人,但他寫作是用藏語。我覺得他身上有很多復合性,他自己一定是藏族精英,而且他深受漢文化教育。少數民族精英勢必要經過漢化這個過程,漢化這個過程其實是有矛盾在里面的,到底應該怎么去選擇。他說對,他說我是有意識地告訴自己雖然我是接受了漢族的教育,我也很向往漢族的文學、藝術,但是我的身份是一個矛盾體。而且他拍的電影里對民族的表達反而是看不到他自己說的他受傷痕文學的影響,他讀書的時候正好是1980年代,他說他是非常愛看那個時期的文學的,他也很活躍。他這個身份多復雜!
魯: 對。我覺得像這種個人化的電影或是少數民族電影挺重要,因為我們平常看不到。看到的多是有宏大敘事的從上到下主導性的電影,就像十七年的少數民族電影。
龔: 那就不叫少數民族電影了。
魯: 叫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是吧?我們對少數民族了解很少,我沒去過那些地方,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實呢?我的知識是從看電影來的,而且都是從一種特殊的角度看電影。現在有一部電視劇《新絲綢之路》,國內主要電視頻道播放。故事怎么開始呢?我不看都知道。開始一定是解放軍解放新疆,以前的統治階級跟國民黨勾結,解放軍來解放被壓迫的人民。少數民族題材的這個大的歷史模式不能變。剛才我說關于西藏題材的電影也有這個問題。那部大片也是從解放農奴著手。大的話語沒變。 1950年前后,解放軍進藏、進疆,這個根基是敘述底線。而萬瑪才旦的電影其實我們挺需要看的,但平常看不到,電影院也不公映吧。
龔: 2014年他在香港做過一個完整的放映。您說的這個“華語”,我記得您之前訪談里提到,他其實是多語種的,不是簡單的普通話。這里面肯定會有人覺得能不能涵蓋到他的范疇。
魯: 這個學術問題我也在思考,也沒有特別好的答案。我知道國內學者也做了一些努力。“中國電影”屬于“國族電影”的范疇,中國境內拍的電影是中國電影。后來華語電影的概念出現以后,國內學者又搞出一個“母語電影”,比如蒙語電影、藏語電影。后來有人覺得這個概念說起來也不太上口。我也在想這個問題,華語不是個語言學的概念吧?在中國大陸,人們說“漢語電影”“漢語字典”。能不能華語電影也包括中國其他語言的電影呢?我想可以把萬瑪才旦拍的片子也算作華語電影,我個人覺得可以。大家可以討論一下,我也沒有特別好的解決方案。怎么歸類和劃分,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東西。華語電影、母語電影有些人贊同,有些人不贊同。華語電影包括各種方言,能不能不光是漢語方言,能不能包括其他民族的方言,少數民族語種?我持開放態度。
龔: 他們會不會糾結在“華”這個字上?
魯: 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這個話題。憲法里說,中華民族是多民族國家,這樣一來,“中華”就包括中國境內各種語言和民族。“華語”是否可以包括這些語言?大家需要反復研討。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叫“中華民族”,但是在美國就沒有這個概念,沒有說“美國民族”,說起來人家笑話。美國是一個多族裔的國家。“中華民族”你怎么翻譯成英文?“美國人民”怎么翻譯成中文?有時候兩個不同的文化語境轉變還是挺困難的。
龔: 是不是還是因為漢文化太過強勢和歷史的書寫作為主題?
魯: 有可能,這里有個歷史過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要成為一個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個國家叫什么名字都成問題。那時別人就開中國玩笑,包括從葡萄牙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說你看,這個國家沒有一貫名字,它叫“明”,或叫“清”,這是朝代名字,不是國家名字。 那時大家討論,這個國家應當怎么稱呼?可以叫“華”,可以叫“中華”“華夏”等等,最后選擇“中國”。“中國”這個字當然幾千年前就出現了,但是在近代,中國經歷了重新構建的過程,新的國家取名“中華民國”。
現在小學生都知道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是“中華民族”,但這個概念也是近代構建的,清末民初吧。辛亥革命志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孫中山他們要推翻滿族統治。后來成功了,滿族被推翻了,他們一看,不行啊,這是個多民族國家,你不能驅除這些民族。隨后,又出現新的概念,“五族”:滿、漢、蒙、藏、回,做了五色旗。中華民族不斷地自我構建。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學習蘇聯的經驗,識別它的民族。前蘇聯有一百多個民族,中國識別了56個民族,到今天這個數也不能變,只可以學術討論。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到“五族共榮”,到56個民族,國族的話語一直演變。電影研究也有類似現象,所謂“華語電影”“母語電影”都是有益的嘗試和話語的構建。
美國是另外一套說法。它有數不清的族裔,西班牙裔、越南裔、日裔、華裔、愛爾蘭裔、意大利裔,等等。它的官方話語是“多元文化”。它是另外一種國家構建。中國這么長的歷史,歷史演變比較復雜。前一陣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葛兆光寫了本書講中國歷史,他提到周成王時代的一件青銅器,上面寫著“宅茲中國”。那時候就出現了“中國”這個字,起碼有三千年了。這里“中國”的概念跟我們現在說的“中國”是否一樣?它可以證明“中國”的悠久,但是隨著歷史變遷,中國的概念不斷變化和擴充,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古老國度旺盛的生命力,就像《詩經》所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那時候周朝已經八百年了。中國是個老的國家,同時煥發新的生命,需要我們不斷地構建、闡釋、研討。什么是語言?什么是華語?什么是華語電影?身份認同問題,國族構建問題,諸如此類問題,需要大家不斷討論。
龔: 那回歸話題,比如說華語、普通話電影,戲曲電影中的黃梅調電影,因為戲曲電影曲目很多,但是黃梅調電影是特例,就是它流傳到東南亞比較盛行,邵氏當時那一批黃梅調電影風靡東南亞,包括北美也有。我想借華語電影這個語境來討論這個問題。黃梅調更傾向于普通話,我覺得這個是它流傳的一個因素。它在東南亞、臺灣地區非常盛行,這個和華語或者和普通話是否有聯系?
魯: 以方言為主的戲劇強調中華民族的多樣性、豐富性,比如昆曲電影《十五貫》,越劇電影,甚至像謝晉的《舞臺姐妹》。當初周恩來總理想把中國各地的戲劇拍成電影,這是強調中國的民族性。香港的方言喜劇電影,也能產生一種民族向心力,同時也娛樂港人。
龔: 對。身份的一個強調。看上去是去政治化,其實我覺得是強調身份的。
魯: 但是在電影工業運作的層面,比如邵氏公司,就有商業考量了。他要賺錢,希望擴展不同層次的華語電影觀眾,而在地理層次,讓公司的電影廣為流傳,波及東南亞。
龔: 但是黃梅調畢竟有點像普通話,那普通話本身就是有一點想要統攝民族,或者想要民族有個建構有個共同語言,所以他并不是所有曲種都拍,他選了黃梅調來拍,實際上在海外散居了各種籍貫的人,但是類似于普通話的黃梅調他是不是有這種建構的意思在?
魯: 也可以這么講。中國大陸的方言電影很多,比如賈樟柯的電影有山西方言。但賈樟柯講的是中國的故事,他用方言是偽裝。越有方言,中國性越強。從《小武》到《天注定》,他的片子使用中國各地方言,增強電影的真實感和戲劇感,內容上涉及中國各地的普通百姓。“十七年”也拍了一些所謂的方言電影,比如《抓壯丁》,那是通過方言講述宏大的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的故事。香港的粵語片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商業運作,以娛樂為中心,自成體系。現在香港電影經歷所謂的大陸化、中國化的過程,為了賺錢而跟大陸合作。影片的觀眾是中國大陸的龐大人口,這也慢慢地改變香港電影的模式和特色。香港幾百萬人口,原來南洋是非常大的市場。冷戰時期,南洋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的觀眾已經很了不起了。但跟13億人的大陸市場比,還是不行。陳可辛說,他不期待歐美市場,中國大陸市場足夠了。他拍《中國合伙人》,就是瞄著中國大陸。原來南洋市場很大,現在是個零頭。這樣做,港片也有點變味吧。片子都是雙語配音吧,針對大陸。
龔: 好像連續剪輯了幾個版本,我記得《無間道》就剪了幾個版本,大陸放的版本是不一樣了。當然版本不一樣在1950、1960年代就有,當時邵逸夫和香港其他公司發給南洋就有不一樣的,他們有考量。您說香港的粵語片挺有意思的,本來香港沒有那么多大陸人,在1940年代初大陸進去的那么多,他本土的人還是以粵語為主,當大量大陸人進去,普通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民族或者身份的標志,其實主要是方便溝通。
魯: 還有臺灣的市場吧。
龔: 對。他還是有市場考慮。但是到1970年代,香港本土化的意識起來了,所以1970年代到1990年代又是粵語特別興盛的時候,然后到了合拍片時代更復雜了。
魯: 臺灣的情況挺特殊。國民黨去了以后,他們的話語是革命話語,很像中國大陸的話語。蔣介石到死都說革命。那個時候就是拍國語片,雖然閩南話或者說臺語片也有。
龔: 臺語片有。
魯: 地位比較低。
龔: 對。那跟粵語殘片的狀況差不多了。
魯: 現在臺灣電影工業已經七零八落了,很可惜。原來以國民黨為主體的電影,輝煌一時。
龔: 有官方的電影廠。
魯: 很可惜,臺灣的電影工業生存艱難。
龔: 這兩年又起來一點,魏德勝拍了《海角七號》。但還是很狹窄,他還是只能到大陸來。
魯: 原來有國家主導的中影挺輝煌,他們的電影也送到香港和南洋,反過來說,臺灣也是邵逸夫的香港電影的市場。臺灣、香港、南洋這幾個地方互動。解禁以后,后蔣經國時代,臺灣的電影受到商業化沖擊。
龔: 但后來政府也鼓勵他們拍藝術電影,商業電影又完全被香港電影吞沒。其實臺灣一度有很好的商業類型,比如瓊瑤電影。
魯: 對。可是現在,它的電影產業微乎其微。
龔: 對,就斷了。現在又有一點但很零星,他們本土市場可能支撐一下,但都不夠。
魯: 前一陣子我還看一個葉月瑜的訪談,關于亞洲電影工業。她說,她寫完她的那本書以后,亞洲電影工業這個概念就不適用了,因為各方都來和中國大陸合作,沒有所謂亞洲電影工業。日本、韓國、香港、臺灣都和中國拍合拍片,看重大陸市場。
龔: 以前是多極的。
魯: 這是商業考慮。
龔: 對。當然也有政治。
魯: 也有,以后香港電影可能就沒有原汁原味的香港的東西了,它的產業跟大陸連在一起了。冷戰時期它跟大陸是分開的,是兩回事,它主要開拓南洋、臺灣,甚至韓國市場。我遇到一位韓國學者,他說他從小在韓國看吳宇森、周潤發的電影,比如《英雄本色》,是他們的粉絲。
龔: 對。那對我影響很大。我以前看過馬來西亞一個人拍的電影,他肯定是看香港電視劇長大的,一個馬來西亞的人拍武俠電影,他看得太多了。
魯: 是。韓國那時候也是臺灣和香港電影的市場。他說他上中學時候看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對周潤發印象很深,特別喜歡周潤發。港片的傳統市場包括日本、東亞、東南亞的觀眾,而現在主要是中國大陸觀眾,大陸的中產階級興起,構成龐大的消費群體。
龔: 但是我自己在大陸倒是感覺這幾年其實好多人還是比較樂觀的,一方面大陸本身生產的質量看上去很多很糟糕,但是錢又很多,錢很多的時候有的人就愿意投藝術片了。就是當商業都不好的時候,藝術就更糟了。現在藝術電影也還出來,雖然大的市場里也很糟糕,國片很差,但是很多像畢贛、萬瑪才旦也還是出來了。
魯: 一般人不愿意看這些緩慢枯燥的“藝術片”。《塔洛》開頭,光讀老三篇《愚公移山》就讀了三分鐘,誰有耐心看?一般老百姓看一會就不行了。賈樟柯的片子都看的煩。好萊塢大片鬧點科幻電影,娛樂目的達到就行了。年輕人看郭敬明的片子,放松一個半小時換換腦子就行了,不需要深刻思考社會問題。
龔: 所以他們其實很難,尤其是這種獨立電影導演。
魯: 拍了又不能流行。兩年前我在上海戲劇學院開會,看到一本新書:《蒙古族影視研究》。文集內容包括中國大陸內蒙古拍的電影,也有蒙古國的電影。這個問題就非常復雜。蒙古國是獨立的國家,而中國大陸有蒙古族。
龔: 但書強調蒙古族,所以還可以用蒙古語來概括,和我們講華語電影還不一樣,跨邊界的。
魯: 對。內蒙古是中國的事。
龔: 我們討論華語電影是討論內蒙古這個部分。
魯: 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不知道以后怎么解決。“國家”這個概念也不是天經地義、亙古不變的東西。馬克思就說,以后國家要消亡的。中國古代是一個帝國的概念,沒有邊境。草原上你的馬來吃草,我的馬也來吃草,沒有說弄個鐵絲網劃邊界。原來都是部落,今天我臣服清朝,明年我臣服蒙古,都無所謂,但是部落一直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現在是民族國家時代,你要劃界限,立界碑。目前人類歷史就是這個階段,咱們死以后誰知道什么樣呢。
龔: 他需要這樣來界定自己的身份,就像柏林墻。
魯: 原來清朝是大帝國,控制很多部落。如果整個部落歸順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一大塊土地隨之都是清朝的。過了一百年,部落跟著英國跑,跟著俄羅斯跑,那塊地又不是中國的地方了,但他們沒有劃一個邊界。
龔: 現在的研究也只有在我們的這個歷史背景之下進行。
魯: 對。我們不能跳出這個背景。我們看事情需要開闊眼界。咱們通過學術,說一些平常人們不愿意說的話,比如國家消亡,這話說了不犯錯,是馬克思說的,毛澤東也說過,共產主義以后國家要消亡,政黨要消亡。政黨怎么消亡我搞不清,一個社會總要有組織嘛。
龔: 連國民黨現在都成這樣了。
魯: 真是希望有一天國家消亡。約翰·列儂最震撼的一首歌就是《想象》(Imagine),想象有一天國家不存在了。每年新年到來之際,美國紐約時代廣場就放這首歌。歌曲想象哪天沒有地獄、沒有宗教。那完全是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充滿反戰情緒。幾十年過去,這首歌還是最動聽的一首。新年來臨之刻,歌詞傳遞出一種和平的信息給全世界。
龔: 文化完全不一樣。
魯: 昨天我說到美國從小學就教育一個孩子成為美國人。孩子不愿意同學們聽見自己說外文,比如中文、俄文、意大利文。他們要認同英語。美國是非常愛國的國家,這個超級大國有特別強的民族意識,民眾非常喜歡批評自己的國家,而這樣的自我批評也是一種姿態,一種高姿態,自豪感。我們敢于批評自己。美國人越批評自己的國家,越顯得愛國。你看,我們的國家可以隨便自由地批評!但外人批評自己的國家就不行,就不容易接受。我想每個國家都一樣,尤其這種超級大國,民眾意識特別強。
龔: 我們能不能從學術上談一下中美差異的問題,因為我基本是在國內受的教育。您作為海外的學者,您自己感受中國大陸學術研究比較大的問題或者優勢是什么?
魯: 我不敢多說。幾年前我接受李煥征訪談時,說了一些話,后來整理出來,似乎我說了中國電影史學研究有一種零碎的感覺,需要整合一下。我現在回憶,好像當初我沒那么說。中國大陸資金特別雄厚,人員多,機構多,成果多,華語電影研究是最繁榮的,其他地方沒法相比。我原話這么說的,好話一大堆。但是有些人還不能滿足,太敏感了。
我個人覺得個人獨立思考比較重要,而不是一個新話題出現后,大家一窩蜂上的造勢。但這也不容易,電影不像研究唐詩宋詞,它的共時性非常強,你不能關上門研究。比如說,一個人在家里反復思考研究了三年,想通了一件事,然后把自己的心得拿出來給大家看。但什么東西傳到國內馬上就不新了,一百個人來談這個事,而且不加引用。一個人好不容易琢磨出來的觀點,一到國內,嘩的就完全被人接受了,炒作太厲害。
龔: 其實大家沒有心平氣和來做自己獨立的研究。
魯: 國內信息傳播特別快。兩年前我和國內同行在復旦大學有個華語電影討論會。有學者說:怎么一亮底牌都是海外人的底牌呢?“華語電影”“文化中國”這些話語怎么都是海外人的底牌呢?中國自己的底牌在哪?
龔: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國內的學者一直在試圖去尋找,為什么李道新會有那么強烈的反應,他其實是要尋找一條所謂的中國自己的路,他們喜歡提民族。但是到現在也沒有看到,不能說這就是最好的,我們也希望提供其他的路徑。
魯: 我是比較文學出身的。在中國比較文學界,有這種說法:我們要創造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你看中國更大的官方話語,我覺得也很好,不是不贊同。幾個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等等,這也說明問題。但是,也不能動不動批評別人是西方理論框架或西方中心主義。你要總是這種態度,就很少有原創性,就不敢有些新的東西。
龔: 交流可能不是特別順暢。
魯: 對,杜維明先生一個很著名的論點就是“文化中國”“邊緣是中心”。他長期在臺灣和美國。也有人說這個概念也不是他提出的,是南洋華僑最先提出來的。現在大陸接受他的觀點,還任命他為北京大學高級研究院院長。他又娶了中國大陸太太。“文化中國”“華語電影”這一系列概念從外邊傳過來,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好。清華大學汪暉教授研究中國現代性起源,寫出四卷的《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多么厲害。但是他借鑒了20世紀上半葉日本京都學派的思想,說宋朝是中國現代性的起源。中國的原創性自然重要,但要營造一個好的氛圍,產生一種寬松的學術環境,這方面大陸可能要注重一些吧。
龔: 有沒有你們覺得大陸學者完全不同于海外的角度?當然不說特別極端、意識形態想要妥協的一部分。可能海外的學者就不會這樣想,他們還是挺有特別的角度。
魯: 對,他們做東西很扎實。他們研究上海電影史、南京電影史,我們跟他們學到很多東西。上次咱們在南京藝術學院開會,我在一個小組里,坐在旁邊的一位國內學者說得很有意思,他說海外學者跟大陸學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海外學者先有一個理論框架然后往里面塞細節,大陸學者先有細節。
龔: 先有材料是不是?
魯: 好像是,他說的也有道理。這兩種學術方法,就好似哲學思維的兩種不同方法:歸納(induction)和推演(deduction)。一個是從經驗到理念,從特殊到普遍;另一種是從理念到現象,從普遍到特殊。近代歐洲哲學史上,曾有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經驗主義(empiricism)之分別。理論框架在海外學術比較重要,跟訓練有關,我們在海外教學生也是如此。就像在中國教語文,你寫一篇文章,一定要有中心思想。在美國人文學科、社會學科,理論構架一定要有。一篇論文不能弄成一個流水賬,要搭構一個理論平臺。這是不是西方中心主義呢?我覺得也沒必要扯到那里。學者都在努力搭建自己的理論框架,說明一個問題。作為學術,不能死板地重復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要不然你做不出新的成果。我是比較文學出身,嚴格意義上我不是搞電影的。很多人都像我一樣,我們在綜合大學的學術背景下進行訓練和工作,思維方式也是綜合的,而技術方面不那么敏感。大衛 波德威爾談電影就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分析。我的訓練是比較文學,偏重理念,就像你有哲學背景。我不是電影學科班出身,電影工業、產業研究不多,而偏重思想吧。大陸學界現在更多元化。在電影學界里,好像有幾個機構培養了不少人才,比如北京電影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它們各有自己的風格和特點,自己的圈子。不少人擅長史學。我覺得電影史很重要,讓人看到整體而不只是片段。有搞史學的,注重資料和考據;有搞電影批評的,比如北京大學的戴錦華老師。
龔: 她確實是在電影的圈子里有眾多的粉絲。她的研究會給人很多啟迪,我入門其實也是最開始看了戴老師的書,覺得很有意思,包括她講“第四代”“第五代”,可能電影史書都沒她講得明確。做電影史有個問題,資源占有的不均衡。
魯: 有些負面的電影,比如李香蘭演的電影,大家也可以看看,作為反面教材,可以研究嘛。觀眾是有頭腦的,能夠分辨是非,了解歷史真相。
龔: 那個沒問題,我們上課要講的。
魯: 但你不能放李香蘭的東西是不是?
龔: 我們沒有資料,不是不能放。
魯: 對啊,在海外你去買就可以,上亞馬遜網去買。中國買不到李香蘭的電影。
龔: 如果和香港與臺灣電影資料館相比,中國電影資料館對資源的共享程度還有待提高。
魯: 大家應當呼吁資料公開。
龔: 好的,再次感謝魯教授接受我們今天的訪談,我們從“華語電影”開始,結束于對電影資源共享的呼吁,希望給更多熱愛電影、研究電影的人以更便捷和公平的平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