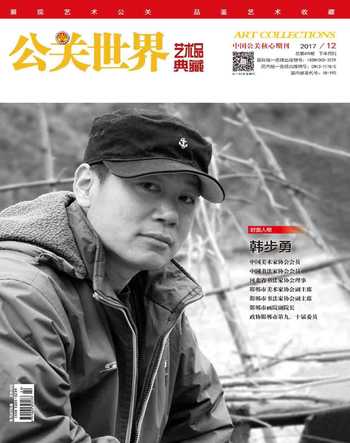巖彩繪畫:中國本土繪畫當代轉型的生長點
張陽
“巖彩是我們老祖宗原有的東西。近些年來,我們習慣中國畫、油畫、版畫、工筆、重彩、水墨等老幾樣,沒有很好地在繪畫材料和繪畫技術方面有所拓展,對于材料本體、材料應用、材料探索乃至在繪畫領域由材料帶動的創作理念、創作樣式、創作風格、語言技巧等諸多方面沒有做過深入的梳理,以至于到今天還未能在專業美術院校中給巖彩一個合理的位置和應有的尊重。”近日,在上海美術學院南院舉行的上海美術學院巖彩繪畫工作室成立儀式暨開學典禮上,中國文聯副主席、上海美術學院院長馮遠這樣說。
巖彩是中國傳統繪畫的精華之一,其歷史文脈伴隨著古絲綢之路綿延相傳。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巖彩畫”這一流傳于古代歐亞大陸經濟文化動脈中的經典繪畫門類獲得新生。上海美術學院巖彩繪畫工作室的成立意味著巖彩繪畫終于結束了20年來徘徊在材料與技法層面的業余狀態,進入了中國高等美術教育體系,這顆蘊含著傳統文化基因的種子正在茁壯地成長著。
以材質為媒介的精神創造
巖彩繪畫是以五彩的巖石研磨成粗細不同的顆粒、用膠為黏合劑調和,繪制在紙、布、板、壁、金屬上的平面繪畫。“巖彩繪畫”這個名稱是在當代藝術語境中,用國際慣例“以材質歸納繪畫種類”的方式對以天然巖石微粒進行繪畫的語言方式的一種稱謂。“巖彩”作為巖彩繪畫的材料,成為了巖彩繪畫豐富的精神內涵和藝術表現的物質載體。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巖彩繪畫工作室主任胡明哲認為,巖彩與其他繪畫材質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巖彩的天然巖石晶體顆粒和色彩呈現具有自然物質和天然本色雙重特性,因此巖彩不只是再現事物形與色的材料工具,而是具有了凸顯自身材質物性和審美特質,并由此喚起審美感受、引申精神語義、表達作品意境的特殊材質。“經由這種獨特的材質,我們可以重新發現腳下的大地,引申出生存危機的覺醒和對文化反思的覺悟。”胡明哲說。
在某種意義上,巖彩成為了畫家內心精神與自然材質深情對晤的媒介,不斷尋找新媒介與材質的過程,也成為了巖彩畫家們尋求情感表達載體的過程。正如美術史家牛克誠在《晤對材質》中所說的:“晤對材質,是對材料的覺悟、體認、靜思與玩味,是對材質認識與把握的一種東方式的思維與感覺。”巖彩材質的天然美感、色彩表現、語言結構和內蘊意味都是巖彩畫家對巖彩材質的心中“意會”,“這種意會結晶到巖彩作品中,即是在實現著一種以材質為媒介的精神創造”。
從畫種到學科,回歸原點的開放性思維
“巖彩繪畫追尋的是中國本土文脈的源頭,回歸的是繪畫語言的原點。”胡明哲說。龜茲石窟壁畫和敦煌石窟壁畫是中國巖彩繪畫語言建構的源頭,當代巖彩畫家與一千年前古代畫師所使用的創作材質、語言要素、語法結構、審美取向一脈相承,油畫的具象寫實模式、中國畫的水墨模式和工筆模式,都不能成為巖彩繪畫的創作基礎,因此巖彩繪畫需要回歸繪畫語言的原點——圖形、色彩、材質、空間,追溯中國巖彩繪畫發生的源頭,自我創建屬于巖彩繪畫完整的語言體系。自巖彩繪畫概念提出至今,經過20多年的實踐,當代巖彩繪畫已經形成了較系統的技法體系和明晰的創作理念,而這也正是巖彩從繪畫門類到學科門類的基礎性條件。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鄭工看來,巖彩畫作為以材料命名的畫種,有其特別的語言系統和表現方式,但繪畫種類與學科門類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相對于學科的規范性而言,繪畫門類的概念沒有明確的規定性。而明確的學科規范對胡明哲所提出的采用開放的態度容納原來不同繪畫領域的人參與進來的理念反而形成了一種制約,如何在保持開放姿態的同時又能夠找到一套學科的規范,推出基本的課程體系,是胡明哲一直在思考和推進的。
巖彩畫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不設邊界,只要是從巖彩出發,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操作方式。“從展示墻上的學生作業中可以看出學生對經典作品的讀解是非常廣泛的,壁畫、重彩、雕塑……古今中外各種繪畫形式都可以作為經典的分析樣本,著眼于內在的形式結構,讓學生通過自己的眼光過濾出黑白灰、點線面等基本的形式構成方式,找到骨架,這是一種返回‘原點的思路。”鄭工表示,“教學上返回‘原點的方式和立足形式構成規律的討論,能夠為創作打開廣闊的思維空間,消解唯一性與神圣性,回到人的個體存在中,激發出人的活力和創造性思維。”繪畫是一個人的事情,但作為一個學科推進則需要一個群體。巖彩繪畫工作室始終堅持的開放性的教學理念和創造性的思維,并正在教學實踐中逐步完善和明晰。
給巖彩一個發展的空間
巖彩繪畫提出后就受到社會各方及美術界的廣泛關注,但褒貶不一,關于巖彩畫的歸屬、中國畫概念的范圍與邊界等問題引發了一系列爭論。學術、專業上認識的不同,使巖彩繪畫始終處在一種漂浮不定的狀態。“巖彩是絲綢之路上一個久遠的藝術樣式,是東方繪畫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它接續下來,重新發揚光大,在上海美術學院未來的發展與建設中應該給巖彩一個空間。”在馮遠看來,中國畫在未來的發展轉型過程中,從教學基礎上應當呈一個開放性的狀態,兼容不同的風格,學校也可以追求自己的辦學特色和教學內容的創新。
“中國文人繪畫的藝術樣式并不能代表中國繪畫藝術樣式的全部,筆墨也不能全部概括中國畫,宋代以前的漢唐繪畫中也有很多經典,應當得到重視。”在談及中國畫的未來發展時,馮遠表示,應當以一種寬闊的胸襟和包容的態度拓寬中國畫的未來發展道路,將巖彩兼容進中國畫的發展。
綜觀中國美術史,中國繪畫的變革都與材料密切相關,材料的變革必將形成一種新的藝術語言和審美價值。中國繪畫從洞窟里、墻壁上走到絹本中,再到宣紙里,中國繪畫也隨之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巖彩能不能帶動中國繪畫下一輪的變革和創新呢?我是寄希望于此的。”馮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