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對你的懲罰
簡·佩克
我在內布拉斯加州的佩蒂中學讀書時,特別癡迷體育運動,尤其是田徑項目,跳高、跳遠、短跑、長跑,都是我最愛的運動。九年級時,我代表佩蒂中學去相鄰的艾奧瓦州參加田徑比賽。原本父母打算開車送我去,但對我來說,這趟旅行是一個放松的機會,我更愿意獨自享受難得的愜意時光,就拒絕了父母的提議,選擇了乘火車前往。
我提前在網上訂了車票,比賽前一晚趕到火車站去坐車。像以往很多次那樣,火車又晚點了,而且整整晚了一個多小時,乘客們都等得很不耐煩,再加上又累又困,情緒開始激動,甚至有人低聲咒罵起來。所以,當火車進站時,乘客們都互相擁擠著一擁而上,想要早一點到自己的位置上休息。
“哎呦!”我前面的一名男子大聲叫著轉過身來沖我嚷嚷,“擠什么擠?腳都要被你踩斷了。”我連忙道歉,并向他解釋,并不是我故意擠他,而是后面的乘客在推搡著我。但是這名男子卻不肯聽,依舊喋喋不休地指責我。我無奈,只好低頭快步走開。心里卻生出了一絲報復的快感,因為剛才男子在叫嚷的時候,我無意中看到了他手里揮舞的車票,上面標注的終點站不是艾奧瓦州,而是莫里斯小鎮,一個與艾奧瓦州方向完全相反的小鎮。是的,他坐錯車了。本來我打算好心提醒他,但看到他如此無禮,我就改變了主意,并在心里暗自得意:這是對你的懲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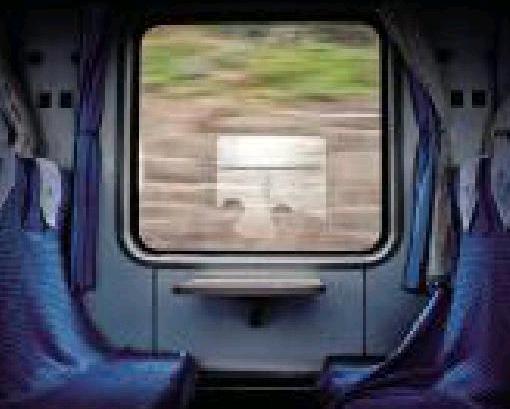
火車并沒有滿座,車廂里還有很多空位置,我就隨便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其實這個位置和那名男子只隔了幾個座位,我想親眼看到他知道自己坐錯車時的尷尬和懊惱。火車開出去半個多小時了,那名男子還在吃著零食,一臉的悠閑和安然,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坐錯車的事實。
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他慌張的樣子,于是起身走到他身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說:“你坐錯車了,現在火車開往的方向與你要去的地方完全相反。”男子一下子跳起來,緊張地掏出車票查看。我忍住笑,靜靜地看著他的反應。這時,男子又向身邊的乘客詢問:“請問現在火車開往哪里?”“莫里斯小鎮呀!”身邊的乘客回答。
什么?莫里斯小鎮?我不可思議地叫道。男子和周圍的乘客都莫名其妙地看著我,不知道聽到這個小鎮的名字為什么要激動。我強作鎮定地對男子擺擺手說:“沒事。”然后回到座位上,心里默默告訴自己:這是對你的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