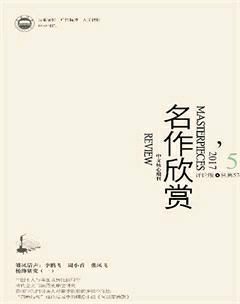清代金文書法歷史地位研究
李思航
摘 要:清代金文書法在清代書法史和篆書發展史中都有著重要的地位,其取得的成就需要重新構建一個書法史敘事模型與之相適應,而擅寫金文的書家在文字學上也有一定的水準。此外,清代金文書法也對20世紀取法金文的書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關鍵詞:清代 金文書法 敘事模型 歷史地位 影響
一、清代金文書法在清代書法史中的地位
清代是書法變革與綜合整理期,金文書法置身其中,一是受到裹挾,二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清代金文書法所取得的第一重大成就是讓金石學從側重于研究文字學、史料學走向了兼顧探討形式美學的道路。“寫金文”成了文字學家和書法家共同關注的命題。眾多文字學家使用金文作為自己在書法創作中的素材,這使得“研究性材料”變成了“生產性材料”。這種取法上的新的突破和閃光,使得清代篆書取得了質的飛躍。
不單是標準的鐘鼎銘文,就連銅鏡銘文也被書家們學習,這也是一大進步。另外,權量詔版這類過去不受重視的材料也成了書家取法的對象,這類材料其實是很有營養的,丁文雋談道:“秦詔版、權量文,雖亦為小篆,然瘦硬方折,與《泰山刻石》不同,是為后世方筆之祖,不可不學。”?譹?訛丁氏雖然將權量詔版劃歸小篆,但也注意到其與其他刻石類小篆的區別。這區別的本質其實在于權量詔版雖然在字形上與小篆接近,但實際屬于金文序列。
到了晚清李瑞清那里,向金文取法則成了改變篆書流于鄧派、千篇一律的靈丹。他“曾將六十多種鼎彝盤敦按器分派,包括殷墟甲骨,共分十派。于各派源流、風格、筆法等都有所論述”?譺?訛。可以想見,李瑞清等書家之所以可以避免淹沒在鄧石如的篆書風格之下,和他們對金文的研習是大有關聯的。
清代金文書法所取得的第二大成就是多樣化的類型構建。“碑學對清代大篆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大篆取法范圍得以擴大,涌現出新的風格面貌;二是碑學的用筆滲透到大篆書法,大篆書法日趨靈活、多變。”?譻?訛
金文書法在清代書家的演繹下,手法多變,風格各異。顫抖、描畫、平鋪直敘、注重水墨都成了書家們用以取得個性化書風的技術。言恭達先生曾說:“書篆貴圓熟,圓熟則使轉靈便,結體熨帖;書篆又忌爛熟,爛熟易俗,難得生意。書篆貴得筆意,避俗去巧,筆少意足,黃賓虹、章太炎之篆筆意甚高,值得細讀。書篆貴淡不貴艷,貴自然不貴著意,貴老重不貴秀嫩,‘秀處如鐵,嫩處如金方為用筆之妙。”?譼?訛清代金文書家正是在不斷上下求索和嘗試技術中逐漸取得了用筆之妙,從而在紙上創造了豐富多彩的金文書法藝術。就清代書法的總體情況而看,傳統文人行草書雖一脈相傳,薪火不斷,但未成為書壇之主流。反而是碑派書法占了上風,篆隸北碑大行其道。金文書法作為碑派書法之篆書中的一員,其地位不可謂不高。但因為篆書,尤其是大篆的識讀難題,使之在書法中屬于“小眾文化”,其社會普及度顯然不如北碑與隸書。而在清代篆書系統內部,鄧石如和其標準化小篆具有教化主的地位,專事金文的書家中卻少有能與之抗衡者。可以說,清代金文書法在清代書壇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也不能過分拔高。
二、清代金文書法在篆書發展史中的地位
鐘鼎銘文既是實用文字,又是書法藝術。秦代以后,篆書退出歷史舞臺,但并未從此消失,在清以前的歷朝書法史上,擅篆書家雖并不繁盛,但各有才人,并未使篆書藝術斷絕,但這一點僅是針對小篆書法而言;相對的,在青銅器銘文藝術退出歷史舞臺的同時,金文書法也在書法史上陷入了沉寂,這主要是由于實物被歷史掩埋,沒有進入人們的視線,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清代。
清代書家使用金文作為創作的素材,使金文書法來到紙面,也掀起了篆書藝術的又一個高潮。但這相隔千年,分別出現在中國書法史兩端的“金文書法”,其功用、技法與書法性質并不相同,我們對其鑒賞時的審美態度也有本質區別。“夏、商、周三代的青銅藝術向我們展示了奴隸社會藝術的風格特點。史載夏鑄九鼎,是奴隸主階級政權的象征。商至西周是奴隸社會的最盛期,這時的青銅禮器,其形制、花紋的設計、裝飾圍繞著一個主題——宣傳奴隸主貴族的‘神權觀念,因此,它充滿了神秘、恐怖和威嚴的格調。這是奴隸主階級的審美理想在藝術中的反映。而作為這時的青銅器藝術的一個組合部分的銘文,其內容為為統治者歌功頌德,書法風格也以凝重、莊嚴而渾樸為主調。這一風格的形成,既有前述這一創作審美意識的主導作用,同時也正與文字及其書法在這個階段以‘象形為書體構形表征的描摹性筆法相適應,從而這時的書法表現技巧的基本特點是生拙、粗獷而圓渾的。”?譽?訛可見,金文書法在產生之初是創制性的,為的是在奴隸制社會的前行進程中取得穩步發展與適于生產(包括熔鑄和手寫)的生存空間,而到了清代,則是創造性的,同樣是為了取得生存空間,但與前者不同的是,清代金文書法所追求的是書家本身的生存空間,所以以金文素材來創造書法圖像就成了這一時期的本質。
金文是中國書法在源頭上的重點研究對象,由于其生產方式是熔鑄和刻畫,使得其和書法形成概念之后的定義——“用毛筆在紙上揮運”形成了一定的矛盾。這導致要想使金文真正納入書法的研究系統,就要追溯其附著在青銅器之前的“書寫”的形態。上古青銅器銘文的書寫狀態于今已不可見,而且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由于正體文字的變化以及青銅器大量被掩埋的諸多因素,導致金文出現了斷層。時間到了清代,在樸學的興盛和大量青銅器出土的推動下,金文成為了清代文人、書家的書寫取法對象,真正走入了書齋,走到了紙上,這讓我們從另一個層面看到了金文的紙面書寫狀態。清代書家使金文書法發揚光大是有其歷史原因的:一方面是由于清代的文化高壓政策,使漢族知識分子將學術精力轉向考據之學;另一方面是書法在清代進入了變革期,文人書法的支柱“二王”一脈的行草書系統逐漸走向末路,書法界急需注入新的“增長點”以增加行業活力。在這些要素的共同驅使下,篆、隸、北碑、楷書逐漸升溫,成為清代書法的主流,而金文書法也借著這股東風,建立了自己在書法史上的地位。
綜上所述,清代金文書法在整個篆書發展史上其實有兩重意義:一是接續了書法源頭位置的金文的衣缽,使其重光:二是使金文納入了書法,避免了金文在文字和書法二者之間徘徊的尷尬局面。在這兩重意義之中,后者顯然更為重要。
三、金文書法的書法史敘事模型
書法史一般都存在一個敘事模型,以此為框,填充具體內容,當新的材料進入視野,或是書法界取得新成就時,模型也隨之變化。當然,清代金文書法加入書法史序列之后,金文書法敘事模型也發生了改變。
拙作《論甲骨文金文形式演進的性質》一文中曾將金文分為八類,即:“1.商代族徽金文;2.西周長篇大論的金文;3.東周后向裝飾化演進的鳥蟲金文;4.兵器金文與錢幣金文;5.權量詔版金文;6.銅鏡、虎符、銅印等上的金文;7.中古以后仿古器物所制的金文;8.現代金屬上的文字。”?譾?訛
以上的分類未見得周全,且聊作一觀。這種分類視角是建立在廣義金文的基礎之上,即對金屬上的文字進行的分類。我們在研究書法史的過程中發現,這八類中的前六類都曾被書法史或詳或略地討論過,也就是說,它們被承認具有“書法的地位”,而不只限于文字。當然,這種地位的確立取決于我們以什么樣的視角看待這些金屬上的文字材料。
在書法史中,金文書法一般出現在商末,終于春秋戰國時代,也就是說其在書法史敘事模型中處于早期位置,但這一部分金文并非狹義書法的涵蓋范圍。狹義的書法概念產生于漢末,伴隨著章草的興起而產生,核心是講求毛筆的揮運。而某些以“字”的形式出現的不論載體與介質的文字藝術最終定性成書法,只能說是狹義書法概念產生之后在廣義層面上對其進行的追認。其實這些或許稱之為“銘文藝術”更合適。
書法的概念產生以后,由于歷史環境的影響(文學藝術的話語權被世家大族所壟斷),很快進入了“二王”時代。這使接下來的一千多年時間里,帖系書法占了統治地位。帖系書法和碑系書法的本質區別在“繼承的維度”上。帖系書法的傳承是“由紙到紙”,而碑系書法的傳承則是“由鑄刻到紙”,清代金文書法尤其是個中典型。
清代的金文書法無疑在碑學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其性質還可以繼續探討。清代金文書法并非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而學習先秦金文,而是在紙面上進行探索。這在紙面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標志著金文的審美與傳承視角之變,即從立體到平面。對于青銅器銘文藝術的理解,不能簡單從拓片角度考慮,也要站在青銅器本身的立場考慮。同樣的行書或楷書字體,大樓之上的廣告牌,效果絕不同于紙面上的書跡,這是三維立體與二維平面的區別。清人對青銅器銘文,或拓片的臨摹所產生的金文書法正是一種“由立體到平面”的繼承,這是清代金文書法所走出的第一步。第二步則是“由平面到平面”。當早期的清代金文書家通過探索將銘文藝術轉化成書法作品以后,這些作品便成為后來書家的取法對象,這樣便又進入了帖學范疇,歸復到一種由平面到平面、紙到紙的繼承關系上去。我們看清代的金文書家,在臨摹金文的時候絕少有不受前人或同時代書家影響的,這在清代中后期尤其明顯。
拙作《用傳播學視角看清代書法史——對傳統“碑帖兩線模式”的認識》一文曾談道:“清代的碑學書法其實還是帖學,因為是寫在紙上的,而且技術也是采用‘紙面性的,在這些人手中,碑只是一種可供使用的創作素材而已。”?譿?訛這樣說不是要否定囊括著鐘鼎銘文的各種“非紙書法”作為書法的合理性,而是想在另一種角度下探討它們在書法史中的準確位置。
回過頭來看書法史,甲骨文出現—甲骨片被掩埋—金文出現—青銅器被掩埋—小篆出現—秦刻石被掩埋—隸書出現—竹簡和漢碑被掩埋,等等,這是“順向書法史”中的脈絡。我們要注意,在青銅器被掩埋之后,金文是否真正消失。其實或許可以拿金文比作恐龍,青銅器就像化石,隸楷行草就像鳥。眾所周知,恐龍滅絕以后,其化石沉入地下,而一部分幸存者轉化成鳥類繼續延續,直到有一天化石被發掘被人類所認識。這道理在金文上也是一樣,金文被小篆取代之后,青銅器被埋于地下,而一部分金文的元素和基因附身于之后的各種字體而繼續存在,直到清代重生。
最終我們可以大致構建起金文書法的敘事模型,這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部分:1.鐘鼎時代;2.雜器時代——包括權量詔版、銅鏡、虎符、貨幣、銅印、兵器等;3.轉化時代——基因通過字體的演變傳承至隸、楷、行、草諸體中;4.紙面時代——清代金文書法。
四、清代金文研究對學術的貢獻
清代金文學是一門綜合學科,除了由文字學、考據學研究走向書法實踐之外,學者、書家們在研究金文文字之美與書法價值的同時,文字學、歷史學等也同時發展,涵蓋在金文文字中的一切信息要素都成為了可供研究的材料。
清代伊始,金文就進入了文字學家的視野。“被譽為‘說文四大家的段玉裁、朱駿聲、桂馥和王筠等,都曾利用金文來研究《說文》,他們逐漸發現金文不僅可以證補《說文》,而且還可以校正《說文》之誤。”?讀?訛有清一代,古文字學者都在研究著金文素材。可以說,清代金文研究對文字學的貢獻是相當大的。此外,“清代學者在搜集、整理和著錄銅器過程中積累了很多關于銅器選擇、去銹、傳拓和辨偽方面的寶貴經驗。因為有了清代學者克服種種困難所做的努力,今天的研究者才能擁有更多可依憑的材料。”?讁?訛清代金文書家們在金文研究領域取得的成就,正和他們在書法上的實踐相呼應。
五、清代金文書法影響的20世紀書家
清代書家在書法層面上對金文進行的探索對一批在20世紀先后名世的書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書家上承清代金文書法遺韻,又為當代的金文書法創作起了鋪墊作用,其歷史地位值得肯定。
羅爰(1874—1954),字季孺,號悉檀居士,廣東順德籍。清末曾任郵傳部郎中,民國后任教育部參事等職。著有《書法略論》等。羅爰有臨權量詔版扇面傳世,這類金文在被吳昌碩等人取法后被廣泛關注,其作品字形準確,線條自然流暢,且勁道十足。
金梁(1878—1962),字息侯,號小肅、東廬等,浙江杭州籍。光緒三十年中進士,任京師大學堂提調等職。著有《清宮史略》等。金梁的金文書法繼承了直接描摹的手法,其線條流暢,用筆飄逸瀟灑,字取左右傾斜之勢,從容生動而神采動人。
王福庵(1880—1960),又名王福廠,本名,字維季,號福庵,浙江杭州籍。他是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所作《說文部首》影響巨大,是重要的學篆入門范本。王福庵的金文書法字形精確,線條清秀流暢,屬于小篆式類型,總體看來精進古雅。他善融會,將小篆秀美工整帶入金文書寫中,得到既規范又遒勁的效果。
王師子(1885—1950),本名王偉,字師梅,號墨稼居士,江蘇句容籍。多年從事書畫教學工作,治學謹嚴。王師子有《臨秦詔版》傳世。其作線條剛勁有力,頗顯作者筆力雄健,布局參差錯落,卻無甚凌亂之感,較好地體現了這一路金文的神髓。
容庚(1894—1983),本名肇庚,字希白,號容齋,齋名頌齋,廣東東莞籍。著名文字學家,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等職。著有《金文編》等。容庚所寫的是小篆式金文,其筆墨光潤,但在潤澤的外表下,古樸凝重之感卻體現出來,這種意境無疑是內斂的,不通過外在形式強調,而要依靠欣賞者的學識來體味。
王個(1897—1988),本名王賢或作王能賢,字啟之,號個,江蘇海門籍。吳昌碩入室弟子,民國時期曾任東吳大學教授。著有《王個書法集》等。王個的金文非常標準,字形把握到位,結構也十分合理,他繼承吳昌碩在水墨上用力的辦法,干濕潤燥均拿捏得很好,傳世金文書法作品用筆有粗有細,墨色有重有輕,十分精彩。
上述書家所作金文書法形態各異,繼承了清代金文書法的各種類型。如取法權量詔版的有羅爰、王師子;呈現鐘鼎銘文樣式的有金梁、王個;以小篆形式出現的有王福庵、容庚。其實,20世紀取法金文的書家還有很多,這里只是略論一二,這些書家通過自身的努力,完成了對前人成果的繼承和創新,使清代金文書法薪火相傳,不斷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