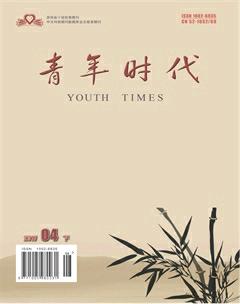中西倫理思想中的友善
賈杰
友善作為人類追求的重要道德品質,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先哲們對友善的論述都非常的豐富,筆者這里主要論述儒家文化、西方啟蒙運動中蘊含的友善思想。
一、儒家與“友善”
在儒家經典中,雖然沒有把“友善”一詞單獨使用,但是在儒家經典中,卻有著諸多有關“友善”內涵的論述,最早體現在親情關系上,包括兄弟關系和朋友關系等。“儒家與友善有著一定的聯系”[1]。
一是仁學思想。孔子認為“仁”是一種境界,擁有仁,就成為了有德性的人。
孔子提倡“仁者愛人”,為儒家仁愛思想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儒家的仁愛思想首先是以愛親人為起步,然后擴展到其他社會成員身上,達到“泛愛眾而親仁”,向普通的人際關系方向發展。按照朱熹的理解,“仁”是人所最為渴盼的,擁有仁是人的本性所趨,達到了仁的境界,則“人皆可以為堯舜”[2]。孔子還強調,“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方面要完善自己的德性,另一方面還要善于奉獻成就他人的德性,即“成人成己”。孟子還提出了著名的人性本善論,以及有名的“四善端說”,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到了宋代又有儒家學者提出“民胞物與”,到最后發展成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3]因此,筆者認為儒家友善思想體現在其政治哲學仁學思想中,通過施行仁政,對其他社會成員賦予仁愛之心,達到社會成員之間友善的目的。
二是和諧思想。孔子指出,“禮之用, 和為貴。”,即禮治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實現和諧。顯然這里已經把和諧作為了人際交往中的重要原則。“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區別,在于君子能夠看到差異,尊重個體差異才能達到協調與統一,而不是強求一致。小人則只看到一致,看不到差異。和而不同,體現的是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達到和諧統一。這一道理同樣適合于人際關系,只有尊重主體差異,施以寬容與理解,則人與人之間才有形成友善局面。因此,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思想,蘊含著友善的內涵。同樣,在國家治理上,孔子同樣主張建設和諧國家,為政者要行仁政,對百姓友善,對其他國家友好,國家才會長治久安,實現天下大同的狀態,這是友善的最高層次。
二、城邦社會與“友善”
在西方文化中,友善同樣有深刻的內涵,是值得發揚光大的道德倫理。在古希臘的城邦社會中,思想家們關于城邦社會需要的德性進行了廣泛探討。特別是亞里士多德的友愛論。
一是友善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古希臘的城邦社會將友善作為最重要的德性,人與人之間需要友愛。城邦之所以能夠存在,原因在于有友愛作為紐帶。在其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還探討過友愛的問題。亞里士多德認為,友愛作為一種重要的德性,是對朋友最誠摯的祝福。他指出,善良的人,具有友愛德性的人,為了朋友、為了父母能盡心盡力,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亞里士多德把友愛分為有用的友愛、快樂的友愛和善的友愛三種,有用的友愛是指彼此雙方都能獲得好處,互惠互利。快樂的友愛則是互相友愛,彼此雙方都能使對方愉悅。亞里士多德認為這兩種友愛,“皆是出于實用性的目的而產生,并且易變且不長久。”[4]。第三種友愛則不一樣,它發生的條件在于在德性相近的人們之間開展。真正德性好的人,會真心地對待自己的朋友,擁有這種德性的友愛,是友愛的最高境界,也是友善品質的最大價值的體現。
二是友愛是愛美、愛善、愛智慧。在亞里士多德友愛的范圍里,不僅包括家庭親情、城邦生活,也包括私人交往、商業伙伴關系等。亞里士多德的友愛論,為人際和諧型社會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寄托。亞里士多德認為友愛就是要認真審視自己,客觀公正的評價自己,特別是正確的認識自己,這是能夠實行友愛的前提。在城邦社會生活中,公民應當具有不浪費、節制的優長,城邦社會之所以能夠井然有序,個體節制行為起到了很大作用。連城邦的立法者們都認為友愛已經大大超過了公正。假如真正做到了公正,其實已經蘊含著友愛。友愛是由多種情感匯聚而成的實踐德性,為了更好的生活,公民應當主動實施自己出于善意的行動,使雙方感到愉悅。這種“利他”的實踐性實質上應該是“互利”的。友愛是交往雙方之間的互動。
綜上所敘,人際交往的友善原則一直都是中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價值追求。友善是人際和諧交往的紐帶。宣揚友善,最終是為了實現社會和諧的目的,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友善是古人的追求,也是現代社會每一個人必備的一種品質,也是社會交往所需要的底線倫理。
參考文獻:
[] 王盛平.中西傳統友善價值觀發展趨勢[J].大觀周刊,2013(1).22-30
[2]許建良.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21
[3] 段江波.友善價值觀:儒家淵源及其現代轉化[J].社會科學,2015(4):139-146
[4]段江波.友善價值觀:儒家淵源及其現代轉化[J].社會科學,2015(4):139-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