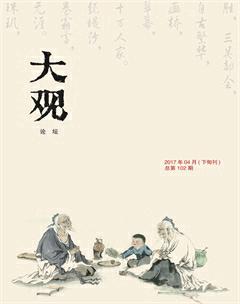東方雅集與西方沙龍的交匯和演變
葉抒明
摘要:文化藝術需要交流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和傳播。當有學問的群體相聚一起,常常探討的內容依然離不開文化藝術。在中國歷來有“雅集”一說,西方也是“沙龍”盛行。本文就東西方的這兩種文化藝術交流形式做一個探討,淺談它們各自的特點和相互的交匯演變。
關鍵詞:文學藝術;交流;交融;多樣化
一、中國古代雅集的形式和雅集圖
“雅集”源自古代,專指文人雅士吟詠詩文,議論學問的集會。此“吟詠詩文”絕非后人背誦前人的現成的詩文,而是指在雅集現場因時、因地、因主題而重新創作詩詞,反復吟詠,最后成稿。比如我們非常熟悉的東晉時期著名的“蘭亭雅集”:永和九年,文人雅士齊聚會稽山下飲酒作詩,創作了37首詩歌,更是成就了王羲之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另外,史上較著名的還有西晉石崇的“金谷園雅集”,唐朝讓王勃一夜成名的“滕王閣雅集”等等。而歷來雅集中人物、地點、行為都很雅,現場還會配有其他雅文化元素諸如:琴、棋、書、畫、茶、酒、香、花等。
回首歷代,古時“雅集”的主角是創作詩文,圍繞的主題是文學,參與的對象是文人雅士。換言之,它只是社會中一小部分群體的活動形式,普及度不高。但是歷代文人都有把這種形式流傳下來,甚至還有很多畫家把它描繪下來,比如明代繪畫大師仇英的《西園雅集圖》,謝環的《杏園雅集圖》等。以“雅集”為主題創作的繪畫作品還有很多,研究它們的學者也不少,不論是否真有這場雅集活動,畫面中描繪的場景都可以作為我們探究當時“雅集”在歷代變化的痕跡和證據。
隨著社會的發展,如今的“雅集”和傳統意義上的“雅集”已經有所區別,其形式、場合、內容也在不斷演變中更趨于多樣化。
二、沙龍的起源與發展
說到“沙龍”,這應該是個外來詞,我印象中最早看到這個詞是“美發沙龍”,不過顯然我要探討的主題不是它,但與之有所關聯。我查了相關資料和文獻,在一篇期刊中看到的這樣一個解釋。在西方文化中,“沙龍”一詞本意為“客廳”,指有知識、有身份的男女人物以言談和娛樂為目的,經常性的非正式聚會活動,一般是在宅院的客廳中舉行,由一個女主人負責邀請和招待賓客以及主持沙龍交談。這種活動最早是在法國興起,最有名的當屬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不過當時舉辦的大多也是文學沙龍。另外,1737年在盧浮宮方形大廳的一次藝術作品展之后人們便也用“沙龍”指稱藝術展覽。這一個含義比“文藝客廳”的所指要晚許多,但是我覺得它對之后“沙龍”的演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美術史的角度上可以這么說。
18至19世紀,法國巴黎官方的沙龍展覽是畫家們向往的地方,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選上在沙龍中展出。這里不得不提到當時的畫家愛德華·馬奈。他受過良好的教育,養成一副紳士派頭,自視清高,熱情奔放,不受拘束,追求獨立自由。他早年曾在沙龍展出《西班牙吉他演奏者》,在巴黎畫壇上嶄露頭角。他的畫具有古典造型基礎,又有明亮鮮艷、光與色的整體表現,仍保持著形象的真實感。但之后他參展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沒有入選沙龍展,于1963年在落選沙龍展出,當時在巴黎了引起軒然大波,并遭到拿破侖三世和輿論的攻擊。可以看出他雖然反對保守,但同時又希望得到官方沙龍的認可。擁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馬奈一個,很多印象派畫家都是如此。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座落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法國巴黎的巴提約爾大街的蓋爾波瓦咖啡館成了他們釋放熱情,大膽言論的好地方。那時馬奈、莫奈、西斯萊、德加、塞尚、畢沙羅等等印象派大畫家都常常聚集在這里,而馬奈是他們談論意識的領導人物。在咖啡廳里,他們可以毫無顧忌的表達自我——關于與作為權威但完全僵化的、提供藝術方面培訓和職業規劃的學院和沙龍的爭議,還有自己對于藝術的準則和目標,總是始終圍繞著“藝術”這個主題。另外,作家左拉在小說《作品》里寫過這家咖啡館,用的名字是“博德坎咖啡館”。其實當時還有關系比較密切的如攝影師納達爾、詩人兼馬奈的好友波德萊爾都常光顧此地。這也說明的了當時的文、藝界交流甚多,漸趨一體。而法國當時“沙龍”的主題不再是純粹的文學,而是有著各類人才的文藝沙龍,包括藝術,甚至說當時的“藝術沙龍”非常盛行,成為藝術家們交流想法獲得靈感的重要方式,這也預示著日后“沙龍”在各方面更加多樣化的趨勢。
同樣的,圍繞這樣的活動,印象派畫家們也留下了不少作品。單單馬奈就有好幾幅,如鋼筆畫《咖啡廳》和油畫速寫《喬治·摩爾在新雅典咖啡館》。后者也說明不止蓋爾波瓦咖啡館是他們聚會的場所,換言之,類似咖啡廳這樣的場所是比較適合開展沙龍的的地點之一。而這亦反映出西方“沙龍”于演變過程中,在場所選擇上的變化。
三、雅集和沙龍的交匯演變
走進近代,隨著中國與世界接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沙龍”傳入中國,并與中國傳統的“雅集”相互交融演變,它們的界限也似乎變得模糊。類似的活動舉辦者很多,值得一提的是林徽因舉辦的“沙龍”,在當時頗具影響力。除此比較有名的,先后還有曾孟樸(真善美書店)、邵洵美(金屋書店)、徐仲年、曾今可、聞一多、徐志摩等人在各地舉辦的沙龍活動。其中邵洵美,對沙龍則有著具體詳盡且高遠的理想,他意圖通過文藝沙龍的倡導,把文藝打進社會里去,一面推廣文藝風氣,一面改良社會,從培育一個“小規模的好社會”開始,進而達到實現“一個大規模的好社會”的理想。在邵洵美眼里,沙龍不再是一種消閑娛樂方式,也不止于引進西潮,而是被賦予了深厚的改造國民性和“文化救國”的意義。此時,這種“沙龍”亦可稱之為“雅集”的活動成為了一種先進文化的象征,一個理想的烏托邦的所在,意義也更為深遠。
雅集和沙龍的交匯演變,至今愈加豐富多樣化,書店、茶樓、公園、咖啡廳等都可能成為活動的地點,討論的話題也不在僅僅是詩詞、文學,還有國內外的藝術、哲學、政治等話題。雅集也好,沙龍也罷,它不在是上流社會的聚會,它的普及有著更豐富的含義和更廣泛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費冬梅.“沙龍”概念的引入和興起[J].社會科學論壇,2015(06).
[2]彼得·J·加特納.藝術與建筑:奧賽博物館[M].劉鑫譯.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