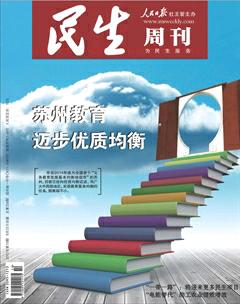為脫貧種下夢想的種子
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只有通過教育才能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他希望自己的介入能為這里的孩子帶來一點改變,助學活動能在孩子們的心里種下一個夢想。
再過兩個月,陳濤就要結束在池溝村的任期了。作為中國作家協會選派到甘肅省臨潭縣冶力關鎮任職的池溝村第一書記,他在這里工作、生活了兩年。
對于陳濤來說,離開熟悉的北京,繁華的都市,來到這個藏族村落,他首先要面對的便是孤獨,語言不通,遠離家人。而離別之際,他又舍不得,放不下這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這里的孩子。
“看到那些孩子眼里的光,瞬間會覺得心靈得到凈化。”陳濤說,在池溝村任職的日子里,助學成了他重要的工作之一,他希望通過教育,為這里脫貧做些事情。
沒有圖書的圖書室
“池溝村的學校是建得很漂亮的。”陳濤剛到池溝村小學的時候,還有些意外,三層的教學樓,蓋得很好,學校的硬件不錯。他了解到,原來的老學校很破舊,這里是易地搬遷點,樓房都是新建的。
但陳濤走進圖書室后就失望了。一間大房子,卻沒有擺上圖書。只在墻邊堆著幾摞書,已經布滿灰塵。這些書大概一二百冊,都是一些經典名著之類,并不適合小學生閱讀。這樣的圖書室自然沒有學生光顧,成了一個擺設。
到任后半年多的時間里,結合自己抓黨建、促扶貧的本職工作,陳濤陸續走訪了冶力關鎮的所有學校——6所小學(其中5所村小學)、3所村幼兒園。他發現這里教育條件十分簡陋,學校普遍缺乏圖書和文體教具,廢棄輪胎是孩子們為數不多的玩具。
每次看到孩子們在村口布滿垃圾的河溝中打鬧,看到他們推著輪胎奔跑嬉戲,陳濤都有些難受。在他看來,所謂教育,不僅在教,更在育,一個健康的孩子,應該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但是,這里卻極度缺乏美術、音樂、舞蹈、體育、文學以及幼兒教育的師資和基本設施。
“村民的貧與愚,鄉村教育最關鍵。不懂農村,難以了解中國,不注重鄉村教育,則難以發展農村。”陳濤說,“對于冶力關的孩子們而言,學校教育還有另一重意義。因父母失位而不能給予的親情,除去長輩的照顧,他們更需要學校、老師的教育與關愛。”
這幾所學校加起來共有305個孩子,多是留守兒童。他們的家基本都在山上,家中老人年邁有時無法送他們上學,就只能自己去學校。高原天氣多變,時常會遇到雨雪天,孩子們踩著泥濘的山路,等到了學校時全身常被泥水裹滿。因為貧苦,他們一年換不上一套新衣服,他們分不清很多蔬菜與水果,因為沒見過,譬如甘蔗、火龍果。
陳濤想為這些孩子做點事情,他決定去做一場幫助學校、教師和孩子們的助學活動。
酸甜助學路
助學并不是簡單的捐錢捐物。陳濤知道,這些年來,也偶有一些組織給孩子們寄了一些物品,但真正能發揮作用的則少之又少。“這里的村民雖然貧苦,但自尊心都很強,我們不能好心辦壞事。”
經過幾個月的調研之后,陳濤得到了相對完整的信息,于是創建了冶力關助學平臺,并初步組建了由學校領導、鎮政府干部、村干部組成的助學小組。
2016年3月12日,冶力關助學小組在微信平臺發布倡議。十多天時間里,他們便收到了多批捐贈物資,100多個包裹。此后,來自全國各地的郵包陸續寄到。上千件玩具、文具、衣物以及上萬冊圖書紛至沓來。
收包裹、統計物資、分配,各項工作十分繁瑣,但每一件物資背后都是一份愛心與信任,陳濤絲毫不敢懈怠。對每一件、每一批物資,助學小組都做了詳細的統計,并及時公布物資的接受和分配情況,捐贈人可以及時查看,當地有關部門可以隨時監督。
但他還是聽到了很多刺耳的聲音。有人說他在不務正業,到池溝村扶貧,卻花力氣在整個冶力關鎮助學。“池溝村小學怎么容納得了這么多物資呢?”陳濤告訴《民生周刊》記者,鎮上其他學校有的條件更差,他也不忍心不管他們。
也有人批評他是在作秀,所做的一切無非是沽名釣譽,為自己的臉上貼金。“這些言語的確對我有影響,但是又都覺得不重要,因為我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陳濤說。
在他看來,一個成功的助學活動,一方面要讓學校、教師與孩子們獲得教學設施的完善與物質上的豐富,另一方面更是傳播一種教育的理念。通過圖書館的創建與完善,從而培養孩子們閱讀的習慣;通過玩具的豐富充實,從而注重孩子們體質的鍛煉與天性的拓展;通過書法與美術作品的布置,從而提升孩子們關于傳統與審美的興趣及能力。這一切,都是僅僅依靠課本很難達到的。
由于真正適合孩子們的圖書增多,他們借閱圖書的興趣也就大了,有的學校還計劃開設閱讀課。陳濤特意到各個學校的閱覽室看過,圖書借閱記錄明顯多了起來。
遺憾與希望
讓外面的老師走進來,帶當地的老師、學生走出去,也在陳濤的助學計劃中。
2016年5月25日,陳濤接待了到池溝村助學的“大秦嶺書畫采風團”的近40位作家、書法家、畫家、攝影家。采風團成員們多數已年過半百,長途跋涉,趕到池溝村小學和孩子們游戲、談心,為孩子們講解書畫文化淵源、發展歷史,書畫家們還當場創作了多幅作品贈送給池溝村小學。
“我確實想邀請更多的兒童文學作家、幼兒教育專家、老師到這里來講課,也想帶著這里的老師、學生到外地去學習、交流,開闊他們的視野。”陳濤說,他還為此做了詳細的計劃,但最后都沒有實現。
即將離任,陳濤為此感到很遺憾。“一個是費用問題,請外面的老師進來,要花錢,我沒有這方面的經費。帶老師、學生出去交流,不但需要錢,還要經過當地教育部門批準,很難溝通。”
去村里的學校跟孩子們一起活動時,他對孩子們說,“希望你們長大了,能去北京上大學,到時候來找我。”
陳濤不知道這個心愿能否實現,這個地方高考錄取率目前還很低,教育質量堪憂,教育方面待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多。但他知道,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只有通過教育才能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他希望自己的介入能為這里的孩子帶來一點改變,助學活動能在孩子們的心里種下一個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