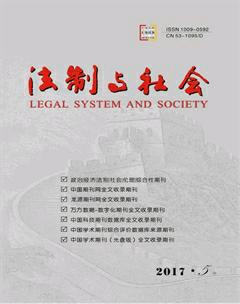論彩禮性質(zhì)與信賴保護(hù)
摘 要 婚前的彩禮贈(zèng)與通常被視作附條件的贈(zèng)與,在婚約被解除時(shí),贈(zèng)與人享有財(cái)產(chǎn)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然對(duì)于彩禮贈(zèng)與到底是附生效條件亦或附解除條件的贈(zèng)與,該條件所指的婚姻究竟為法律婚姻亦或事實(shí)婚姻,各國立法例與理論界不無爭(zhēng)議。就彩禮贈(zèng)與的性質(zhì)而言,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而應(yīng)區(qū)分討論;而事實(shí)婚姻解除后彩禮的返還問題,雖然在我國立法上仍處于空白狀態(tài),但不能以單純的財(cái)產(chǎn)法去解決具有親密關(guān)系屬性的婚姻法問題,此處或可引致信賴保護(hù)原理以減少司法的機(jī)械性與隨意性。
關(guān)鍵詞 彩禮返還 附條件 行為 事實(shí)婚姻 信賴保護(hù)
作者簡(jiǎn)介:傅樂天,南京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研究方向:民法學(xué)。
中圖分類號(hào):D920.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190
一、 彩禮贈(zèng)與的性質(zhì)探究
(一)附條件的贈(zèng)與
彩禮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與深厚的社會(huì)基礎(chǔ)。古代婚姻所講究的“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qǐng)期、親迎。其中,納征與今日的彩禮無異,是指男方在婚前需向女方給付一定數(shù)量的聘禮。聘禮在作為一種情感表征方式的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男方家庭的物質(zhì)基礎(chǔ)。
在今日的法律語境下,彩禮被視作附條件的贈(zèng)與,但該條件到底是生效條件或解除條件,不同的立法例與理論學(xué)說卻不無爭(zhēng)議。
史尚寬先生指出:“證明婚約的成立并以將來應(yīng)成立的婚姻為前提而敦厚其因親屬關(guān)系所發(fā)生的相互間的情誼為目的的一種贈(zèng)與 , 它是一種附有解除條件的贈(zèng)與 , 它具有普遍無償贈(zèng)與所不具有的特性 。” 解除條件說乃立法通例與學(xué)界通說,該說認(rèn)為贈(zèng)與人所附的條件為“婚約被解除”,當(dāng)該條件成就時(shí),贈(zèng)與便失去效力。但在德國、美國等國家,彩禮被視作附生效條件的贈(zèng)與,即贈(zèng)與行為僅使受贈(zèng)人獲得財(cái)產(chǎn)的占有,其所有權(quán)仍歸贈(zèng)與人,待婚約被履行時(shí)所有權(quán)得以移轉(zhuǎn)。
鑒于立法與理論的分歧,本文將在我國的立法模式下,從贈(zèng)與允諾與財(cái)產(chǎn)交付兩個(gè)行為分別討論彩禮贈(zèng)與的性質(zhì)。
(二)附條件的贈(zèng)與合同
如果我們承認(rèn)物權(quán)行為的獨(dú)立存在,那么一個(gè)贈(zèng)與行為將被拆分為兩部分:首先是贈(zèng)與允諾,即贈(zèng)與合同的成立;其次是贈(zèng)與的履行,即財(cái)產(chǎn)交付行為。前行為乃發(fā)生債權(quán)效力,后行為發(fā)生物權(quán)效力。在附條件的贈(zèng)與中,“贈(zèng)與”既可理解為債權(quán)行為,也可理解為物權(quán)行為,那么所附之條件到底依附于何者,筆者以為應(yīng)該區(qū)分討論。
如果是對(duì)贈(zèng)與合同附條件,就需要明確贈(zèng)與合同的成立與生效時(shí)間。在我國,贈(zèng)與合同通常被認(rèn)為是諾成合同,在贈(zèng)與合意達(dá)成時(shí)即對(duì)當(dāng)事人發(fā)生法律上的拘束力。故在討論彩禮返還時(shí),贈(zèng)與合同顯然已生效。在合同生效的前提下,只可能附解除條件使其失效,而不可能附生效條件使其再次生效,否則將生邏輯與事實(shí)的悖謬。
簡(jiǎn)言之,贈(zèng)與人在此表達(dá)的意思為:“婚約被解除,則贈(zèng)與合同失效。”
(三)附條件的交付行為
本文承認(rèn)物權(quán)行為的獨(dú)立性,但不從中抽象出物權(quán)合同這一概念。也就是說,作為法律行為的一種,物權(quán)行為可以附條件,但附條件之意思同樣須通過債權(quán)行為來表示。
“對(duì)于動(dòng)產(chǎn)物權(quán)移轉(zhuǎn)行為是不能附加解除條件或終期限制的,否則必然產(chǎn)生僅在一定期限內(nèi)有效的所有權(quán)關(guān)系,這無異于否定大陸法民法中的所有權(quán)制度。” 在大陸法系的民法理論中,所有權(quán)的一大特征便是永續(xù)性。如果為物權(quán)移轉(zhuǎn)行為附解除條件,等于是為財(cái)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附加了終期限制,使所有權(quán)的穩(wěn)定性受損,物權(quán)移轉(zhuǎn)行為也就失去意義。
所以,為了盡量不突破所有權(quán)的固有概念,在交付行為層面,認(rèn)為所附條件是生效條件更有利于理論體系的維護(hù)。它表明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與占有的暫時(shí)分離,即“婚約被履行,則贈(zèng)與財(cái)產(chǎn)歸你所有”。
但是,我們不能說交付行為在生效條件未成就之時(shí)不發(fā)生任何效力。因?yàn)閺囊馑急硎緛砜矗?zèng)與人所表示的物權(quán)效果意思可被拆解為兩部分,第一層意思是“轉(zhuǎn)移占有”,第二層意思才是“所有權(quán)保留”。交付行為的生效條件僅停止“所有權(quán)移轉(zhuǎn)”的效力,而“轉(zhuǎn)移占有”的效力不受生效條件束縛,在交付時(shí)即生效。
此處仍需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動(dòng)產(chǎn)都可以實(shí)現(xiàn)所有權(quán)與占有的分離。就單純的聘金而言,由于貨幣的“所有即占有”,不存在分離的可能。對(duì)于聘金給付行為,在給付之時(shí)所有權(quán)即發(fā)生移轉(zhuǎn),故只能附解除條件。
(四)彩禮贈(zèng)與的性質(zhì)
經(jīng)上述討論可知,就贈(zèng)與合同而言,附解除條件更宜。而聘金以外的動(dòng)產(chǎn)交付行為,附生效條件更優(yōu)。權(quán)衡比較之下,二者中誰更合理呢?
解除條件說有如下利弊:由于我國采債權(quán)形式主義的立法模式,不承認(rèn)物權(quán)行為無因性,那么贈(zèng)與合同的失效,會(huì)直接導(dǎo)致交付行為的效力瓦解, 故贈(zèng)與人的原物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僅通過為贈(zèng)與合同附解除條件即可得到。但如此一來,交付行為的效力瓦解又會(huì)導(dǎo)致所有權(quán)的失效,這必然對(duì)所有權(quán)概念造成沖擊。而且在解除條件成就之前,受贈(zèng)人為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人,可對(duì)財(cái)產(chǎn)進(jìn)行任意處分,不受贈(zèng)與人限制,這對(duì)贈(zèng)與人是不利的。
生效條件說有如下利弊:依據(jù)《合同法》第186條,贈(zèng)與人在贈(zèng)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移轉(zhuǎn)前可撤銷贈(zèng)與。若采生效條件說,則所有權(quán)仍屬贈(zèng)與人,受贈(zèng)人僅取得占有,不得隨意處分。在結(jié)婚目的不達(dá)時(shí),贈(zèng)與人得行使任意撤銷權(quán)。此時(shí),受贈(zèng)人失去的僅為占有的合法性,不會(huì)貶損所有權(quán)的永續(xù)性。但是生效條件說面臨的困境是,《物權(quán)法》第23條規(guī)定動(dòng)產(chǎn)權(quán)利自交付時(shí)移轉(zhuǎn),未留下“當(dāng)事人另有約定”的空間。而所有權(quán)保留只在《合同法》“買賣合同”一章中有所規(guī)定。那么,贈(zèng)與合同是否可以適用所有權(quán)保留呢?
筆者認(rèn)為,允許贈(zèng)與合同適用所有權(quán)保留,乃尊重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同時(shí)也不會(huì)威脅到物權(quán)法定原則的存在,故應(yīng)予認(rèn)可。
綜上,贈(zèng)與人的原物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通過附解除條件或生效條件皆可得到,前者的路徑是通過解除條件成就來否定贈(zèng)與合同的效力,進(jìn)而否定受贈(zèng)人的權(quán)利;后者的路徑則是通過任意撤銷權(quán)否定受贈(zèng)人占有的合法性。在承認(rèn)贈(zèng)與合同所有權(quán)保留的前提下,從理論體系維護(hù)和贈(zèng)與人的物權(quán)保護(hù)出發(fā),對(duì)于聘金以外的動(dòng)產(chǎn)彩禮,可采生效條件說。而聘金不存在物權(quán)保護(hù)的需要,故應(yīng)采解除條件說。
二、事實(shí)婚姻的信賴保護(hù)
(一)事實(shí)婚姻解除后的彩禮返還
我們?cè)谏衔挠懻摿瞬识Y的性質(zhì)后可以得知,婚約是否被履行,直接決定了贈(zèng)與人是否享有財(cái)產(chǎn)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那么,“婚約被履行”所指的婚姻是法律婚姻還是事實(shí)婚姻?
在討論該問題之前,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事實(shí)婚姻的構(gòu)成要件。本文認(rèn)為,事實(shí)婚姻指男女雙方在不違背我國《婚姻法》有關(guān)結(jié)婚的實(shí)質(zhì)要件的前提下,未辦理結(jié)婚登記手續(xù)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情形。“以夫妻名義”包括雙方訂立婚約、舉辦婚禮等行為。彩禮贈(zèng)與之后,男女雙方已達(dá)成婚約,只要不違背實(shí)質(zhì)要件,此后的共同生活應(yīng)被界定為事實(shí)婚姻。
我國《婚姻法解釋(二)》第10條第一款規(guī)定:“當(dāng)事人請(qǐng)求返還按照習(xí)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予以支持:(一)雙方未辦理結(jié)婚登記手續(xù)的;(二)雙方辦理結(jié)婚登記手續(xù)但確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給付并導(dǎo)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可以看出,該款第一項(xiàng)未周延討論的情形是:雙方未辦理結(jié)婚登記手續(xù)但形成過事實(shí)婚姻時(shí),彩禮是否需要返還以及返還多少?
由于立法的空白,各地法院對(duì)該問題的處理方式也顯得紊亂不堪,或是機(jī)械地認(rèn)定只要未辦理結(jié)婚登記手續(xù)一律全部返還,或是在部分返還的數(shù)量裁定上充滿隨意性。
從比較法視角來看,1928年5月21日,日本京都法院做出判決指出,“事實(shí)上的夫妻共同生活只要開始,交付訂婚禮品的目的就已經(jīng)完全實(shí)現(xiàn)。”然而1935年10月15日,最高法院卻指出,“事實(shí)婚姻雖然已經(jīng)成立,但由于持續(xù)期間比較短暫,且雙方感情不合,訂婚禮品之增進(jìn)雙方情誼之目的沒有實(shí)現(xiàn)”,因此,受贈(zèng)人應(yīng)該返還贈(zèng)品。此后,神戶、弘前法院在事實(shí)婚姻只持續(xù)了一個(gè)多月的案件中,均支持了返還的請(qǐng)求。
在國內(nèi)理論界也有觀點(diǎn)認(rèn)為,持續(xù)時(shí)間過短的事實(shí)婚姻在解除后,彩禮仍需返還。在彩禮無需返還的情形中,夫妻雙方的財(cái)產(chǎn)由于長期共同生活已經(jīng)混同,起初的彩禮作為共同財(cái)產(chǎn)已被夫妻共同消耗,此時(shí)讓受贈(zèng)人返還彩禮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在未同居或者同居時(shí)間過短的情形中,由于雙方未形成共同財(cái)產(chǎn)以共同消耗,彩禮返還仍具有可行性。
這種觀點(diǎn)具有一定合理性,也能說明“雙方辦理結(jié)婚登記手續(xù)但確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下,彩禮應(yīng)該返還的原因。但按照這種觀點(diǎn),夫妻雙方在訂立婚前財(cái)產(chǎn)協(xié)議的前提下共同生活多年后離婚,此時(shí)雙方并未發(fā)生財(cái)產(chǎn)混同,故受贈(zèng)人仍需返還多年前接受的彩禮。這種處理方式顯然不合情理。
解決婚姻法的相關(guān)問題,親密關(guān)系是不可回避的要素。上述觀點(diǎn)所犯的錯(cuò)誤是以純粹的財(cái)產(chǎn)法視角去處理婚姻法問題,卻忽略了彩禮贈(zèng)與旨在“敦厚情誼”的目的。本文認(rèn)為,為了減少司法裁判的機(jī)械性和隨意性,我們或可引致信賴保護(hù)原理來思考彩禮返還的問題。
(二)信賴保護(hù)
信賴保護(hù)原為合同法上的概念,它旨在保護(hù)當(dāng)事人因信賴要約或合同而為簽訂合同所導(dǎo)致的財(cái)產(chǎn)損失及與他人訂約的機(jī)會(huì)喪失,其救濟(jì)手段包括期待利益損害賠償和信賴損害賠償。 合同法上的信賴保護(hù)范圍僅限于財(cái)產(chǎn)損失,對(duì)當(dāng)事人所附加的注意義務(wù)也多為商業(yè)道德。若要將信賴保護(hù)原理引入彩禮返還問題中,意味著不得不對(duì)信賴保護(hù)的內(nèi)容進(jìn)行擴(kuò)充。
本文認(rèn)為,信賴原理的本質(zhì)是賦予當(dāng)事人善的行為義務(wù)。這要求我們的法院在裁判彩禮糾紛案件時(shí),不能機(jī)械地以贈(zèng)與所附條件是否成就來決定是否返還,而要充分考慮當(dāng)事人的信賴投入,以及當(dāng)事人對(duì)于婚約未被履行這一結(jié)果的過錯(cuò)。
第一,在是否返還這一問題上,由于彩禮是附條件的贈(zèng)與,故可類推適用《合同法》第45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當(dāng)事人為自己的利益不正當(dāng)?shù)刈柚箺l件成就的,視為條件已成就;不正當(dāng)?shù)卮俪蓷l件成就的,視為條件不成就。” 若贈(zèng)與人存在惡意,如欺詐、惡意毀約等行為,哪怕雙方同居時(shí)間很短或者受贈(zèng)人未遭受實(shí)際損失,受贈(zèng)人亦無需返還彩禮。
第二,在返還數(shù)量這一問題上,要保護(hù)受贈(zèng)人的合理信賴。受贈(zèng)人的信賴?yán)婕劝ㄒ蛐刨嚮榧s而投入的利益,也包括將來與他人締結(jié)婚姻而可期的利益。受贈(zèng)人所遭受的利益損失包括財(cái)產(chǎn)、人身與精神上的損失。若贈(zèng)與人對(duì)婚約解除有過錯(cuò),則受贈(zèng)人可以主張信賴保護(hù),且該信賴保護(hù)須建立在性別差異與當(dāng)?shù)仫L(fēng)俗習(xí)慣的考量上。
比如,在我國傳統(tǒng)習(xí)俗觀念中,婚禮、同居對(duì)于女性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對(duì)外昭示著婚姻成立。如果女方因信賴婚約而與男方舉辦婚禮、共同生活后遭遇男方悔約,這對(duì)女方及其家庭必然有極大的精神損害;再比如,女方因上述信賴而名譽(yù)受損,可能喪失將來與他人成婚的機(jī)會(huì),這在我國的傳統(tǒng)倫理觀下是具有可預(yù)見性的。法院在裁判彩禮糾紛案件時(shí),這些因素都不得不考慮。
注釋:
史尚寬主編.親屬法論.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0.113.
陳群峰.彩禮返還規(guī)則探析——質(zhì)疑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十條第一款.云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法學(xué)版).2008(3).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122.
屈茂輝.物權(quán)法·總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283-284.
張學(xué)軍.彩禮返還制度研究——兼論禁止買賣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財(cái)物.中外法學(xué).2006(5).
馬新彥.信賴與信賴?yán)婵?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