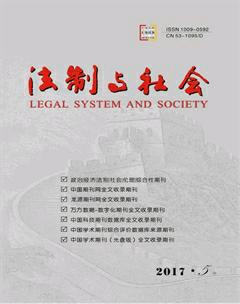未成年人校園暴力行為的刑法對策研究
竹懷軍 張敏玲 陳映明
摘 要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未成年人校園暴力事件通過網絡不斷被披露出來,同時經過各方媒體與社交軟件的傳播,使這些事件不斷發酵,帶來了許多不良影響。校園暴力給未成年人身心帶來的傷害是無法估計且無法修復的,有必要運用刑法手段加以規制。
關鍵詞 未成年人 校園 暴力 法定年齡
基金項目:韶關學院2016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
作者簡介:竹懷軍、張敏玲、陳映明,韶關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229
校園暴力,是世界各國致力解決的一大難題,它普遍存在于各階段的學校中,美國更是直接把校園暴力稱為校園欺凌(bullying)。
世界衛生組織對暴力定義為:蓄意地運用軀體的力量或者權力,對自身、他人、群體或者社會進行威脅或者傷害,造成或極有可能造成 損傷、死亡、精神傷害、發育障 礙或權益的剝奪。① “校園暴力”一詞在我國學界一直沒有統一的定義,直至2016年4月才在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確提到:“校園欺凌”即“發生在學生之間蓄意或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傷害”的行為。《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對于“校園欺凌”中的“傷害”并未作出具體的解釋。姚建龍教授表示:“在實踐中所發生的校園暴力案例, 往往難以把身體與心理的傷害、財產的傷害截然地分離開來。”因此,筆者認為,對校園暴力中“傷害”的解釋,不應該局限于解釋為生理上的侵害,還應該包含財產和心理上的侵害。
一、我國未成年人校園暴力的現狀
(一)普遍化
2016年5月,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對2013-2015年各級法院審結生效的100件校園暴力刑事案件進行梳理發現,在100起案件中,故意傷害罪占57%,故意殺人罪占6%,性侵占12%,其他類型占25%。在本次最高人民法院挑選的100件案件中,持兇器的達到49%,接近案件數的一半。這些未成年人被告人都在上下學途中攜帶彈簧刀、水果刀、獵刀等足以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其中,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占35%,重傷的案件則占32%。②而這些案件,僅僅是在未成年人被告人是在年滿十四周歲以上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八種嚴重犯罪行為才立案處理的案件,那些行為人未滿十四周歲而未達到刑事責任法定年齡而不作立案處理的遠遠大于以上這些案件的個數。
(二)低齡化
2015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針對我國10省5864名中小學生進行校園暴力的調查研究,發現:接受調查的5864名中小學學生,有38.60%的學生表示曾經遭受校園暴力。據搜狐網上一份長期有效的調查問卷顯示:被調查者表示,身邊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有73.32%是發生在初中階段,22.24%發生在高中(中專/職高)階段,4.18%發生在小學階段。③兩份調查均反映我國校園暴力低齡趨勢越來越明顯。
(三)網絡化
從 “連云港電大女生被辱事件”、“ 田家炳實驗中學春藥案”、“ 江西永新女生打人案”再到今年的“廣西思練中學女學生群毆事件”、“北京中關村二小霸凌事件”、“深圳龍華愛義學校初一學生遭圍毆事件”,校園暴力案件近年來在各地校園中頻發,而且通過網絡的傳播,造成嚴重的、惡劣的社會影響。自2015年起,我國校園暴力事件呈逐年遞增的趨勢,而且大部分校園暴力案件都是通過在網絡上的快速傳播,引起網絡熱議從而被關注。隨著智能化時代來臨,信息網絡化趨勢的進一步加深,校園暴力事件的施暴者以及圍觀群眾將校園暴力過程拍成視頻,通過網絡在互聯網上短時間快速、廣泛的傳播開來,從而形成校園暴力噴涌現象。 “網絡校園暴力視頻還導致部分中小學學生形成一種畸形的“炫暴”心理:他們將對弱小同學的單獨或集體施暴過程拍攝成短片,上傳到網絡上,以此在網絡平臺上獲得關注度,甚至通過殘忍的方式凌辱弱小、被孤立的同學,從而滿足自身畸形的快感,或者達到在網絡中得更高的關注度和視頻點擊率的目的。
網絡的傳播是新媒體中速度最快、范圍最廣、輻射人群最大的傳播方式。微信、微博、QQ等通訊工具更是成為未成年人交友溝通、獲取信息、娛樂消遣的重要途徑,五花八門的網絡視頻平臺中新奇的視頻容易滿足未成年人的獵奇心理。未成年人施暴者利用網絡傳播快、廣、高的特性傳播校園暴力視頻,容易給觀看校園暴力視頻的未成年人起到實施校園暴力的心理暗示的消極作用。
二、我國在未成年人校園暴力法律規制的不足
(一)缺乏專門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
迄今為止,我國未有針對校園安全的立法或者對校園暴力行為進行一種明確界定,因此反欺凌、反校園暴力的具體制度或者立法也處于缺失狀態。我國保護未成年人在校園安全的法律條例主要分散在各部法律中,如《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司法解釋等。這些法律條例、司法解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護在校未成年人,維持校園安全和穩定的作用。然而,未成年人犯罪仍在刑法其中被提到仍存在不夠明晰的地方,對未成年人特有犯罪處理的體系仍然缺失,例如并無具體針對校園暴力的刑罰處罰規定。
我國《刑法》第17條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另外,《治安管理處罰法》第12條也規定: 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滿14周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不予處罰,但是應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刑法明確規定,未成年人需負刑事責任年齡是已滿14周歲,這就造成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代價過低,其立法本意是保護未成年人,如今卻變相的鼓動了14周歲以下年齡的人犯罪。而且,在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罰處罰不僅種類過少,而且除收容教養外其他非刑罰處罰方法都不涉及到剝奪自由的問題,也不需要任何勞動教育或其他改造措施。在實踐中往往一放了之,對實施了犯罪的未成年人明顯失去了教育性和懲罰性。
(二)少年法庭“低使用率”
不完善的少年庭制度是我國校園暴力治理的受阻原因之一。在我國,沒有專屬未成年人適用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庭與成人庭無明顯區別。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均未達到生物學上的發育成熟狀態。在庭審過程中,旁人的注視、私語都容易給未成年人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我國法治建設過程中本著教育為目的開設少年法庭,少年法庭審判多采用圓桌會議的形式,減少與案件無關人員的參審人數,旨在能有效的幫助犯罪少年認識錯誤,回歸社會。然而我國各級人民法院中設立的少年庭,很多更是形同虛設。審理未成年人案件,與普通成年被告人的審判庭無異。一方面,導致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心理承受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受害人經過犯罪侵害,難免會留下心理陰影,在庭審過程中容易對未成年人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導致被害人容易心理失衡,出現抑郁的情況。由此可見,無區別地適用成年人普通審判庭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利于未成年人被告人更好更快回歸社會以及未成年人受害人走出校園暴力的陰霾。
三、對規制我國未成年人校園暴力行為的刑法立法
(一)建議降低未成年人定罪的法定年齡
2010年的《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與2005年的調研結果對比顯示: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男生抑或女生,身理生長速度都加快了2-3歲;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至少提前了 2-3歲。當代未成年人無論身理還是心理方面,較之10年前同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都顯得更為早熟。按照我國《義務教育法》第11條規定:凡年滿六周歲的兒童即可被法定監護人送入學接受義務教育。而完成6年的小學學習階段后,未成年人便進入到初中的學習階段,此時未成年人都是已經年滿十二周歲。根據前面提到的數據顯示,校園暴力發生的高發區是初中階段,筆者認為,有必要修改現行《刑法》第17條中未成年人定罪的法定年齡,將現行的刑法規定的限制行為能力人由“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降低為“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相對應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的“不滿14周歲不予處罰”降低為“不滿12周歲不予處罰”。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對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認定做出了新的規定,由原來的10周歲調整降低到8周歲,8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成熟程度和認知能力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所提高。為能更好地尊重這一年齡段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識,適當降低年齡,肯定其從事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的能力,有利于保護其合法權益。民法總則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年齡的下調,是對未成年人生心發育與認知能力提高的肯定,刑法也應該對刑事責任年齡進行符合當代社會的重新評估,考慮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為12周歲。
(二)在刑法中用專門章規定未成年人刑罰處罰
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與成年人都存在不可忽視的差距。因此,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刑法應該以專門的篇章對未成年人的刑罰處罰體系進行構建,細化未成年人刑罰處罰的規定。體現出刑法“教育為主,刑罰為輔”的理念,以刑法的威懾力更好的輔助法治教育的推行。在校園暴力立法方面,可參考韓國2012年修訂的《校園暴力預防及對策法》中對校園暴力的規定,將“傷害、暴行、監禁、脅迫、綁架或誘拐、損毀名譽、褻瀆、恐嚇、搶奪、強制做事(跑腿)”等校園暴力行為進行了明確的列舉,清楚而不易產生歧義,也易于執行。
注釋:
① 唐曉顯主譯.世界暴力與衛生報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19.
② 完善制度強化治理 有效遏制校園暴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校園暴力案件的調研報告.人民法院報(第八版).
③ 校園暴力頻發,誰會是下一個受害者?http://news.survey.sohu.com/poll/result.php?poll_id=90319訪問時間2016年12月26日.
參考文獻:
[1]姚建龍. 校園暴力:一個概念的界定.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8(4).
[2]黃偉. 校園暴力的成因及法律防范.大連海事大學.2012.
[3]王靜. 校園欺凌和校園暴力治理法治化探析.河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