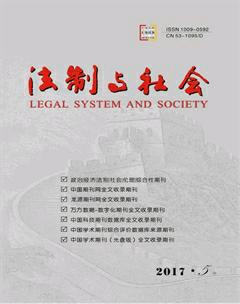遺失物拾得者報酬請求權與我國法律傳統
摘 要 依我國現行法律,如果遺失物的所有權人沒有以懸賞廣告等形式承諾給予遺失物拾得者報酬,遺失物拾得者無權請求報酬。現實生活中,曾有遺失物拾得者怠于歸還或上交遺失物,以期待遺失物的所有權人做出懸賞承諾的事例。這也引發了在立法上確立遺失物拾得者報酬請求權的議論。本文認為法律制度的確立,不能不考慮與法律傳統相吻合的問題。本文圍繞這一問題,考察了我國唐明清以至民國時代的相關法律規定。雖然各朝代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但不妨礙得出遺失物拾得者報酬請求權與我國法律傳統大體相吻合的結論。
關鍵詞 遺失物 報酬請求權 法律傳統
作者簡介:孫振海,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教師,研究方向:民事法律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275
一、 一則案例引發的思考
案例 :
1993年3月30日中午,朱晉華在天津和平電影院看電影。散場后將朋友李紹華委托代辦的內裝洛陽市機電公司價值80余萬元人民幣的汽車提貨單及附加費本等物品的公文包遺忘在座位上。同場看電影的李珉發現后,將公文包撿起,并委托同去看電影的王家平保管。同年4月4日、5日和7日,朱晉華先后在《今晚報》、《天津日版》刊登尋包啟事,表示要“重謝”拾得人。李紹華得知失包情況后,與4月12日和13日也在《今晚報》刊登內容大體相同的尋包啟事,具體承諾“一周內有知情送還者酬謝15000元”。12日晚,李珉得知以李紹華名義刊登的啟事后,即告訴王家平并委托王家平和李少華聯系。次日,雙方在約定的時間地點交接錢物,由于在給付酬金的問題上雙方發生爭執,李珉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朱晉華、李紹華依其承諾支付酬金15000元。朱、李答辯稱:尋包啟事中承諾給付酬金不是其真實意思,公文包內有被告李紹華單位及本人的聯系線索,原告不主動進行尋找,物歸原主,卻等待酬金,法院應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本案一審天津市和平區人民法院,接受被告方的主張,認定啟事中關于支付酬金的承諾非真實意思表示,應屬無效,駁回了原告的請求。二審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沒有充分依據可以認定支付酬金的承諾是非真實意思表示。在此前提下,主持調解,雙方達成協議,由被告方一次性支付原告方8000元。
本案涉及懸賞廣告的法律性質及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問題,對此理論界、實務界早有研究。本文不對懸賞廣告展開討論。本案引起筆者注意的是:為什么原告方3月30日撿到遺失物,遲至4月13日,在被告方屢次發出懸賞廣告、并最終作出具體的支付酬金的承諾后才將遺失物歸還失主呢?如果不需要懸賞廣告的承諾、而是由法律直接承認遺失物拾得者的報酬請求權的話,本案原告還會如此長時間“等待”嗎?
本案原告(上訴人)最終能夠得到一定報酬,依據在于被告(被上訴人)事先在懸賞廣告中的承諾。如果沒有這種承諾,其請求不可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也就是說,上訴人的請求權是一種約定的權利。這就可以理解,上訴人為什么遲遲不愿意和被上訴人聯系,其目的就在于等待這個約定。與這種基于約定產生的權利不同,遺失物拾得者的報酬請求權是一種法定的權利。只要具備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不需要失主的承諾,遺失物拾得者就可以請求失主履行相應的義務。
關于遺失物拾得者報酬請求權問題,就國外的立法來說,即便同為大陸法系的法國和德國,法律規定完全不同。法國民法典完全沒有對遺失物拾得者支付酬金的規定。德國民法典則有比較詳細的規定。依德國現行民法典,遺失物價值在500歐元以下的,拾得者可以請求遺失者支付5%的酬金;超過500歐元的部分,可請求的比例為3%。但遺失物為動物的,其比例一律為3%。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幕府時代的法律就承認遺失物拾得者的報酬請求權。明治維新后,日本門戶開放,大規模引進西方法律制度,于1899年頒布實施《遺失物法》。該法規定遺失物拾得者可請求報酬金的比例為遺失物價值的5%-20%。該法實施一百多年后,于2006年全面修訂,并于次年生效。新舊法對照,雖有重大修改,但報酬金的比例沒有改動。
近年來,圍繞遺失物拾得者的報酬請求權問題,我國法學界也有所議論。眾所周知,植物的移植有水土不服的問題,人體器官的移植有排異反應的問題。同樣的道理,法制建設也存在同傳統文化是否相吻合的問題。如果一項法律規定同傳統文化不相適應,在施行中就會同社會生活發生諸多牴牾,很難發揮規范和協調社會秩序的功能。那么,我國傳統法律中,遺失物拾得者能否獲得一定的報酬呢?本文擬對這個問題做簡單的考察。
二、我國傳統法律對遺失物拾得者報酬金的規定
周禮秋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刑人、奴隸、逃亡者)、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由此可見,早在周朝,拾得東西,就要求上交官府。對于周禮的這一記載,東漢的鄭司農(鄭眾)解釋說:“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 依現存的資料,很難確知漢朝的法律是如何規定的,但由此解釋可推知,漢代必有拾得遺失物送交官府的規定。 當然,無論周朝或漢朝,遺失物送交官府后,最終未必全部歸官府所有。若十日后無人認領,大物充公,小物歸拾得者所有。
唐律雜律規定“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贓重者坐贓論。私物,坐贓論減二等。”條文中的“以亡失罪論”,指拾得官府之物,如寶、印、符、節等,不依五日之限送還者,以官吏遺失官物之罪來論處,其最高刑為杖一百,并須賠償。所謂“坐贓論”,以價值來計算,最高為徒三年。大明律的戶律錢債門“得遺失物條”規定:“凡得遺失之物,限五日內送官。官物還官,私物召人認識。于內一半給予得物人充賞,一半給還失物人。如三十日內無人認識者,全給。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贓論,私物減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給主(如果無人認領,當然全部歸官府)。”《大明律集解附例》纂注對此的解釋是:“夫送官者無罪而給賞,賞其有還人之意也。不送官者不賞而有罪,罪其有隱匿之情也。”大清律沿襲大明律,對于拾得遺失物,也有同樣的規定。由此可知,明清的法律,對于遺失物,區分官物和私物,官物無條件歸還官府,官府也無須充賞。對于私物,如有人認領,一半歸拾得人,一半歸還失主;如無人認領,則全部歸拾得人所有。與明清的規定相比,唐代的法律沒有官府要對拾得人“充賞”的條文。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唐代的法律道德化比較高,“出禮則入刑”的觀念表現的更強烈。
中華民國成立后,在民法典中對遺失物拾得者的報酬請求權做出了規定。至今仍然在我國臺灣地區施行的“民法典”第805條第二款規定“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一;其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單就物質利益來講,依明清的法律規定,遺失物送交官府后,拾得人可以獲取相當豐厚的酬勞。但在法律性質上,這種酬勞不能等同于現代民法上的“報酬請求權”。在明清時代,要由官府“充賞”。現代民法上的“報酬請求權”,是遺失物拾得人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的一項法定權利,可以要求義務人履行。如果義務人拒絕履行,權利人可以請求法院保護。“充賞”更多的體現了“義務本位”的法律觀念,“報酬請求權”更多的體現了“權利本位”的法律觀念。
三、結語
由以上所引各朝代法律可知,在我國數千年的法律傳統中,既有像唐代那樣的高度道德化的法律,視拾金不昧為天經地義,不承認遺失物拾得者可以獲取報酬。也有明清那樣的規定,一方面強調物歸原主,同時又規定拾得者可以由此獲得一定報酬。可以說,物歸原主是不變的天理,給予拾得者一定的報酬是合理的人情。法律遵循天理的同時,也應同時斟酌合理的人情。明清兩代綿延五百多年,時間上又與今天的社會更接近。因此,同唐代的法律規定相比,明清的規定對今天社會的影響可能更為深刻。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法律上承認遺失物拾得者的報酬請求權可能更符合當代社會民情。
拾金不昧始終是社會所提倡的、所推崇的高尚道德。在法律上承認遺失物拾得者的報酬請求權,并不意味著對社會道德標準的降低,僅僅意味著法律不把道德規范簡單的法律化。在社會治理中,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各有其不同的功能,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也不可能簡單的相互替代。遺失物拾得者的報酬請求權,通過在一定限度內滿足拾得者的“利己心”,從而更有效地實現物歸原主、乃至于抑制刑事犯罪的發生,具有積極的意義。
注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5(2).
薛允升撰.懷效鋒、李鳴點校.唐明律合編.法律出版社.1999.735.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下冊).中華書局.1996.1942.
勞政武.古今法律談.(臺灣)民族晚報社.1979.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