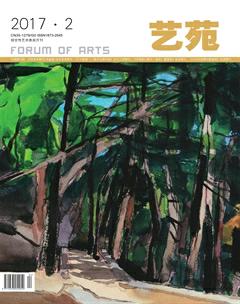敦煌壁畫的色彩構成方式探析
郭旺學
【摘要】 敦煌壁畫具有獨特的色彩體系,是敦煌美學的內容構成要素之一。研究敦煌壁畫的色彩構成方式,有助于更深刻地認知敦煌藝術。本文試圖從宏觀上把握敦煌壁畫的色彩構成特色,旨在通過具體研究來了解敦煌壁畫色彩構成的內在邏輯,深度解讀敦煌壁畫的形式構成因素,為當代藝術創作、設計中對色彩的運用提供借鑒參照,以更好地傳承傳統經典藝術。
【關鍵詞】 敦煌壁畫;色彩;構成方式
[中圖分類號]J20 [文獻標識碼]A
敦煌壁畫是色彩的世界,與中國傳統繪畫水墨體系既形成強烈的對照,又共同構筑起中國繪畫藝術的色彩體系。色彩藝術美學的呈現,在于構成關系。敦煌壁畫藝術的神奇魅力,與這種獨特的構成關系密不可分。正如其它各個視覺要素一樣,色彩不可避免地必須在一種整體系統中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表現力。
一、敦煌壁畫色彩與造型的關系
色彩作為重要的視覺要素,離不開它與形的結合。但從創作到欣賞的不同階段,色彩與造型卻分別起到不同作用。阿恩海姆認為:“接受態度大都是由色彩引起的,但有時也適于對形狀的反應;積極態度多半是對形狀的知覺中所具有的,但有時也適合于對色彩結構的知覺。總的說來,凡是富有表現性的性質(色彩的性質,有時也包括形狀性質),都能自發地產生被動接受的心理經驗;而一個式樣的結構狀態,卻能激起一種積極組織的心理(主要指形狀特征,但也包括色彩特征)。”[1]455這說明色彩能賦予形象以情感、形象及式樣,往往能給人以積極心理,這里造型及形式結構在欣賞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對于創作者,如何安排造型與色彩的優先級,體現不同的藝術態度?西方傳統的觀點始終認為,在形與色的關系中,形是第一位的,色是第二位的。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曾說:“那種能使得輪廓線放射出光彩的色彩,起的是刺激作用。它們可以使物體增添引人的色澤,但并不能使物體成為經得住觀照審視的美的對象。相反,它們卻常常因為人們對美的形狀的需要而受到抑制,甚至在那些容許色彩刺激的場合,它們也往往因為有了美麗的形狀才變得華貴起來。”直到以莫奈為代表的印象派才執著地研究光與色的關系,并把色彩感受擺在第一位,塞尚更是致力于以色彩表現第二自然,認為:“線是不存在的,明暗也是不存在的,只存在色彩之間的對比……色彩越正確,造型也就越正確。”再到后來的表現主義,更是直接以色彩來表現豐富的感情。藝術史證明,不同的藝術流派、藝術家,對造型與色彩都持有不同的態度,且都據此創作出經典的作品。
大量資料表明,敦煌壁畫的創作大多采用在畫底上依“粉本”拷貝、而后勾線、再填色的程序,造型在先,敷色在后。也有部分畫不一定依這個固定程序,是在底色上直接“寫”出造型,如第419窟中的《須達孥本生與薩埵太子本生》中眾多剪影式人物形象,生動有趣,體現出畫師極高的造型能力。但不論哪種方式,敦煌壁畫從創作過程到結果來看,造型仍是最重要的。而造型最主要的手段,是建立在線條的框架之下,以線造型,以形寫神,即使是直接寫繪的形象,也如書法般一揮而就,更重視造型和意趣。整體畫面中,色彩主要起到裝飾、象征的作用,并達到色不礙線的效果。敦煌壁畫從借鑒到成熟,經歷了中西合璧、多元融合,從注重表現體積的“暈染法”、三白法、小字臉等西域式畫法,最終歸于以中原式為主流的畫法,從體積模擬到以線造型,從色彩裝飾到樂舞精神,自然地融入中國傳統藝術血脈,成為中國色彩藝術的范本。所以,敦煌壁畫色彩構成中,造型仍然是第一位的,這既不是畫師的主觀選擇,也不是“古典主義”情懷的普遍影響,而是與敦煌壁畫的傳承方式密切相關,也是潛在追求神韻的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以及宗教繪畫的意義決定了的。
但是,色彩使造型豐富化、感情化,色彩渲染了整個洞窟的氛圍,色彩把信眾的情緒刺激到了極致,而形與色的結合方式,也在隨時代審美而變化。敦煌壁畫作為色彩的繪畫,在中國藝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敦煌壁畫色彩構成的對比方式
兩色相并,必有對比。對比是視覺呈現的必然方式,也是藝術表現的重要手段,其運用方式直接決定藝術表現的效果。敦煌壁畫的色彩效果,也源于宗教藝術審美理想的需要。由于歷史和客觀現實的原因,敦煌壁畫的色彩主要以紅、青、黃、黑、白等色為核心展開,稍做變化,呈現非常明確的色相并置效果。縱覽全窟,突出地表現在互補色、明度等方面的對比。
1.補色對比
互補色對比是色彩構成中最強烈的對比現象,兩種色彩分別傾向于使對方向自己的補色轉變,可以使對比雙方呈現一種有生氣的活動力。敦煌壁畫中最常用的是紅、綠、青等色,成為最典型的補色對比,幾乎貫穿于全部壁畫中。早期以紅色比重較大,自晚唐往后,綠、青色的比重越來越大,甚至占主導地位。據李廣元先生在《東方色彩研究》中的分析,即使現在看到的灰黑色,也是在繪制時加了鉛白的紅色變色而成,與至今鮮艷的石綠色形成紅與綠的補色對比結構,而且對比雙方明度較高。[2]95相對而言,其它色彩只起到陪襯的作用。自隋代始,及初、盛唐的菩薩像中出現少量的金、黃色于配飾,以及尊像的臉、臂等處以代替膚色,直到中唐才出現更多土黃、赭黃、淺黃色及少量的橙色等作為衣服及裝飾物色彩,與少量的藍紫色形成又一種補色對比,使極少量的金黃色憑借微弱的光線在洞窟中熠熠生輝。
2.明度對比
相對于直觀的以色相呈現為特征的補色對比,明度對比比較隱蔽,但它必然存在。明度是畫面最重要的視覺元素,伊頓認為,畫面的表面效果只有在色平面中進行組織才能取得,而建立色平面的首要動機,是必須維持一種單調的整體效果。要維持這種整體關系,就必須把以明暗這一要素為主的色調聚合到主要的色組或色平面中去,使其相互間協調一致。[3]46-47總體來看,敦煌壁畫仍然遵循東方的平面空間傳統,色彩在明度上不是以表現深度為要,也并非相近明度的單一結構,而大體是亮與暗的兩種極色平面的機制,其組合方式也是平面色塊的并置,不存在有序的漸變、銜接,體現的是并置的節奏感。最亮的色彩用到了純白色,最暗的部分用到了純黑色,而處于灰色狀態的其它各色,明度顯示為大量的淺灰或者深灰,并沒有模糊黑與白這對主要色組之間的差別,而是維持了明度兩極化的平面空間,成為強化主色調并使之起豐富作用的色彩。畫面中各種色彩幾乎毫無過渡地散落、拼接在一起,大大增強了畫面直接對比的效果。但隋唐之后的大量經變畫中,由于內容繁密,色彩更為豐富,畫面明度層次整體上又達到了黑、白、灰三個色組。
3.其它對比
在一個色彩系統中,往往包含了全部的色彩因素,各種對比情況多少都會有所呈現。敦煌壁畫中除了補色對比與明度對比較為典型之外,還存在純度、色相、冷暖等對比情況。
(1)純度對比。現存的敦煌壁畫中,除有部分破損外,有大量壁畫保存完好,色彩艷麗如初,在窟頂的各種裝飾圖案中尤其明顯。除因繪制時使用大量比較穩定的如石青、石綠等礦物質顏料外,還有各種紅、黃等色,其高純度的原初設計是主要原因。為了強化宗教震懾人心的效果,高純度的色彩設計具有神奇的效果,也符合自發的“民間”藝術創作的特征。但由于各個色塊處于低純度線條、底色的間隔、襯托之下,以及局部的漸變調和處理,純色直接對比的效果大大減弱,卻使獨立的純色塊顯得更為突出,起到強化形象的作用,例如各種尊像壁畫。
(2)色相、冷暖對比。藝術欣賞中,色相往往會給人最直觀的、持續的映像。敦煌壁畫使用了多種色彩,冷暖傾向明確,其色相、冷暖對比也較明顯,光是千佛圖像中藍色與紅色的對比就同時包含這兩種情況。
敦煌壁畫的色彩對比主要采用平涂、并置的手法,現在看來,即使是注重體積表現的“暈染法”,也缺少非常細膩的色階過渡,總體效果屬于對比強烈、甚至是沖突的。總的來說,如果以九宮格分析法來定調的話,敦煌壁畫總體應當是強補色對比、低長調對比、強冷暖對比、高純度對比以及各種色相的直接對比。我們在這種特定空間中欣賞壁畫時,這些色彩的處理方式不可避免地投射于視覺中,使敦煌壁畫呈現出強烈的、充滿異域的、戲劇性的藝術效果,加強了藝術圖像的識別性,同時更好地實現了宗教宣傳效果。
三、敦煌壁畫色彩構成的調和方式
強對比的畫面會增加表現力,但往往缺少和諧性。令人意外的是,敦煌壁畫的色彩在強對比的同時,實際上仍然做到了統一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線條的分割
根據色彩諧調基本原理,無彩色、低純度色可以使雜亂的色彩統一、調諧起來。敦煌壁畫中大量的黑、白色線條、色塊形象,自始至終主導畫面,不僅恰到好處地起到了色彩諧調作用,還對畫面進行了分割、間隔,使純色塊有了對比的緩沖,并使壁畫呈局域化布局。
2.重復的手法
敦煌壁畫的形式構成中,大量出現重復式的視覺元素,使靜止的畫面動了起來。例如飛天中翩翩飄動的線條,裝飾圖案的序列化排列并置,富有節奏感的千佛畫,連環故事畫中重復的人物、山頭、樹木、建筑等。即使是大型經變畫中,其對稱、象征性或程式化的構圖安排,使畫面形成諸多規則化的處理單元,其色彩也因這種點、線、面的構成、均化布局形成一種視覺的平衡狀態。即使是高純度、強對比的色彩,在這種重復中也容易被統一、聯系起來,最終使色彩滿壁呼應,形成音樂般的節奏感。
3.色調處理
由以上所知,敦煌壁畫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注重使用不同的色彩傾向,例如早期以紅色為基調,中期對比絢麗,晚期一派清冷。在每個不同時期洞窟中,也因壁畫主題內容不同而形成局部的色調化處理。這種利用單一色為主色而形成色調的處理手法,雖沒有臨近色那樣統一化,但色調感是極其明確的。
4.同時對比的視覺平衡
如前所述,敦煌壁畫中最突出的對比方式是互補色對比,幾乎充斥整個洞窟。按照伊頓的觀點,互補色是色彩和諧布局的基礎,遵守這種規則便會在視覺中建立精確的平衡。互補色在畫面中既可以保持相互的色彩強度,又可以因為在視覺中由于同時對比作用相互中和成為灰色而滿足了視覺心理的平衡,產生一種靜止地固定形象的效果。[3]57-63這種保持穩定的力量在壁畫中尤為重要。由于洞窟視距較小,且是秉燭閱讀的欣賞方式,壁畫中逐步出現的互補色在使人感到驚異的同時,潛在地滿足了這種視覺生理上對補色的需求,從而達到一種和諧狀態。
5.變色、斑駁化
經過一千多年的歲月,敦煌壁畫大量色彩仍保持如新。但不可避免的是,部分顏料出現了變色現象,如銀朱和粉色變成黑色。再加上近代的人為破壞、自然腐蝕,使現今大量敦煌壁畫盡顯斑駁、滄桑。對于壁畫保護而言,這無疑是不可挽回的傷痛。但從審美而言,恰恰是這種變色現象,使敦煌壁畫形成了第二面貌。這種面貌一方面因變色使舊有彩色降低了純度,或者直接變成無彩色,使畫面色彩顯得更加和諧。另一方面通過殘缺,把過于濃麗、大俗的色彩給統一了起來,也去掉了新畫的火氣,因此形成了一種古拙之美,使色彩渾然一體,和諧、厚重而富有生命力,這種美也許是眾多藝術家終身追求的藝術品格。正如李廣元先生所言:“由于偶然性的自然材料變化所形成的超越,看起來更合于藝術的真諦。”由自發的自由色彩創造,又經過大自然的變化所實現的“雙重自然”,使敦煌壁畫的色彩達到人類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時間所實現的特殊高度。這是東方繪畫藝術除在水墨畫中極端地發展了黑白對比之外,又一獨到的色彩成就。[2]89、94
結 語
敦煌壁畫的色彩構成方式,是在既定的空間格局中,以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動態構成,既反映時代審美,又反映古代中西藝術融合的進程。其色彩表現的豐富性既有原初色彩設計的意圖,又有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更是宗教宣傳的需要。其效果也必然受到欣賞視距、微弱光線、宗教感情的影響。色彩的表現功能主要依附于線條的造型,起到裝飾、象征的作用。色彩構成方式主要是在紅、黃、青、黑、白等大體五色體系中突出紅與綠的強補色對比、黑與白的強明度對比、各色塊的高純度對比;但同時通過色彩的重復使用、線條分割、光線弱化、洞窟色調強化、秩序化構圖排列等手法,加上基于時間的變色、破損等形成第二自然的統一,以及視覺心理的自覺平衡,最終形成濃烈、厚重、神秘、豐富、動感的敦煌壁畫色彩體系。
參考文獻:
[1](美)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視覺藝術心理學[M].滕守堯,朱疆源,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李廣元.東方色彩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1996.
[3](瑞士)約翰內斯.色彩藝術[M].杜定宇,譯.上海:上海美術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