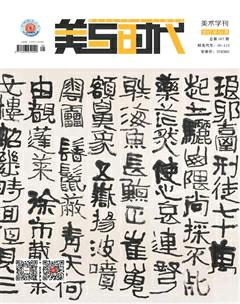劉益之談桂林山水畫
張艷華 方照周 劉國紅
時間:2014-11-27-15:00 地點:桂林廣西師大育才校區北苑
[注:本文系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桂林山水畫發展史研究》編號:YB201031課題階段成果之一]
張景鴻(以下簡稱張師):很榮幸見到劉老,占用您的時間了。桂林山水畫發展史研究課題已經兩年,最初是那次在大瀑布飯店的啟動儀式。后來經過一些調研如收集資料等,發表過幾篇論文,也通過了幾次訪談、座談會采訪過幾位前輩。今天想先由幾位研究生請教您幾個問題。
方照周(以下簡稱方):劉教授好!您作為享受國務院津貼的資深教授,也是當地桂林山水畫的一個重要畫家,我們十分榮幸有機會向您請教。黃獨峰先生是嶺南畫派第二代的重要畫家,他在外學習數年后回廣西,對桂林山水畫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是嶺南畫派跟桂林山水畫的橋梁,您怎么看待嶺南畫派對桂林山水畫的影響?
劉益之(以下簡稱劉師):提起嶺南畫派,原來“二高一陳”是老三杰,而黎雄才,關山月,黃獨峰是“新三杰”中的代表人物,黃獨峰原來是一直跟高劍父學畫,高劍父讓黃獨峰在“南中”任教。因此黃獨峰是嶺南畫派嫡傳,關系比較密切。黃獨峰一生要的目標是:寫生要像高劍父(一樣靈活);用筆要像吳昌碩;色彩要像齊白石;造型要像徐悲鴻(雄渾)。徐悲鴻的畫雄渾大氣。他這個目標基本上也是這么過來的,當然他也有自己的東西。黃到了廣西后稱得上一個旗手。他到廣西藝術學院教學,帶出了不少學生,其為人從藝留下了寶貴財富,我是他(教學的)的助手,帶了黃格勝、陳玉圃。個人關系也很密切。招了兩個研究生。當時還在香港,其間我深受他的教育。山水人物畫家劉錫永,73歲去世。
我59年畢業分配到廣西,在校(湖北美院)時就喜歡山水。那時老師是張振峰、王宰文革受迫害嚴重,張在桂林辦展我出力相助。我凡是藝術上對我有幫助的我就學習。上世紀50年代初,李可染、張仃、羅銘三人一起寫生,辦展,我受此寫生潮流(影響),不管國畫油畫都不靠相機,都現場畫。老一代過世的,像黃賓虹、李可染(的畫)我在校就常臨。羅銘也是嶺南畫派。人問我是什么畫派?我說我是嶺南畫派——重寫生,又把西方的東西吸收,當然還是初期階段。高劍父等人是吸收些日本畫法,撞粉啊,染天,染水呀,都學過來。黃獨峰入嶺南后,感到自己的傳統功夫還不夠深,于是52年又拜了張大千,后來有人改換門庭,(過去,講宗派那是很嚴格的)黃獨峰立場堅定,立足點確立。因為張大千的“大風堂”藏畫可謂富可抵國。進了“大風堂”才可看到,才有機會真正學習到。我到黃獨峰家看他畫畫,這是(學習中國畫)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方法。
黃老1960年從印尼回國,受南亞一帶包括印尼的中西畫風影響很大。他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在合作中學習。你參與了合作,就會拿出來(方法、水平)。過去學武,老師不教,就偷看、偷學。所以我認為,黃老比高劍父一代是超過了的。比廣東的關山月、黎雄才也超過了。這一點雖然陳(樹人)不承認,因有門戶之見。我看過一本陳傳席主編的《空有畫派……》,只字不提(黃獨峰),也是門戶之見。黃獨峰畫冊《印尼寫生》,山水、花鳥都擅長,比黎、關、在用筆、用墨、表現實際上都進了一步。所以,嶺南畫派通過黃獨峰影響是比較大的。黎雄才不但畫漓江,還到周邊去畫。黃、黎、關三人都應在一個水平線上。他們的造型能力是傳統中國畫家所不及的。
黃獨峰這人廣東很多畫家不知道,是由于排斥心理。一山不能藏三虎。兩虎都不能。當廣西知道這情況,就收了過來了廣藝沒有住處,剛到時就住飯店。系里要我第一個去接觸他。到南湖邊,后搬到藝術學院旁。所以嶺南畫派和桂林山水畫,不分伯仲,就是說嶺南畫派對桂林山水畫促進或說是起的是示范作用。
漓江畫派最重要的是寫生,用毛筆、宣紙,其它都不要。為什么?用毛筆、宣紙作畫可以直接鍛煉駕馭中國畫材料的能力,難度很大。但是我不怕難。我的作畫特點是毛筆寫生。這五十,六十多年我就是當場畫,不足的回來慢慢收拾。桂林山水,漓江畫派,應說是畫桂林。我就是畫桂林。我這些年所到之處,都是毛筆寫生。你鋼筆的一條線,回來再變成畫,很難。像李可染、宗其香、陸儼少、唐云、羅銘等(都重視直接寫生)。齊白石畫過桂林,但只是寫意,畫收集素材的速寫。有個北流的人(馮震),是很有文化的人,他邀請過黃賓虹來。但畫北流的,就是喀斯特地貌,共8張小畫。講到外來畫家可以說,來畫的很多,畫的好的少。寫生,過去有成見,雖“三真三假”或“七真三假”,但人家一看就是這地方。具體皴法,就是黃賓虹以后,習慣那一套,習慣了。勾以后,就是點,皴法少。桂林這地方,跟別地方都不一樣,跟太行、華山都不一樣。不一樣在什么地方呢?這不是一般畫家能觀察到的。我就是用整體觀察方法,這個是傳統方法,包括白雪石啊,(傳統習慣),他(的程序)是勾、皴、擦、點、染,這個對于桂林山水一是沒有長期體驗,二,不是整體觀察,整體表現。
桂林山水畫這一名詞(概念),沒問題!我書名就是用過,如《桂林山水畫法》。宗其香寫生是三個基地:桂林、西雙版納、三峽。他是水彩畫家,央美水彩畫主任。是徐悲鴻最重視的學生。徐悲鴻的理念 “西法之可采用者融之”。他的水彩畫在中國是一流的,一生摸索,西方的什么可以融入?我一生體會,整體觀察是最重要的方法,也是最不被人注意的。整體在色彩關系中最重要。傳統要從整體開始,整體觀察是西法中最值得我們引進的。傳統不是這樣,我一看這個山,一眼(看)就知道用什么皴,就因為是整體觀察。傳統是從局部入手。用傳統法畫漓江的為什么不敢畫?那就是沒有整體觀察,所以外地人到桂林,也就十天八天就走了。觀察不到(位)。必須是當地人,長期在這。李可染不畫漓江竹子,他不畫漓江最美者(竹子)。不可能不見到(竹子),因為一是他注重語言,二是他畢竟不是桂林人。所以避開。榕樹、竹、劉海粟、李可染肯定是喜歡的,但(在語言技法上)李主要是擦,發揮素描之長。漓江人,桂林人不畫桂林,遺憾!一直,桂林畫家都認為,桂林山水只用折帶皴,(是誤區。)
整體觀察,油畫最強調。冷暖只有靠對比才能看到和畫出來。我是解放后進的美術學院,接受的是蘇俄繪畫體系。其實,就四個字:整體-局部。實際解決要幾個鐘頭。是因為從整體表現。如搞得很細致,很豐富。徐悲鴻到了以后,一些人一下做不到,就聯合起來反對他。
張師:今天的一代學生都是從素描入的手,但如果國畫創作中不利用這地點,是否是基本資源的浪費?
劉師:就只是過關(高考)為實用學一招。畫不像,就需要整體觀察,明暗、形等要不斷比較。陳丹青搞油畫的,強調寫生。油畫畫色彩。現在畫照片的,色彩肯定單調,因為是從整體中單個切取。我寫生就是用墨。到一定階段,夠,就上色。離開對象可以回來畫,方法可以靈活運用。我寫一千張畫沒有雷同的,因為景物不同。我寫生,往往板凳不移開,一景多角度畫,畫出多張畫。畫派,不管什么派都有可取的。
張:桂林山水的審美特征,您怎樣理解?
劉師:奇秀為主,雄奇有沒有?有。這要根據你的觀察分析。比如獨秀峰雖然不高,但它是號稱“南天一柱”,所以很高。橫看成嶺側成峰,看的角度不同,你高處看、仰看,它的雄、奇、險就出來了,另一角度看又很秀。現實中植被、樹木,茂密了,看上去就秀。你像疊彩山也不高,但上面的建筑稱“拿云亭”。 雄、奇、險、秀、幽、曠,登泰山而一覽眾山小。
張:桂林是水層巖?
劉師:喀斯特地質,基本是橫向紋理,長橫短豎,長豎短橫。經雨水侵蝕,植被長期影響。太行山植被下緊接就是懸崖,懸崖也不過是橫的。你掌握,先是植被,有進去,有凸出,因不同受光,形象就有變化。華山荷葉皴是大關系,但里面還有小的(石頭紋理變化),總之是橫、豎變化。水層巖,一層又一層,經幾千萬年變化,有孤峰,叢峰,九屋山、駱駝山是一種殘峰,現在該崩的崩掉。通過皴擦點染,這種豐富性變化要表現出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就是這么畫。再變化還是要表現。對象沒有固定表現的皴法。河邊水沖原因,骷髏皴出來了。雨淋(墻頭)皴也是。七星巖石頭也有折帶皴。
張:劉老您怎么看桂林山水畫藝術市場,藝術經濟及規范市場的有序化?
劉師: 70至80年代,隨著文革后旅游熱的出現,那時客人買紀念品,帶上桂林山水畫回去最盛行。當然是低價位的。市場上的桂林山水畫是低品位的。要隨社會整體文化發展而發展。西方有西方的需求習慣,要了解。西方掛畫的習慣不像舊中國。一幅中堂,兩旁配對聯。西方(建筑)我看過,中堂根本沒地方掛,只適合小畫。桂林五通農民畫,分工制作,流水作業。要隨人民審美提高而發展。我從不賣畫。
劉:請老師對桂林山水畫發展史研究的課題給點指導意見。
劉師:有本《名家畫桂林》各流派,畫桂林在哪方面去做,總之有審美眼光。不可能是一個模式,是多元。像我是一種。葉侶梅,從廣東來的,畫桂林比較長。首先要有作品。外地人畫桂林、桂林人畫桂林、一直畫桂林的,可歸類。各畫種畫桂林,非山水畫家畫桂林山水的。先搜集作品,再分類。
作者單位:
廣西師范大學
指導教師:
張景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