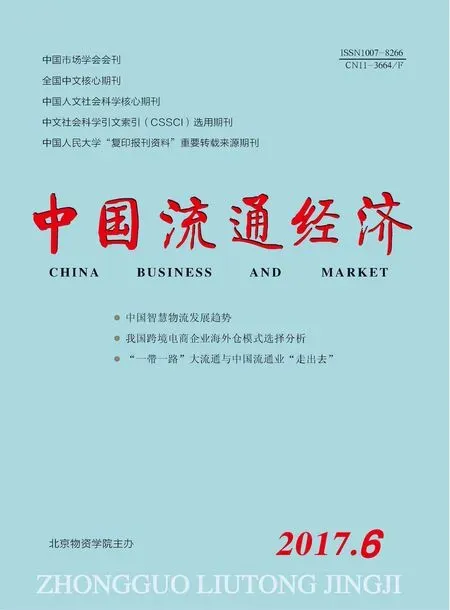股權結構對過度投資行為的治理效應
——基于混合所有制企業異質股權制衡的理論與經驗證據
殷裕品
(北京物資學院商學院,北京市101149)
股權結構對過度投資行為的治理效應
——基于混合所有制企業異質股權制衡的理論與經驗證據
殷裕品
(北京物資學院商學院,北京市101149)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的混合主要通過投資行為來實現,這一過程必然加大過度投資風險,但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對過度投資行為可能產生調節作用,從而約束過度投資行為。根據股東關系假設,如果制衡股東對控股股東發揮了監督作用,則會降低這種風險;如果制衡股東與控股股東之間合謀共同掠奪中小股東,則會加劇這種風險。由于存在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的客觀前提,股東關系會受到資本屬性的影響。控股股東持股在10%~50%區間時,如果控股股東與制衡股東性質相異,第二大股東的制衡變量對過度投資行為沒有發揮監督作用;如果控股股東與制衡股東性質相同,二者都為國有資本屬性時,股東之間的利益行為異化從而產生了制衡效果,表現出“同而不合”,二者都為非國有資本屬性時,制衡變量對過度投資行為沒有顯著影響,股東之間的合謀概率較大。
異質股權;股權制衡;過度投資;混合所有制
一、引言
早在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Berle&Means)[1]就研究了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經濟后果,開創了基于委托代理矛盾的研究領域,即第一類代理沖突;隨后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公司的實際控制權由少數大股東控制,股權集中使得大股東和小股東利益沖突加劇[2],公司治理的焦點同時轉向基于大股東與小股東利益沖突的第二類代理沖突。股權集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委托代理矛盾,但是隨著股權的集中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越發嚴重,那么是否存在最優的股權結構呢?股權制衡理論對這一難題提供了解決方法。法西奧和郎(Faccio&Lang)[3]通過收集歐洲公司的股權數據發現39%的樣本存在兩個以上的控制性股東,16%的樣本存在3個以上的控制性股東,這說明制衡股東普遍存在。貝利德森(Bennedsen)[4]研究了共同控股股東之間合謀行為的形成;戈麥斯和諾瓦斯(Gomes&Novaes)[5]的研究發現制衡股東之間的討價還價問題取決于三個公司特征,其中包括過度投資傾向問題。
繼以上開創性研究之后,學者們主要展開了關于股權制衡對企業價值的影響[6-7],股權制衡對非效率投資行為、過度投資的影響[5]以及股權制衡的影響因素、實際控制人、終極控制人[8]等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無疑解釋了公司治理行為,也為我們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路徑。關于股權治理方面,國內學者主要圍繞股權結構對公司價值、股權制衡對公司價值和過度投資等方面展開研究。其中關于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的關系研究方面,主要從股權制衡、大股東掏空、隧道效應、終極控制權等視角研究公司治理對企業價值和公司業績的影響,但研究結論并不一致[9-11]。企業的投資行為對公司價值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因此很多學者研究了股權結構對非效率投資包括過度投資行為的影響,間接探索公司治理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研究發現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的分離是導致非效率投資的內在動因,而股權性質對過度投資行為存在調節效應[12-15]。以上研究為公司治理行為提供了很好的解釋依據,但是關于股權性質方面,多數研究僅分為國有股和非國有股進行對比研究,或者將終極控制人按國資委、其他政府機構、法人股東、個人、其他,來區別股權性質,并且主要是對第一大股東性質進行區別,很少有研究探索第二大股東的股權性質。
基于上述文獻研究基礎,本文試圖探索第一大股東與第二大股東之間的股權性質因素對股權制衡效果的影響。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之間的混合必然通過資本投資來實現戰略調整、市場收縮和產業升級,這一過程必然提高過度投資風險。但是一個企業存在非常有效的制衡股東,那么過度投資風險會相應降低。根據竇煒等[14]的分析,第一控制人和第二控制人性質相同則樣本劃分到共謀組,若不同則劃分到監督組。本文采用了這一分組方法,并在共謀組基礎上進一步區別(國有股,國有股)、(非國有股、非國有股)組,在監督組進一步區別(國有股,非國有股)、(非國有股,國有股)組。筆者認為,股權性質相同的共謀組未必共謀,而股權性質相異的監督組未必能發揮監督治理作用,這需要通過經驗證據來檢驗股權之間的實際制衡效果。因此本文要回答的問題是第二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過度投資行為的治理效應是否受到股權性質差異的影響,并分析制約第二大股東制衡效果的可能原因,從而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加速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參考。
二、文獻回顧及研究假設
治理(Governance)一詞最早起源于古希臘語,來自于政府對城市的管理、管制背景,后來隨著股份制的出現,公司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公司治理應運而生。伯利和米恩斯[1]最早研究了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后果;詹森和麥克林(Jensen& Meckling)[16]在此基礎上從代理模式的視角研究了所有者和企業控制者之間的關系,奠定了第一類代理沖突的理論基礎。繼詹森研究之后,學者們又從投資者保護的視角研究公司治理[17],這使得公司治理的焦點同時轉向基于大股東與小股東利益沖突的第二類代理沖突。隨后,大量的研究圍繞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及股權集中度對業績的影響來評價公司治理效率,但眾說紛紜,研究結論并不一致。正相關的文獻發現,股權集中度高有利于降低第一類代理成本從而提高公司業績[18-19];負相關的文獻發現,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過高或股權集中度過高時就會產生第二類代理成本,從而造成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害,降低企業效率[17];非線性派認為,股權集中度與業績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我國學者發現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對業績影響是不同的[20],股權集中度與業績指標存在“倒U型”關系[21]。面對公司股權結構對業績的“混合”結果,有學者從大股東獲取私人受益及制衡股東尤其是第二大股東視角研究了股權結構對過度投資等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影響。為獲取較高的私人收益,大股東往往通過延伸終極控制鏈條來分離現金流權和控制權,從而對上市公司實施掏空行為,比如過度投資[9-11,22]。
關于股權制衡與過度投資,梅丹[12]認為,股權過度集中會形成大股東對小股東的掠奪優勢,而制衡股東可以緩解這一矛盾,并用第一大股東與第二到第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作為股權制衡變量,研究發現國有股與過度投資正相關。安靈等[23]運用夏普利(Shapley)指數對股權制衡度進行度量,地方政府控制的企業股東之間利益微弱趨同,而中央直屬和省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權制衡較差。簡建輝[13]將股權性質分為地方政府控股和國企控股、民營控股,研究了不同股權治理環境下的過度投資行為,發現國企存在顯著的過度投資行為。李香梅等[24]直接用第二到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作為股權治理的替代變量研究公司治理對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影響,發現股權制衡具有治理效果。陳志軍等[15]區別了制衡股東類型,研究發現當制衡股東為國有法人和銀行證券基金等關聯股東時,股權制衡效果不顯著,研發投資較差。竇煒等[14]收集了關于終極控制人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相關的數據,并據此研究股東控制權變量對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行為的影響,同時根據第一控制人和第二控制人性質將樣本分為共謀組和監督組,研究發現,監督組如果控制權均衡,那么過度投資會被抑制,而合謀組則加劇了過度投資。
綜上所述,可見持股比例、股東的性質是影響制衡效果的關鍵因素,但目前的文獻對股權制衡持股數據研究較多,對制衡股東性質研究不足,大多數文獻將第一大股東股權性質按照行政管理方式劃分為中央直屬、省政府控制和民營控制組別,或者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對比組,這些研究結論提示我們從行政管理角度排除發揮股權制衡的干擾因素,卻沒有深究制衡股東的性質,即第二大股東的性質與第一大股東性質之間的關系,僅有竇煒等[14]根據第一控制人和第二控制人性質將樣本劃分為共謀組和監督組,因此本文借鑒了其分組方法,在此基礎上根據第一大股東和第二大股東是否為國有資本,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形態下國有資本對制衡機制的治理效果。
根據第二類代理模型,大股東掏空行為的價值損害程度受到控制性股東數量和股東關系的影響[6-7]。當第一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超過50%的時候,對公司擁有絕對控制權,個人私有收益最高從而企業價值相對最低;而存在兩個控制性股東的時候,如果第二大控股股東與第一大控股股東合謀并且顯著地減少獲取收益的成本,那么公司價值將受到進一步的損害,但是如果第一大控股股東獲取私有收益的成本并沒有發生改變且對決策控制權討價還價的能力下降,這時候第二大股東將發揮監督治理的功能,從而間接提高公司價值。隨著控股股東數量的增加,比如三個或者四個制衡力量相當的股東,股東之間合謀越來越困難,第一大股東討價還價的能力受到多個制衡股東的牽制,股權性質和股東特點成為決定私有收益的主要變量。那么哪些股權性質或者股東特點會導致股東之間的合謀或者監督呢?在無法判斷多個控制股東真實關系的條件下,竇煒等[14]根據第一控制人和第二控制人行政管理級別是否相同將樣本劃分為監督組和合謀組,其研究視角對觀察股權制衡效果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但是本文認為,我國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之一是國有企業不僅作為第一大股東,且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占有強勢地位,處于超級大股東地位,與之對應的中小股東往往在國有企業沒有話語權[25-26],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混合后非國有資本不能起到很好的股權制衡作用;同時國有資本與國有資本之間也存在利益分化,不同的國有資本之間可能為了爭奪共同的資源而相互制衡。因此,在考慮股東制衡關系的時候,有必要考慮資本屬性對制衡關系的影響。在考慮第一大股東與第二大股東資本屬性的前提下,可能的股權結構是(國有股,非國有股)或(非國有股,國有股),從理論上分析股權的異質性會增強股東的監督效力,但考慮國有資本的話語權優勢,受國有資本牽制的股權結構很難發揮監督作用。在第一大股東和第二大股東屬性相同的情況下,股權組合可能是(國有股,國有股)和(非國有股,非國有股),從理論上分析股權性質相同股東之間合謀概率會提高,但同樣也可能存在因為爭奪共同的資源或利益分化而產生制衡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為了研究股東之間的交互行為對股權制衡關系的影響,我們根據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將公司持股狀態分為三種情況: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10%時,股權高度分散;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大于10%、小于50%時公司存在多個控股股東,股東之間的制衡關系加強;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大于50%時,第一大股東對公司擁有絕對控制權。在股權相對分散的狀態下,股東之間由于持股比例差異小,個別股東的控制權相對較小,因此股東之間制衡度差;在國有資本參股的企業,國有股完全可以用腳投票,而非國有股致力于效率提高,從而發揮更顯著的制衡作用。在存在多個控股股東的情況下,第一大股東和第二大股東股權性質相異的制衡股東之間監督制衡效果受到國有資本屬性的影響;股權性質相同的股東之間的合謀行為同樣受國有資本屬性的影響,而絕對控股企業的決策權高度集中,制衡股東很難發揮監督作用。具體假設如表1所示:
H1:在股權相對分散的情況下,股東之間的制衡約束不顯著;國有資本主導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約束效力較低,而非國有資本主導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約束力較強。

表1 股權制衡關系分組及研究假設
H2:在共同控制企業的狀態下,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的混合并不能有效發揮異質股東的監督作用,國有資本的資本屬性決定了決策的話語權。
H3:在共同控制企業的狀態下,資本的相同屬性資本合謀掠奪中小股東,但國有資本與國有資本之間由于利益差異分化而加劇非效率投資,從而弱化股權制衡的治理效應。
H4:在單個資本絕對控股的企業,非控股股東處于絕對弱勢地位,股權制衡的治理效應較差。
三、樣本選擇與研究設計
(一)樣本及數據來源
數據選取的時間區間是2007—2015年,因為數據處理涉及滯后一期變量,實際研究區間是2008—2014年,其中公司財務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數據主要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公司實際控制人數據來自于中國經濟金融(CCER)數據庫,數據用STATA12處理。
根據數據系統采集的結果,本文共采集到15 410個原始樣本。由于金融、銀行和保險行業的特殊性,剔除了268個樣本,考慮到創業板的風險特征和企業規模,本文主要保留了主板和中小板的上市公司樣本。按常規做法,去掉了ST、*ST、PT的公司,最后去掉數據缺失和有明顯系統錯誤的樣本(通過排序觀察的方法去掉了系統數據異常及缺失的公司),最后得到樣本12 111個樣本。樣本的篩選過程及結果如表2所示。
表3報告了分組樣本的數量分布,其中股權性質是根據國泰安數據中分類而獲取的。從表3可以看到,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10%的樣本即股權分散組樣本共有1 162個,占總樣本的9.5%;異質監督組共有樣本3 214個,占總樣本的26.5%;同質合謀組共有樣本5 523個,占總樣本的45.6%;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超過50%的獨權控股公司共有2 212個,占總樣本的18.26%。以上混合樣本(Pool Data)的分布情況說明,共同控股或對公司產生重大影響的樣本共占約72%,而一股獨大的公司樣本約占18%,這一樣本分布趨勢在2014年基本保持不變。因此對這些樣本的股權制衡關系進行分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研究設計與模型構建
關于過度投資的研究起源于非效率投資。瑞查森(Richardson)[27]首次量化了非效率投資,他用企業實際新增投資水平與預測的投資水平之差作為非效率投資的量化指標,并定義了過度投資為實際投資超出預期投資水平的部分,而實際投資低于預期的投資水平為投資不足,國內研究主要借鑒了這一計量模型。根據其研究模型,企業新增的投資水平為第t年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除以年初總資產,由于新增投資水平主要受到企業銷售業績增長率、企業貨幣資金持有量、上一期投資量等因素的影響,因此用公式(1)來預測企業的預期投資水平。

表2 樣本篩選過程

表3 樣本的分布

根據公式(1),用實際投資水平減去預期新增投資水平得到非效率投資(即公式(1)的回歸殘差),定義公式(1)預測的投資水平為e_inv,則過度投資水平為Oi。Oi的具體表達公式(2)為:

關于股權制衡變量,目前學者們主要用股權集中度、相對持股比例來衡量。竇煒等[14]用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與所有權比例之差衡量了控制權分布的均衡狀態,同時用第一大股東與第二大股東之差進行對比分析;梅丹[12]、簡建輝等[13]、陳志軍等[15]用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或第一大股東持股數/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數等度量指標來研究股權制衡方法,本文參考了這些研究方法。本文認為,第二大股東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相近,第二大股東投票表決權越大,股權制衡能力越強,因此第二大股東的股權制衡變量CB為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為了研究CB對企業過度投資行為的影響,構建模型(3)。過度投資行為通常還會受到企業增長率、現金流量、投資回報率、規模和資本結構的影響,本文一并控制了這些變量。

本文各個模型涉及的所有變量及定義如表4所示。
四、實證研究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5報告了回歸模型中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總體上來看,我國上市公司2008—2014年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均值為33.105,大于中位數31.93,結合最大值和標準差(sd)說明樣本受個別樣本的影響整體呈右偏分布;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Top2均值為8.705,第二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制衡系數CB均值為0.39,這說明總體上第二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弱勢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制衡能力不足。企業每年因投資而支付的現金流量占總資產的7.08%,明顯高于企業銷售增長率(Growth)的2.7%,這說明企業存在一定的過度投資行為,投資量與市場需求、銷售業績并不協調。根據模型(2)的計算結果發現,共有4 666家上市公司存在過度投資行為,占總樣本的38.52%,且超過最優投資量的3.93%,這對于公司規模上萬億元的公司而言是不可估量的效率損失,如中國石油(股票代碼:601857)2014年的總資產約為24 053億元,僅僅3.93%的過度投資就意味著約945億元的超額投資水平。2008—2014年樣本的貨幣資金及現金等價物占企業資產總額的22.98%,樣本資產規模對數size均值為21.925,整體負債率Lev維持在46.5%的水平,投資效率Roa為4.8%,國企主導的企業約占總體樣本的50.17%,這些數據為觀測樣本總體概貌提供了參考。

表4 變量定義

表5 總體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國有資本主導與非國有資本主導的企業各占半壁江山,對比研究兩種資本主導下的股權制衡機制及經濟后果有利于我們發現國企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問題、探索改革路徑,因此本文分組報告了樣本股權與投資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6所示。
從表6可知,股權分散組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均值僅為4.53%,而非國有產權主導和國有產權主導的第二大股東制衡變量CB分別為0.906、0.987,這說明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第二大股東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懸殊差距較小,股權制衡力量相對比較大,處于勢均力敵的狀態;股權分散組的過度投資水平最低,非國有產權組Oi為0.034,國有產權組Oi為0.029,這說明在股權分散的狀態下,單個股東很難獨當一面,決策行為往往受到其他股東的牽制。在股權異質監督組,股權制衡變量CB為0.345,國有資本控股的第二大股東持股為8.166%,可以看出相對第一大股東持股而言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考慮到國有資本先天的優越性,作為非國有性質的第二大股東很難發揮制衡作用。而在股權同質的合謀組,由于股權性質相同,股權制衡變量CB提高到0.418,我們認為同為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在第二大股東與第一大股東性質相同時,股權制衡力量會加強,表現出“同而不合”。而由第一大股東獨權控制的企業,第二大股東的制衡能力最差,在國有資本組CB為0.075,在非國有資本組CB為0.115,過度投資行為數量相當,一股獨大的特點非常明顯。
表7報告了研究變量的相關系數。從表7可以看到,股東持股比例與投資水平絕對量Inv正相關,這說明股權持股水平代表的投資決策權與投資規模正相關,但股權制衡變量與投資水平負相關,這說明股東之間的制衡關系對投資水平會有一定約束作用。從表7中可見,其他自變量之間并不存在嚴重的線性關系。CB與top1、top2之間的相關系數大于0.5,為了避免它們之間的共線性,后文模型回歸后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以規避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表6 股權與投資變量的對比描述
(二)回歸分析
表8是基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分組的股權結構治理效應。從總體樣本回歸的結果來看,第二大股東與第一大股東之間的制衡變量CB與過度投資行為之間負相關,體現了顯著的制衡作用,但是混合數據調整過后的擬合優度為0.017,整個模型的擬合程度較低。通過分組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普遍提高,這說明分組回歸是恰當的,提高了模型的增量解釋能力。從回歸(2)可以看出,在股權分散的狀態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有抑制過度投資行為的傾向,股權之間的制衡效應在1%的水平區間顯著,治理效應較大,回歸系數為-0.207。這說明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個別大股東很難左右投資水平,股東之間持股比例差距小,股權制衡作用顯著。在回歸(3)中,存在控股股東是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的組合,但是股權變量和制衡變量的t值都非常小,這說明股權結構幾乎對過度投資行為沒有影響,而不是因為股權性質不同產生了先天的制約機制;而過度投資行為主要受到銷售增長率(Growth)和現金等價物持有水平的顯著影響。在回歸(4)中我們認為控股股東和制衡股東屬性一致,從而股東合謀的概率更大,但實證研究表明制衡股東發揮了顯著的監督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股東之間決策行為異化導致的,國有股東和國有股東之間未必會合謀,相反它們可能會為了爭奪共同的資源而形成互不妥協的制約力量,從而產生制衡作用。在回歸(5)中,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都在50%以上,而制衡股東的制衡能力受到持股比例約束因而制衡能力非常差,從回歸結果也能看到過度投資行為并不受股權結構的影響。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控股股東獨當一面,具有絕對的決策話語權,一股獨大的特點非常明顯,與理論預期一致。

表7 變量的相關系數

表8 基于持股比例分組回歸的股權結構治理效應
在控制變量中,企業的管理層規模越大,那么過度投資行為會更嚴重,企業過度投資行為普遍與企業銷售增長率顯著正相關,這說明高速增長的同時必然伴隨一定程度的過度投資。根據投資理論,很難準確給出與未來預期一致的最優投資水平,通常是通過對未來增長進行估計、項目評估等方法進行投資,因此基于增長率的投資決策有必要評價投資的非效率,將其控制在適度范圍。在各個回歸中,投資都受到現金等價物持有量的約束,無疑投資行為必然伴隨著現金流出,因此企業要根據投資階段保留適當的現金,以捕獲投資機會,提高資本投資回報率;投資回報與投資之間會形成良性循環,較高的投資報酬率會刺激新一輪的投資,而企業的存量規模和財務杠桿會制約過度投資行為,這說明規模和債務約束發揮了治理作用。
為了在上述分析基礎上挖掘出股權制衡的內在機理,表9基于混合所有制企業異質產權的視角報告了公式(3)的回歸結果,同時驗證了本文的假設。從中可以看出,在股權分散組中,國有產權主導的公司制衡變量并未發揮作用,而非國有產權資本主導的公司制衡變量顯著制約了過度投資行為,如回歸(1)的結果CB的回歸系數為-0.23,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非國有資本主導的公司治理效率高于國有資本主導的公司治理效率,盡管是國企參股,但是國企的資本優越性仍然沒有完全褪去。在異質監督組,針對第一大股東和第二大股東資本搭配模式可以概括為(國有資本,非國有資本)、(非國有資本,國有資本),我們僅僅從資本屬性出發認為資本之間會形成一種監督力量,但實際情況并不盡然。在回歸(2)中,國有資本起主導作用,非國有資本的相對制衡力量處于弱勢,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地位的懸殊并不是持股比例決定的,而是股權特質決定的,因此制衡的監督機制無法運行;在非國有資本主導的回歸(2)中,國有資本處于第二大控股地位,資本組合模式為(非國有資本,國有資本),但是從回歸結果來看,國有資本并沒有發揮監督的制衡作用。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混合,很多時候是看中非國有資本的投資效率,因此在這種混合資本共同控制的局面下,要么非國有資本監督不足,要么國有資本不作為,分組情況與總體樣本結論一致。這也可能是監督組不監督的原因。在同質合謀組就第一大股東與第二大股東資本屬性而言資本組合模式為(國有資本,國有資本)、(非國有資本,非國有資本),由于資本屬性的一致性,假設資本投資者之間更容易為了共同的利益目標而合謀決策,掠奪中小股東,但實際情況是否完全一致呢?從回歸(3)的結果可以看出,制衡變量CB的回歸系數為-0.042,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國有資本,國有資本)組合模式下,第二大股東為國有資本,與第一大股東不存在資本屬性地位方面的差異,只有持股比例形成適當的制衡力量,控股股東之間因為爭奪共同的資源而決策行為異化,第二大股東將發揮顯著的制衡力量;但是(非國有資本,非國有資本)的組合模式下這種效果并不顯著。在獨權控制組,股東決策行為主要以第一大股東決策為主,持股比例的絕對數量優勢使得其他股東很難發揮制衡作用。

表9 股權結構治理效應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測試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將以上不同組別之間進行了ANOVA檢驗,結果發現不同組別之間過度投資行為受到資本屬性(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顯著影響,這說明分組研究不同資本組合模式對探索公司制衡治理機制的做法是可取的。另外我們還用第二到第五大股東的股權集中度、Z指數作為制衡變量的替代變量,研究結論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報告結果。
五、研究結論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的混合主要通過投資行為來實現,這一過程必然提高過度投資風險,而良好的股權制衡結構使得制衡股東發揮監督功能從而降低這一風險。基于此,本文試圖探索第二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過度投資行為的治理效應是否受到股權性質差異的影響并提出假設,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結論:
第一,當第一大股東與制衡股東的資本屬性是(國有資本,國有資本)的組合模式時,股權制衡變量對過度投資行為有顯著的制衡作用,表現為“同而不合”;而非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組合股東合謀的概率更大。第二,當第一大股東與制衡股東的資本屬性是(國有資本,非國有資本)或(非國有資本,國有資本)的組合模式時,第二大股東的制衡變量CB對過度投資行為幾乎沒有影響。這兩點主要結論說明,國有資本的資本優越性在不同的資本組合模式中發揮的制衡作用不同,資本屬性會影響監督制衡作用的發揮。因此,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尤其是在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混合時,應考慮如何擺脫資本優越性的束縛以發揮資本內在的監督效率。
[1]BERLE A A,MEANS G C.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New York:Macmillan,1932:57.
[2]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471-517.
[3]FACCIO M,LANG L.The ultimate ownership of western european compani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2,65:365-395.
[4]BENNEDSEN M,WOLFENZON D.The balance of power in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8:113-139.
[5]GOMES A,NOVAES W.Sharing of control as a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R].Philadelphia:PIER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2001.
[6]BENJAMIN Maury,ANETEPajuste.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firm value[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5,29:1813-1834.
[7]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 etc.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J].Journal of finance,2002,57:1147-1170.
[8]BLOCH F,HEGE U.Multiple shareholders and control contests[J/OL].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3(2013-06-03)[201 7-02-10].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6158bee1f5fb0758601af1a3597d5540%29&filter=sc_long_ 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 2F%2Fpapers.ssrn.com%2Fabstract%3D2273211&ie=utf-8&sc_us=4326371584284384908.
[9]劉芍佳,孫霈,劉乃全.終極產權論、股權結構及公司績效[J].經濟研究,2003(4):51-62+93.
[10]吳紅軍,吳世農.股權制衡、大股東掏空與企業價值[J].經濟管理,2009(3):44-52.
[11]夏立軍,方軼強.政府控制、治理環境與公司價值——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05(5):40-51.
[12]梅丹.國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機制與過度投資[J].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學報,2008(4):47-56.
[13]簡建輝,黃平.股權性質、過度投資與股權集中度:證券市場A股證據[J].改革,2010(11):111-119.
[14]竇煒,馬莉莉,劉星.控制權配置、權利制衡與公司非效率投資行為[J].管理評論,2016(12):101-115.
[15]陳志軍,趙月皎,劉洋.不同制衡股東類型下股權制衡與研發投入——基于雙重代理成本視角的分析[J].經濟管理,2016(3):57-66.
[16]JENSEN,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05-360.
[17]SHLEIFER A,VISH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7,52:737-783.
[18]GROSSMAN S J,HART O D.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8,94:56-92.
[19]朱雅琴.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與公司績效——來自滬深兩市的經驗證據[J].財會通訊,2010(15):56-58.
[20]徐向藝,李鑫.自由現金流、負債融資與企業過度投資——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軟科學,2008(7):124-127+139.
[21]陳德萍,陳永圣.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與公司績效關系研究——2007—2009年中小企業板塊的實證檢驗[J].會計研究,2011(1):38-43.
[22]郝穎,李曉歐,劉星.終極控制、資本投向與配置績效[J].管理科學學報,2012(3):83-96.
[23]安靈,劉星,白藝昕.股權制衡、終極所有權性質與上市企業非效率投資[J].管理工程學報,2008(3):100-105.
[24]李香梅,袁玉娟,戴志敏.控制權私有收益、公司治理與非效率投資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5(3):139-143.
[25]謝軍.中國混合所有制企業國有產權管理研究[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2013.
[26]張敏.論混合所有制企業公司治理的特殊性[J].青海社會科學,2015(6):58-65.
[27]RICHARDSON S.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2):159-189.
責任編輯:林英澤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n the Over-investment Behavior——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Brought by Heterogeneous Equity in the Mixed Ownership Enterprises
YIN Yu-pin
(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101149,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the mix of state-owned and private capital will be realized through investment;and this process will definitely increase the risk of over-investment.Sou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may play the adjustment role to over-investment,which will limit the behavior of over-investment.According to the hypothesis of stockholder relation,if stockholders with balance of power play their role in supervising controlling stockholders,this risk will be reduced;and if they plot together to exploit small and medium stockholders,this risk will be increased.Because of the precondition of state-owned and private capital,stockholder relation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 nature of capital.It is found that,when the equity percentage held by controlling stockholders is from 10%to 50%,if the nature of controlling stockholders and stockholders with balance of power is heterogeneous,the second large stockholders’variable concerning balance of power can not play its role in supervising over-investment;and if the nature of them is the same,the heterogeneous interests behavior among stockholders will lead to the effect of balance of power when they are all state-owned capital,which will demonstrated as“the same,but no conspiracy”,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balance of power on over-investment when they are all private capital,which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conspiracy.
heterogeneous equity;equity balance of power;over-investment;mixed ownership
F279.24
A
1007-8266(2017)06-0113-10
10.14089/j.cnki.cn11-3664/f.2017.06.014
殷裕品.股權結構對過度投資行為的治理效應[J].中國流通經濟,2017(6):113-122.
2017-05-22
殷裕品(1964—),男,湖北省京山縣人,北京物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管理會計與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