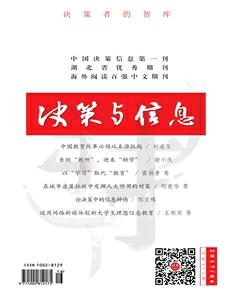統一“內在積極”與“外在積極”:中國慈善發展戰略
王鍇
[摘 要] 中國慈善事業近代轉型的最大特點是提倡“積極慈善”,用以替代傳統的“消極慈善”。但彼時的積極慈善還只是一種簡單的“外在積極”,內在本質依舊是對傳統消極慈善的保留。當下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需要繼續這一積極化的過程,即是統一“內在積極”與“外在積極”。“內在積極”要求個體主體性的自我弘揚,其核心范疇為自由主體、平等主體、責任主體和目的主體。“外在積極”要求從贈與者與接受者的直接互動向以慈善組織為中介客體的間接互動轉變,從物資型慈善向服務型慈善轉變,從參與對象的有限性向“全民慈善——慈善全民”轉變,從使人生存向促人發展轉變,從事后干預向預防與干預相結合轉變。
[關鍵詞] 中國慈善;慈善事業;慈善制度;慈善組織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17)06-0043-08
中國慈善思想源遠流長,向前可追溯至先秦。管子曾說:“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賑,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近代以降,伴隨著開眼看世界的浪潮,部分有識之士如魏源、馮桂芬在關注西方慈善救濟的同時開始了自我反思,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了向西方慈善學習的主張,“其主要表現之一,便是帶有近代意義的‘教養并重或‘教養兼施思潮的興起” [1]。 中國傳統慈善“重養而輕教”,比之西方較為消極。而當時學習西方的先進國人所提倡的是一種樸素的積極慈善理念:在授人以“魚”的基礎上,更要授人以“漁”,強調知識和技能的傳授。當下而言,學界內鮮有對積極慈善的專門性研究,多以歷史學為陣地,將其作為研究中國近代慈善的一個視角,而對積極慈善的概念理解也多停留在近代所理解的“外在積極”層面(將其作為提高慈善行為效率的一種手段),而缺少對這一概念的內涵挖掘和當代解釋。因此,研究“內在積極”與“外在積極”之慈善,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本質內涵:積極慈善的內在“積極化”路徑
對積極慈善這一概念的理解,首先需要把握它的本質內涵,可稱其為“內在積極”。在中國慈善的近代轉型中,所提出的積極主張只是一種對慈善外在行為方式的改良,針對的是如何提高慈善行為和善款的利用效率,強調的是“外在積極”,而其本質卻依舊是傳統消極型慈善。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指出,“中國傳統的慈善事業,偏重于消極施舍,救助層次較低。相較而言,西方的救助手段更為積極。如前所述,在救助貧民和殘疾人時,西方各國不單給予其生活救助以維持其生存,還會對具有勞動能力者進行職業培訓,以便自食其力” [2]157。馮桂芬在《收貧民議》中亦寫道:“荷蘭國有養貧、教貧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紳輒收之,老幼殘疾入養局,廩之而已;少壯入教局,有嚴師,又絕有力,量其所能為而日與之程,不中程者痛責之,中程而后已。國人子弟有不率者,輒曰逐汝,汝且入教貧局,子弟輒為之改行,以是國無游民,無饑民”,“瑞顛(典)國設小書院無數,不入院者官必強之,有不入書院之刑,有父兄縱子弟不入書院之刑,以是國無不識字之民”[2]158 。由此,馮桂芬根據西方的相關做法提出了“嚴教室”和“化良局”等構想,對游手好閑的貧民實施收容教育和傳授技能。可以看出,近代國人對慈善的見解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提出的對西方慈善行為的經驗性學習,沒有涉及慈善的本質。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這樣的慈善思想在本質上與傳統慈善并無二致,即是一種以國家、社會和給予者自身為目的,以“主-客”二元關系為交往形態的傳統慈善。其中,接受者被當作了手段,成了給予者眼中的客體和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也就毫無尊嚴可言。“中國之為慈善者,皆先以禍福之酬報為心,而慈善之事業,實為此禍福之芻狗者也,為善之本源若此,則救人者其視此待救之人,無異供其求福之一物”[3] 。接受者需要對給予者“感恩戴德”,而給予者也會“高人一等”,因此這樣的慈善即使在行為策略上進行了改進,也不能真正幫助接受者擺脫困境,不能改變其社會底層地位。
提出慈善發展的未來走向,即內在“積極化”的過程,首先要明確積極慈善的本質內涵,即何為“內在積極”。結合時代精神而言,我們認為,當下的時代精神是一種對后現代的反思精神,是經歷了從啟蒙現代性、經典現代性直至后現代發展而來的,強調作為社會中之個體主體性的“人的精神”。這樣的精神要求擺脫過度強調整體的思想束縛,而要關注個體人的生存發展,將人作為目的,將個體主體性的弘揚作為終極追求。因此,中國的慈善事業需要以符合時代精神的慈善理念作為指引,這就是積極慈善的“內在積極”所要表達的內容。具體來說,這一主體性要求的核心范疇包括自由主體、平等主體、責任主體以及目的主體。
自由主體意味著接受者的自我選擇權,強調接受者作為理性的個體應擺脫外界因“慈善”而強加其身的各種枷鎖,如傳統慈善中所提出的“強制收容”“強行勞動”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對個體自由的束縛。個體只有首先得到了自由,才能有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的權力,才能有自我發展的權力,也才有實現自我主體性的可能。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平等主體要求摒棄傳統慈善行為中的“主-客”二元交往結構,意指在慈善行為中,給予者和接受者是處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的狀況,不存在一方需要對另一方“感恩戴德”。雙方是平等交往的主體,互相承認對方的主體身份。而對單一主體身份的消解也正是后現代的追求。但后現代所提出的“主-主”交往結構,因對個體自身的過度強調而難免會陷入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境地,因此要克服這一問題,就需要結合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對后現代的反思,提倡構建加入中介客體的“主-客-主”交往結構。無論如何,積極慈善的“內在積極”要求對接受者平等主體身份的恢復和確認。責任與自由是一體兩面,個體擁有自我選擇權,需要對自我選擇負責。對積極慈善來說,接受者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如果選擇參與到慈善互動中,那么就需要承擔相關的責任,如積極配合教育培訓,努力擺脫困境,這可以看作是接受者擺脫困境所需要的內在動力。傳統慈善和近代慈善之所以“內在消極”,最根本的一點是將個體作為鞏固政權統治、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實現給予者個人利益的手段,將個體當成了工具。“往日慈善事業的動機,在‘作好事‘得善報‘入天堂,‘修橋補路為的是兒女的將來” [4] 。而要將消極轉為積極,就需要明確慈善的目的,即對人的尊重。人即是目的,沒有一個超脫于這一目的之上的終極目的。也只有在明確了人是目的之后,個體才能獲得尊嚴。一言以蔽之,對積極慈善的當代理解首先需要明確這一概念的本質要求,即“內在積極”——幫助個體重獲主體性。
二、概念外延:積極慈善的外在“積極化”路徑
由上可知,近代提出的對傳統消極慈善外在行為方式的改良,大概可視為中國積極慈善的濫觴。然近代對積極慈善的理解還僅僅停留在“外在積極”部分,如近代學人曾憲琳指出:“但慈善事業,為一種消極之救濟事業,能救貧而不能除貧……故根本防止貧窮,救濟難民,宜發展交通,開辟富源,厲行公共衛生事業,驅除一切疾病之根源,獎勵科學研究,以控制自然,增加生產者之收入,取締掌有生產機關者之活動與收入,防止產業之不穩,保護女子與兒童之權利。”[5]在對“外在積極”的理解上,大致也呈現出不斷豐富的過程:由晚清時期魏源提出的“院內救濟”“強制勞動”到民國初期關注個體的教育培訓,再到民國南京政府時期擴展到對整個社會制度環境的關注。但由于受到“內在消極”的束縛,這時對積極慈善概念外延的理解始終沒能有質的變化,僅僅都是圍繞慈善效率方面提出的技術性改良。當代而言,社會的慈善發展需要結合時代精神的要求提出更加完整和豐富的概念。具體來說,中國當下積極慈善中的“外在積極”要求做到以下五個轉變:
(一)從贈與者與接受者的直接互動向以慈善組織為中介客體的間接互動轉變
傳統慈善在交往關系上最大的特點是“主-客”二元關系的交往,給予者處于主體地位,接受者處于客體地位,從屬于主體。這一交往關系直接反映出給予者和接受者雙方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接受者尊嚴的喪失。同時,對處于客體地位的接受者來說,無論怎樣接受主體給予他的“積極外衣”,也無法擺脫從屬地位,獲得自我的主體性。
當代對于積極慈善的內涵理解中的重要一條是雙方地位的平等,亦即“去單一主體化”,實現多主體間的交往關系。但這樣一種交往關系何以可能?正如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探討“他人的目光”的問題一般樣,有的學者將其稱為“美杜莎之謎” [6] 。美杜莎是古希臘神話中的惡神,被其目光所及人即成為石像。在薩特看來,作為主體,其眼中的他者都將成為客體,因此薩特感嘆“可怕的他人的目光”。如現實中某些富人的慈善行為,雖然拿出了真金白銀予以慈善捐贈,且常常是直接發放現金,但往往不顧接受者意愿要求和接受者合影。這樣的行為從接受者角度來看,無論富人如何宣稱對對方的尊重,也無法改變主客二元對立的局面。這涉及交往哲學的重要命題,即多元主體如何能夠共存。我們認為,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需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交往實踐觀,“主體之所以能夠面對另一極主體,主體性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存在著中介客體。這一客體,是中介化的客體和客體化的中介。它向多極主體開放,與多極主體同時構成‘主-客關系,因此,它通過自身而建立起‘主體-客體-主體三級關系結構” [6] 。以中介客體作為交往底板,能夠有效地將多元主體連接起來,各極主體在面對這一客體時能夠彰顯自己的主體性。具體到慈善行為中,接受者和給予者如果想要真正實現多元主體的交往活動,就必須要依靠中介客體,而這一中介客體就是慈善組織。給予者將資源提供給慈善組織,這一活動中給予者面對慈善組織而彰顯了自己的主體性;另一方面,接受者享受慈善組織提供給自己的慈善物品,接受者也在這一過程中體現了自己的主體地位。慈善組織作為這樣的一種中介客體,可以說是給予者和接受者之間的橋梁,將雙方連接在一起的同時也將雙方進行了阻隔,避免了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的狀況。作為給予者,不會有“高高在上”之感,作為接受者,也不會自認“低人一等”,更無需對給予者“感恩戴德”。當然這并不說明接受者不會有感恩之心,只不過其感恩的對象不會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這樣的一種慈善制度。
以慈善組織作為中介交往的形式,可以說是積極慈善在“外在積極”部分中最主要的表現。這樣一種“主-客-主”的交往形式來自積極慈善概念內涵的要求,同時也是其內涵價值實現的可能。
(二)從物資型慈善向服務型慈善轉變
中國傳統慈善在內容上多以直接的金錢和實物給予為主,或者是設立相關機構對災民貧民實施隔離供養,如棲流所、施粥廠等。“即如消極的救災恤貧辦法,在我中國施行已久,非但慈善機關林立,即依布施以為生活之人,亦不在少數。……然則此類救濟,究非根本方法”[7] 。直接物資給予雖然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迅速幫助受助者解決眼下的困難,但并非長久之計,因為這無法幫助受助者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只能“安貧”而不能“脫貧”。而且,這樣的一種直接物資幫助所針對的對象是極有限的,即只是針對物資貧困的人群,而對能力貧困、精神貧困等人群卻并不適用。即使是針對的物資貧困人群也可能會出現雖然獲得了資金的救濟,卻無法購買到所需產品的狀況,這最典型的是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的慈善扶貧。何況,這樣的直接方式使得善款的利用效率很低,是一種“無底的竹籃打水”,比如當有大量資金投入的時候,接受者的境況會得到提升,而一旦資金減少或停止,則接受者又會回到原初狀態之中。因此這樣的一種救助內容是非常消極和被動的,作為接受者來說倘若缺少主動性,那么就很難獲得真正的幫助。
積極慈善所注重的慈善內容應當擺脫單純的物質包括金錢給予,轉而構建以服務為核心的慈善內容。這里的服務主要是個人社會服務(personal social services),即指以個人的需求為導向,差別化地提供相應服務性資源的行為。這在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領域已經有了體現,這些國家改變以往重金錢而輕服務的狀況,“紛紛走上了‘社會服務導向型的新型社會給付之路,實現了福利國家社會給付模式的革新” [8] 。諸如“瑞典、挪威、英國、荷蘭、丹麥已邁入‘準社會服務國家的行列” [9] 。以服務作為慈善有諸多優點:首先,可以解決接受者對資源“可及性”的需求。可以針對不同人的不同境況提供不同的服務,如老年照料、醫療護理、兒童教育、精神康復等。當然,我們雖然強調服務,但并非否定物質資金的救濟。其次,服務型的慈善內容可以以人力資本投資作為著力點,關注個體的能力建設,幫助個體增強能力。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也是切斷代際貧困傳遞的根本途徑。只有個體的自我能力得到提升之后,才能使他們通過自身的能力量擺脫困境,實現“自助”,這才能真正幫助到受助者。再次,服務型慈善的內容從短期來看成本更高,操作也更為復雜,但從長遠來看,卻能擺脫傳統消極慈善中“無底的竹籃打水”這一狀況,避免無限制的資金投入。從社會角度來看,受助者在獲得能力提升后也能加入到社會生產之中,增加社會總財富。最后,服務型慈善可以促進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如使受助者擺脫懶惰心理而實現自立,并能在服務過程中起到“勸善”的作用,洗滌受助者的心靈。可以說,將服務作為慈善內容的主體,使得“外在積極”具有當代價值,并與近代“外在積極”所強調的“規訓”相區別,從而促使自身變得更加尊重其主體性。
(三)從參與對象的有限性向“全民慈善——慈善全民”轉變
2016下半年的“羅爾事件”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疑問,即中產階級在倫理上能否成為接受慈善的對象?在傳統慈善文化中,通常對于慈善的接受者來說具有一定的道德要求,受助者除了要心懷感恩之外,也需要保持社會公認的倫理規范。因此對于那些品行不端者而言,他們通常很難獲得救濟。同時由于慈善的發端是人之善心,是看到他人所受痛苦之后的感同身受,因此對于受助者來說,一定要足夠“可憐”才能激發他人的慈善行為,否則給予者便會產生一種心理上的“欺騙”,即“你有錢還要我們捐款”。而且,傳統慈善的給予者是少部分社會上層人士,是受到過“仁者愛人”思想訓導的“君子”,或自身富足之人(如社會名流、官宦士紳等),他們主動把自己和底層貧民隔離開來,認為自己在社會地位、道德地位和經濟地位上都高于他們,而慈善行為也不可避免地折射出這些思想。而作為社會中大多數的中間人群,卻會對慈善保持相對的“冷漠”,既不愿成為慈善的接受對象,也不愿參與慈善給予,而認為慈善是“肉食者”的事。這就造成了傳統慈善參與者的有限性,即使近代提出的“外在積極”改良也只是針對社會上層人士的要求。
就當代社會而言,人們處于一種有機團結之中,沒有誰能“與世隔絕”,人與人的依賴性空前加強。慈善也不僅僅是道德高尚者的行為象征,而是源自內心的善意而對他人的關愛,以及對整個社會共同體的關愛。積極慈善內涵中的平等要求,使得交往雙方不存在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的情況,也就不存在給予者“高尚”、接受者“低賤”的陳腐看法。而且,可將慈善內容大大擴展到慈善對象。不但促使人人都可以參與慈善,如從事義工、志愿服務等,也可使應該享受慈善的人享受到慈善且可使得慈善受助對象得以擺脫“污名”的尷尬身份,使得整個慈善的外延逐步向“公益”推進。從積極慈善的參與對象來看,“外在積極”要求慈善參與對象向全民擴展,形成“全民慈善——慈善全民”的理想狀態。
(四)從使人生存向促人發展轉變
近代慈善“外在積極”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只關心人的生存,如以工代賑獲得一定的口糧和薪資,舉辦“工藝局”“習藝所”傳授一些諸如編織、木工等最簡單的謀生技能等(這樣的教育對象主要以兒童為主)。雖然對于接受者來說,自己的能力有一定提升,但也只能勉強維持最低生活,抗風險能力依然很低,始終無法從社會底層跳脫,在自我的精神、道德上也沒有提升。這就造成了慈善對象只能是最低生活之下的貧困人群狀況。
當下對積極慈善的理解,不能再是追求個體生存的最底線,不能僅僅滿足于 “基礎教育”,因為這樣的目標標準太低,而且也不利于慈善的全民化推廣。真正的做法是,應當將目標提升至促進個體的積極發展。同時,在服務項目上要擺脫簡單的技能培訓,要強調全面的素質教育。要積極倡導終身學習,不僅要學習如何獲得基本技能,而且還要進行相關文化素質、道德情操的培育,要讓受助者獲得自我反思的能力,達到提升自己。在教育層次上,不但要使受助者獲得基礎教育,還應當讓他們有機會獲得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在相關技能學習方面,不僅要注重精細化和技術化,使受助者謀生的同時,還能生成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以促人發展為目標的慈善行為不僅僅要求個體的轉變,還要求社會的改變,如要求社會提供全民化的公共服務、完善制度建設、健全基礎設施、改善自然環境等。相比近代的“外在積極”和傳統消極型慈善,這種現代意義的積極慈善目標更高、要求更高,且更為積極,無疑使得當今的慈善事業更加大有作為。
(五)從事后干預向預防與干預相結合轉變
“防患于未然”的“治未病”的慈善思想在近代已有發端。“積極之慈善,防患于未來,曲突徙薪者也,消極之慈善,救濟于已然,焦頭爛額者也。能防患于未然,即不致救濟于事后,善醫者治病于無形,大慈善家亦能弭患于未現”[11] 。在具體措施上,這種慈善思想主張救濟貧民生活問題、籌辦成人教育、籌辦社會教育等。其具體包括設立平民讀書處、設巡回書庫、籌辦規模較大的普通圖書館、多開辟公園及運動場等。由此可見,這樣的慈善理念已經具備了現代積極慈善的部分特點,但由于其依然身處傳統社會,所面對的問題與當今現代化、后現代化社會出現的問題不盡相同,因此當下對這一理念的理解理應更加豐滿。
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積極福利就是要擺脫“把預后關懷作為解決風險的主要手段以及對它的依賴” [12] 。現代社會的風險與傳統社會大不相同。傳統社會更多地是自然風險或外部風險,相對較為穩定和可控,對此人們通過歷代的知識傳遞對風險也有比較充足的認識,但現代社會的風險大量多數情況下是人為風險,且不確定性強、難以控制。因此傳統的事后干預已無法奏效,不得不將干預手段提前,達到克服風險同時實現節約成本。吉登斯進一步指出,“擺脫對預后關懷的強調意味著用直接的、參與的方式來解決風險”[12] 。這意味著要以更為積極的心態去面對風險,并在應對風險中實現自我發展。在對積極慈善的要求上,不僅僅要通過教育解決問題,更要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各個部分,如宣傳安全的交通行為、健康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保護意識等方法解決問題,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仍以羅爾事件為例,即使羅爾是中產階級,有一定財產,也完全沒有必要等到他將所有財產都花完成為赤貧之時才予以救濟,那樣只會大大降低受助者的自我恢復能力。而且在風險確實已然發生之時,有必要以事后關懷的方式解決問題。
三、結語
當下中國的慈善事業發展需要擺脫消極慈善模式,在近代開始的“積極化”路徑上繼續邁進,這需要結合當下的時代精神對慈善提出新的發展要求。本文認為,這一發展要求就是從消極慈善走向積極慈善,而積極慈善又是“內在積極”和“外在積極”的統一。在明確積極慈善概念內涵的基礎上豐富其概念外延,使慈善“由內而外”地符合當代價值。在此意義上,本文所做的分析有利于拓寬當前對慈善事業的認識,并對中國慈善事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有益借鑒。
[參考文獻]
[1] 王衛平. 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近代轉型及其啟示[J]. 史學月刊,2013,(3).
[2] 周秋光.中國近代慈善事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3] 社說.論慈善事業中外之不同[J]. 東方雜志,1904,(11).
[4] 言心哲.社會事業與慈善事業的區別[J].振濟月刊,1937,(2).
[5] 曾憲琳.中國慈善事業應改良之點.節制月刊[J].1931,(7).
[6] 任平.交往實踐與主體際[M].江蘇: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
[7] 舒.節食救貧——由德國節食運動說到中國慈善事業[N].申報.1934-03-07.
[8] 梁譽. 現金還是服務:歐洲福利國家社會給付模式的革新與啟示[J]. 學習與實踐,2014,(7).
[9] 林閩鋼,梁譽. 社會服務國家: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J]. 公共行政評論,2016,(5).
[10] 曾桂林. 近代中國慈善教育事業的歷史考察[J].井岡山大學學報,2015,(1).
[11] 羅濟時.敬告本港慈善團體及慈善家[J].鐘聲月刊,1924,(6).
[12] 安東尼·吉登斯.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M].李惠斌.楊雪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