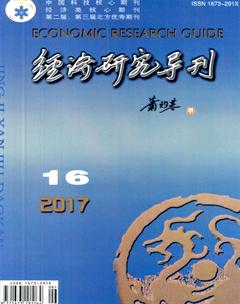班級社會網(wǎng)絡(luò)對學(xué)業(yè)成績的影響
蔣麗 胡寧馨 胡亞楠
摘 要:個體都嵌入在人際交往的社會網(wǎng)絡(luò)中,班級中的人際網(wǎng)絡(luò)是大學(xué)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探索大學(xué)生的線上與線下人際關(guān)系是否一致,線上和線下的社會交互是否會影響其學(xué)業(yè)成績,采用整體社會網(wǎng)的方法,獲得兩個班級158位學(xué)生的整體社會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通過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和回歸分析,探索其在線上和線下班級網(wǎng)絡(luò)中的網(wǎng)絡(luò)特征與學(xué)業(yè)成績的關(guān)系。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大學(xué)生的線上與線下人際關(guān)系基本保持一致;在控制了性別、網(wǎng)絡(luò)使用經(jīng)驗等變量的影響后,學(xué)習(xí)者個人在班級整體網(wǎng)絡(luò)中的地位對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影響。其中,線下課業(yè)網(wǎng)絡(luò)的外向中心性與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正相關(guān);線下課業(yè)和信息網(wǎng)絡(luò)的中介性與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正相關(guān),但線上課業(yè)網(wǎng)絡(luò)的中介性與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負(fù)相關(guān)。結(jié)果表明,學(xué)生在線下和線上網(wǎng)絡(luò)中的網(wǎng)絡(luò)特征與其學(xué)習(xí)成績有關(guān)。在此基礎(chǔ)上,討論研究結(jié)論對教學(xué)和學(xué)生管理的啟示。
關(guān)鍵詞:大學(xué)生;人際關(guān)系;社會網(wǎng)絡(luò);學(xué)業(yè)成績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16-0150-05
引言
個體都嵌入在社會網(wǎng)絡(luò)和人際互動中[1~2]。與個體主義和原子化的解釋相比,社會網(wǎng)絡(luò)研究是一種更為關(guān)系化和情境化的視角[3],而中國社會又特別強調(diào)個體間的社會關(guān)系[4~5]。因此,可以通過考察社會場景中的人際互動更好地理解個體的態(tài)度和行為[6]。
班級網(wǎng)絡(luò)是大學(xué)生活的重要社會場景。在班級中的人際互動可能對大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生活產(chǎn)生很大影響。同時,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線上網(wǎng)絡(luò)也成為流行的人際溝通渠道。根據(jù)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CNNIC)發(fā)布的第36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報告》,截至2015年6月,我國網(wǎng)民規(guī)模達(dá)6.68億,半年新增網(wǎng)民1 894萬人,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為48.8%。其中大學(xué)生用戶數(shù)量占很大比重,是網(wǎng)絡(luò)用戶的主要力量[7]。線上網(wǎng)絡(luò)能夠彌補現(xiàn)實人際交往中的時空和地理局限。大學(xué)生的網(wǎng)絡(luò)交往會是現(xiàn)實人際交往的復(fù)制,還是一種延伸和補充?即網(wǎng)絡(luò)(線上)與現(xiàn)實(線下)人際關(guān)系是否一致?這些人際互動對其學(xué)業(yè)成績會產(chǎn)生何種影響?研究這些問題,對于了解和引導(dǎo)大學(xué)生的人際交往,促進(jìn)學(xué)生的學(xué)業(yè)成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
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經(jīng)過人類學(xué)家、社會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及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不斷完善,已經(jīng)成為一種跨學(xué)科的方法[1]。對群體內(nèi)社會網(wǎng)絡(luò)的定量測量有助于呈現(xiàn)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及其方向性,從而描繪出整體的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這種方法起源于莫雷諾創(chuàng)立的社會測量學(xué),使用社會關(guān)系圖來代表群體內(nèi)人際關(guān)系,稱為整體網(wǎng)絡(luò)分析。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的分析單位不是行動者(如個體、群體、組織等),而是行動者的關(guān)系[8]。整體網(wǎng)絡(luò)分析集中于小群體內(nèi)部關(guān)系,探討網(wǎng)絡(luò)中成員直接或間接的聯(lián)系方式,使用的主要概念有:整體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的簇(clusters)、橋梁(bridges)、中心性(centrality)、緊密性(closeness)等[9]。
羅家德(2001)以臺灣某大學(xué)為例,研究了大學(xué)生線下人際關(guān)系與線上人際關(guān)系是否一致的問題[10]。線上交往是線下人際互動的延伸,還是完全有別于線下人際互動?有學(xué)者認(rèn)為線上交往可以彌補線下交往的缺陷,包括時空的局限和交往主體的個人缺陷,從而可以緩解其現(xiàn)實心理壓力,并減少對現(xiàn)實人際關(guān)系的依賴[11]。但現(xiàn)有研究既有線上與線下人際關(guān)系一致的結(jié)論[10,12],也有在現(xiàn)實社會的情感關(guān)系與虛擬社會的情感關(guān)系存在顯著差異的結(jié)論[13]。因此,本文將對大學(xué)生線下與線上人際網(wǎng)絡(luò)的一致性進(jìn)行探索。
為了探討大學(xué)生線上人際關(guān)系與線下人際關(guān)系是否一致、人際關(guān)系是否影響其學(xué)業(yè)成績,借鑒前人研究,本文將大學(xué)生的人際網(wǎng)絡(luò)分為課業(yè)咨詢網(wǎng)絡(luò)與信息網(wǎng)絡(luò)[10,14]。
二、網(wǎng)絡(luò)中心性與學(xué)業(yè)成績
網(wǎng)絡(luò)中心性(network centrality)是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的一個重要概念,它表明了個體對資源的控制程度[15]。中心性高的人,在網(wǎng)絡(luò)中與其關(guān)聯(lián)的行動者越多,與其他行動者的距離越短。
高中心性的個體可以獲取更多與工作或?qū)W習(xí)相關(guān)的信息[16],包括與任務(wù)相關(guān)的知識、戰(zhàn)略的、政治的、甚至是保密信息。與任務(wù)相關(guān)的建議和社會支持也會隨著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進(jìn)行傳遞[15,17]。在組織中,網(wǎng)絡(luò)中心性與組織內(nèi)的權(quán)力和影響力相關(guān)[1,16,18]。高中心性的個體有充足的多樣化資源,來幫助其完成任務(wù)。因此,擁有更豐富社會網(wǎng)絡(luò)的個人更有可能得到升遷的機會,對工作的滿意度更高,而且在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中成功率更高。Baldwin,Bedell,and Johnson (1997)研究發(fā)現(xiàn),MBA學(xué)生團(tuán)隊中個人的社會網(wǎng)絡(luò)中心性與學(xué)習(xí)分?jǐn)?shù)呈正相關(guān)[19]。在班級網(wǎng)絡(luò)中,國內(nèi)研究也發(fā)現(xiàn)大學(xué)生由學(xué)習(xí)交流所形成的社會網(wǎng)絡(luò)(程度中心性)與其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的正相關(guān)[20]。因此,我們做出如下假設(shè):
學(xué)生在班級網(wǎng)絡(luò)的中心性與其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正相關(guān)。
三、研究方法
(一)樣本
本研究以蘇州大學(xué)本科二年級的兩個班級為調(diào)查對象。兩班屬于同一學(xué)校的同一專業(yè),可以排除年齡,職業(yè)與教育程度的影響因素。同時作為大學(xué)二年級的學(xué)生,由于其共同科目較多,班級的社會網(wǎng)絡(luò)相對穩(wěn)定和成熟,學(xué)生之間的交往關(guān)系相對比較緊密。
發(fā)放班級社會網(wǎng)絡(luò)調(diào)查問卷160份,收回有效問卷158份,其中58.9%為女生。
(二)變量測量
1.網(wǎng)絡(luò)中心性。中心性有兩種常用的測量方法: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與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21]。程度中心性用來衡量誰是團(tuán)體中最主要的中心人物。對于具有方向性的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中心性又分為外向程度中心性(out-degree centrality)和內(nèi)向程度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外向程度中心性是一個成員(A)承認(rèn)對外關(guān)系數(shù)量的總和,即在這項行為上,A選擇了多少人。內(nèi)向程度中心性是其他成員承認(rèn)對成員A有關(guān)系的數(shù)量總和,即在這項行為上,有多少人選擇了A。中介中心性表示在一個社會網(wǎng)絡(luò)中,每兩兩成員互動必須透過某個行動者的程度,程度越高則說明該行動者的中介中心性越高。兩種網(wǎng)絡(luò)類型(課業(yè)咨詢、信息網(wǎng)絡(luò))×兩種互動渠道(線上、線下)×三個網(wǎng)絡(luò)中心性指標(biāo)(程度外向中心性、程度內(nèi)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即共有12個網(wǎng)絡(luò)特征的指標(biāo)。
2.學(xué)業(yè)成績。由于選修課程差異較大,因此不考慮學(xué)生的選修課程成績。選擇8門一致的必修課程的分?jǐn)?shù)平均值作為學(xué)業(yè)成績指標(biāo)。
(三)統(tǒng)計分析
運用UCINET6.0和SPSS20.0進(jìn)行統(tǒng)計分析。運用UCINET將人際互動的整體班級網(wǎng)絡(luò)進(jìn)行分析,計算出每位同學(xué)的中介中心性和程度中心性。運用SPSS軟件,對線上和線下網(wǎng)絡(luò)特征進(jìn)行相關(guān)分析;其次,將控制變量、中介中心性和程度中心性納入回歸方程,學(xué)業(yè)成績作為因變量,進(jìn)行回歸分析。
四、結(jié)果
(一)各變量的描述統(tǒng)計
表1為各種網(wǎng)絡(luò)中心性及學(xué)業(yè)成績的描述統(tǒng)計。其中,各類網(wǎng)絡(luò)的程度中心性變異較小,標(biāo)準(zhǔn)差范圍在1.35~2.26之間;而中介中心性的變異則較大,標(biāo)準(zhǔn)差在45.48~237.81之間。學(xué)業(yè)成績的平均數(shù)為79.51,標(biāo)準(zhǔn)差為6.94。
(二)線上與線下人際網(wǎng)絡(luò)
在探索大學(xué)生的線上和線下人際關(guān)系是否一致時,即考察學(xué)生在線下日常交往中選擇的人和在線上交往中選擇的人是否一致,采用外向程度中心性為測量指標(biāo)。
根據(jù)上文提到的課業(yè)咨詢和信息網(wǎng)絡(luò),設(shè)置線上和線下兩組變量。運用相關(guān)分析,得到表2線上和線下網(wǎng)絡(luò)中心性特征的相關(guān)系數(shù)。以線上和線下網(wǎng)絡(luò)中心性具體指標(biāo)間的兩兩相關(guān)系數(shù)判斷(見表2方框內(nèi)對角線上的系數(shù)),將相關(guān)系數(shù)大于0.3作為中高程度相關(guān),該對角線上的相關(guān)系數(shù)均大于0.3,其中信息網(wǎng)絡(luò)的程度中心性指標(biāo)在線上和線下完全一致(相關(guān)系數(shù)為1)。因此結(jié)果表明,大學(xué)生的線上和線下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是一致的,即一個行動者在線下有怎樣的網(wǎng)絡(luò)特征,其在線上也有相似的特征。
(三)回歸分析
逐步回歸分析的方法可以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影響,特別適合做探索研究使用。因此,本研究采用逐步回歸分析的方法,由多個網(wǎng)絡(luò)中心性變量的相關(guān)高低來決定預(yù)測變量是否進(jìn)入回歸模型,最終獲得一個以最少預(yù)測變量解釋最多因變量變異的最佳模型。回歸分析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線下課業(yè)網(wǎng)絡(luò)的外向程度中心性對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的積極影響(β=0.25,p <0.01)。線下課業(yè)和信息網(wǎng)絡(luò)的中介中心性對學(xué)業(yè)成績均有顯著的積極影響(β=0.26,p <0.01;β=0.21,p <0.01)。但線上課業(yè)網(wǎng)絡(luò)的中介中心性對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的消極影響(β=-0.18,p <0.05)(見下頁表3)。
五、討論
初步探索的結(jié)果表明,首先,大學(xué)生的線上和線下人際網(wǎng)絡(luò)基本一致,網(wǎng)絡(luò)交往是現(xiàn)實人際交往的一種延伸。與那些媒體報道中陳述的大學(xué)生沉溺網(wǎng)絡(luò)世界而脫離現(xiàn)實世界的現(xiàn)象并不一致。完全依賴網(wǎng)絡(luò),在網(wǎng)絡(luò)中尋求安慰而脫離現(xiàn)實的很可能只是少數(shù)個體,而不是大學(xué)生的普遍現(xiàn)象。線上網(wǎng)絡(luò)作為一種新的溝通渠道,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對促進(jìn)大學(xué)生人際關(guān)系有著積極的作用。
其次,線下網(wǎng)絡(luò)中心性對學(xué)業(yè)成績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在課業(yè)網(wǎng)絡(luò)中主動尋求他人幫助(網(wǎng)絡(luò)外向程度中心性)、與其他同學(xué)討論,這些都能促進(jìn)學(xué)業(yè)成績的提升。處于線下課業(yè)和信息網(wǎng)絡(luò)中介的學(xué)生,其學(xué)習(xí)成績也相對較好。課業(yè)知識和信息都通過他們在線下進(jìn)行傳遞。但與假設(shè)相反,處于線上課業(yè)網(wǎng)絡(luò)中介的學(xué)生,其學(xué)業(yè)成績反而較差。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處于線上網(wǎng)絡(luò)中介時,課業(yè)內(nèi)容的傳遞更為便利,中介者本人也可能并未完全掌握所傳遞的知識內(nèi)容;而處于線下網(wǎng)絡(luò)中介時,中介者本人對課業(yè)知識已有過認(rèn)知加工。另一方面,線上溝通時非語言線索的缺失也可能影響了課業(yè)互動的效果,這一研究發(fā)現(xiàn)和解釋還需要在將來研究中進(jìn)行驗證。
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對教學(xué)管理有以下啟示:首先,應(yīng)鼓勵學(xué)生主動拓寬自己獲取信息的渠道,積極與同學(xué)進(jìn)行交流,增強自己獲取課業(yè)知識的能力,從而有助于學(xué)業(yè)成績的提高;其次,個體的網(wǎng)絡(luò)位置與其獲得與學(xué)習(xí)任務(wù)相關(guān)的知識、信息的難易程度有關(guān)。中介中心性高的個體處于信息和課業(yè)網(wǎng)絡(luò)的最短路徑上,更容易獲得與學(xué)習(xí)有關(guān)的知識,因而容易取得好的學(xué)業(yè)成績,但這種效應(yīng)只在線下網(wǎng)絡(luò)中存在,處于線上網(wǎng)絡(luò)中介的個體并未獲得更好的學(xué)業(yè)成績。因此,應(yīng)適當(dāng)為學(xué)生提供更便利的線下課業(yè)咨詢的方式,增強學(xué)生間的交流互動,并引導(dǎo)學(xué)生更多進(jìn)行面對面的溝通。線上網(wǎng)絡(luò)的過度便利及非語言線索的缺失可能會降低線上課業(yè)互動的效率。
本研究只是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在教學(xué)管理中的初步嘗試。將來研究可進(jìn)一步通過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的方法識別班級網(wǎng)絡(luò)中具有特殊位置的學(xué)生,以及這些特殊位置特征對其人際關(guān)系和學(xué)業(yè)成績的影響;其次,可以進(jìn)行班級內(nèi)小群體分析,從而可以掌握班級中非正式群體的現(xiàn)狀,有利于掌握班級中信息流向以及規(guī)范形成的規(guī)律,從而為班級管理提供內(nèi)容支持。最后,本文僅考察課業(yè)與信息兩種網(wǎng)絡(luò),情感網(wǎng)絡(luò)在大學(xué)生群體中也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今后研究可以比較不同類型的網(wǎng)絡(luò)對教學(xué)和學(xué)生管理的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 Borgatti S.P.,et al.,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J].science,2009,(16):892-895.
[2] Granovetter,M.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1360-1380.
[3] Borgatti S.P.and P.C.Foster,The network paradigm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A review and typology[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3,
(6):991-1013.
[4] Chen C.C.,X.-P.Chen,and J.R.Meindl,How can cooperation be fostered? The cultural effect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285-304.
[5] Markus H.R.and S.Kitayama,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1991,
(2):224-253.
[6] Chen X.-P.,et al.,Affective trust in Chinese leaders linking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to employee performance[J].Journal of Man-
agement,2014,(3):796-819.
[7] 第36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報告[R].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中心,2015-07-22.
[8] 申■,周策.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法在人際關(guān)系中應(yīng)用的研究綜述[J].中國電力教育,2013,(1):201-202.
[9] 陽志平,時勘.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在社會心理學(xué)中的應(yīng)用[J].社會心理研究,2002,(3):56-64.
[10] 葉勇助,羅家德.虛擬關(guān)系是真實關(guān)系的鏡射嗎[J].資訊社會研究,2001,(1):33-55.
[11] 羅群英.論大學(xué)生的網(wǎng)絡(luò)交往與現(xiàn)實交往的互動——網(wǎng)絡(luò)時代大學(xué)生社會化問題的思考[J].蘭州學(xué)刊,2006,(2):169-171.
[12] 郭金龍,陸宇杰,許鑫.基于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的大學(xué)生現(xiàn)實與虛擬社會人際關(guān)系研究[J].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2012,(12):91-95.
[13] 馮銳,謝英香.當(dāng)代大學(xué)生虛擬與現(xiàn)實社會人際關(guān)系的差異性分析[J].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2009,(1):28-32.
[14] Krackhardt,D.,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The importance of philos in organizations[M].i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Structure,form
and action,N.Nohria and R.G.Eccles,Editor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Boston:1992:216-239.
[15] Mehra A.,M.Kilduff,and D.J.Brass,The social networks of high and low self-monitors:Implications for workplace performanc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1,(1):121-146.
[16] Sparrowe R.T.,et al.,Social network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2):
316-325.
[17] Cross R.and J.N.Cummings,Tie and network correlates of individual performance in knowledge-intensive work[J].Academy of man-
agement journal,2004,(6):928-937.
[18] Ibarra H.and S.B.Andrews,Power,social influence,and sense making:Effects of network centrality and proximity on employee per-
ception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3:277-303.
[19] Baldwin T.T.,M.D.Bedell,J.L.Johnson,The social fabric of a team-based MBA program:Network effects on student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6):1369-1397.
[20] 葉新東,朱少華.大學(xué)生社會網(wǎng)絡(luò)與學(xué)習(xí)的相關(guān)性調(diào)查研究[J].電化教育研究,2007,(2):32-37.
[21] Freeman L.C.,D.Roeder,R.R.Mulholland,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II.Experimental results[J].Social Networks,1979,(2):119-141.
[責(zé)任編輯 史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