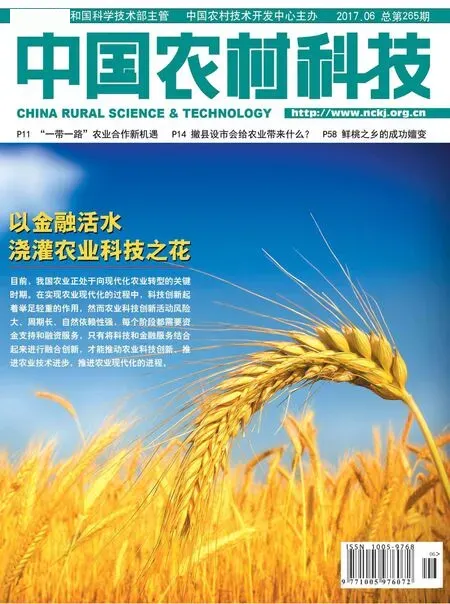撤縣設市會給農業帶來什么?
本刊記者|柴帆
撤縣設市會給農業帶來什么?
本刊記者|柴帆
近日,國務院發布的撤縣設市名單引發了公眾猜測。有人認為,撤縣設市這一封閉已久的大門即將打開,不僅促進了當地資源的高效集聚,更為發展當地現代農業提供了機遇。但是,隨之而來的農業功能弱化、土地財政陰謀也讓不少人擔心撤縣設市會影響到我國的糧食安全。

日前,經國務院批準,同意湖南省撤銷寧鄉縣,設立縣級寧鄉市;陜西神木縣撤銷,設立縣級神木市;浙江玉環縣撤銷,設立縣級玉環市;河北平泉縣撤銷,設立縣級平泉市;四川隆昌縣撤銷;設立縣級隆昌市。
五天之內,六地密集撤縣設市。今年以來,已有四十余縣提出加快撤縣設市步伐,主要集中在安徽、青海、貴州等省。有人認為,這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在去年個別縣“謹慎解凍”之后,暫停了20年的撤縣設市開始正式重啟。
我國歷史上的撤縣設市
撤縣設市,顧名思義就是將原來的行政單位“縣”改名行政單位“市”,但縣級市仍然屬于地級行政區或省級行政區管轄。
在國務院發布六地撤縣設市的消息之后,各地網友便活躍了起來。有人說:“市也好,縣也好,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增進民生福祉,都是讓老百姓對未來有更好的預期。”也有人說:“一字之差,領導肩負的責任更大了。”
追蹤溯源,我國首次的撤縣設市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五年。1983年3月,江蘇省常熟撤縣建市,設立縣級常熟市,成為我國第一個撤縣設市的城市。發展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出現大規模的“撤縣設市”熱潮,最高峰時,撤縣設市的數量多達445個。
無論是獨立設置的市,還是城市下轄的區,本質上都是指區域載體功能較為完善、已經城市化的地方。撤縣設區、撤縣設市、撤鎮設市,如果僅僅是拼湊,僅僅是為了“行政功利”,就會將“市”從城市屬性中游離出去,喪失應有的基本意義。
當時許多地方盲目追求“縣改市”,造成縣級市市區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城郊比例失調,城鄉概念模糊等“假性城市化”問題。由于以上問題的逐漸加重,1997年,國務院暫停了實施十一年多的撤縣設市政策。
從此,我國縣級市的數目基本上是處于逐步減少的狀態。自從1997年叫停撤縣設市政策以來,截至到2013年,16年間,幸運實現“縣改市”的地方屈指可數。
就在縣級人民對撤縣設市已經不抱有多大希望之時。2013年一月,民政部卻罕見地一次性批準了兩個縣改市,分別是吉林扶余和云南彌勒。
吉林扶余和云南彌勒的“美夢成真”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政策信號似乎讓縣級政府們再次看到了希望。人們紛紛猜測,政策解禁的大門已經開啟。隨著城鎮化發展規劃頒布時間日趨臨近,各地除了著力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更多的是開展大規模的中小城市建設,撤縣設區、撤縣設市、撤鎮設市由此將成為一股“大潮”。撤縣設市這股熱潮就像一口“不斷升溫的高壓鍋”,洶涌而來。
熱潮背后的催化劑
如今,打開很多縣級政府的官方網站,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關鍵詞:撤縣設市。這四個字飽含了縣城人民對“市民夢”的渴望。
一些地方之所以熱衷于撤縣設市,自然有其好處。從縣到市,不僅僅是一個名字的變化,更會帶來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影響和變化。無論是上級政府給予的經濟發展角色定位、還是轉移支付、專項扶持資金、包括招商引資形象,都千差萬別。
行政區“撤縣設市”或“縣改區”有利于精簡機構,合理配置地區經濟、社會資源,提升核心區規劃建設和整體管理水平。市的影響、聲譽要比縣高,有利于提高居民的自豪感,也有利于招商引資、吸引人才。此外,市比縣的行政管理范圍更寬,行政管理權限更大,如果升格成地級市,還可以在“代管”附近的縣和縣級市時,得到更多的實際利益。相對于縣來說,改市之后更容易爭取到更多的項目、資金和政策以及可觀的城市建設費用。
當然,在這些看得見的好處背后,還有領導更容易受到重視和提拔、當地公務員可以獲得高一等級的行政級別和工資補貼等更多的基于權力自肥的“行政功利”,同樣也在催化撤縣設市的熱潮。
無論是獨立設置的市,還是城市下轄的區,本質上都是指區域載體功能較為完善、已經城市化的地方。撤縣設區、撤縣設市、撤鎮設市,如果僅僅是拼湊,僅僅是為了“行政功利”,就會將“市”從城市屬性中游離出去,喪失應有的基本意義。
一股腦地撤縣設區,也與國家加大中小城鎮建設、提升城鎮化質量的要求背道而馳。因此,面對新一輪的撤縣設市沖動,務必做到具體情況具體對待,保持應有的清醒和謹慎。
撤市設縣給農業帶來了什么?
縣與市的最大區別就在于“農業”這個功能定位上。全國農業人口主要集中在縣域,縣以農業為主,定位重點在農業,目標是促進農業生產,市則以工商業或者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為主。其次,縣涉農部門較多,市則以城市經濟和城市管理部門設置為主。再者,上級政府轉移支付或者專項扶持資金也有差別,縣只能用于農業相關領域,而市可以用于城市相關領域。
“縣改市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否則我們的人口就會向大城市無限集中,就會導致一些城市房價上漲等問題,大城市已經飽和,小城市還沒發展起來,這是一種斷裂,因為所有大城市都是小城市發展而來。”華東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經濟系、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林拓說到。

中國當前的農業生產目標已經從解決吃飯問題轉向追求經濟效益,而從事農業能不能帶來較高的效益、農民愿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資金愿不愿意往農業領域投入,并不取決于政府部門重視還是不重視,而是取決于有沒有市場需求,有多大的市場需求。為什么最富裕的農業區都是在大城市周邊的郊區,為什么蔬菜爛在地里都是出現在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區,就是這個距離半徑能否解決市場需求的問題。
撤縣設市以后,城市發展起來,實際上是為農業解決了市場需求不足、農產品賣不出去的問題。同時,縣改市能夠更好地將農業從業人員聚集在當地,吸收高技術的農業從業人員、高新農業技術公司等進駐,從而解決當地農業從業者稀缺的難題,為發展當地現代農業提供了難得機遇。

但是,由于撤縣設市以后,行政職能對農業的重視程度降低,定位重點也將從農業轉向社會經濟管理。許多人擔心,縣改市農業功能弱了,會不會妨礙農業,給農業帶來負面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表示,如果配套的法律法規能夠有效跟進,避免城市盲目占用耕地,撤縣設市反而會帶給農業提質增效的機會。比如,縣改市后,不能自行盲目地增加城市建設區的面積,不能隨意地去調整城市規劃,不能突破國家有關耕地保護的法律法規。如果這些方面的要求能夠得到遵守,應該問題不大。一個地方城市發達,農業也容易發達。高水平的城市也容易有高水平的農業。這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做不好,會出現問題。但是做好的可能性更大。關鍵是要有好的規章制度,好的體制。
警惕撤縣設市后的“土地財政”陰謀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肖澤晟認為,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財政最大化的沖動是撤縣設區的重要原因。
一般熱衷于撤縣設區的地方都是城市規模比較大、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較大的轄區市,且現有城市土地資源不足以支撐城市的進一步擴張,因而有將所轄地距離較近的縣改為區的強烈沖動。縣改為區后,廣闊的農村土地會納入城市規劃區范圍,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事實上將逐步變為國有土地,土地財政收入也會有很大提高。
當前,在我國的城市發展過程中,一些地方,把水源好、肥沃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設,導致良田銳減。由于國家要求嚴格執行占用耕地補償制度,弄虛作假也時有發生,田地的征收、耕地補充等環節,都暴露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以江西省余江縣為例,據《新法制報》2013年報道,余江縣以“建設優質高中校園”為名征用525畝良田,但之后卻被用于房地產開發。按照國務院在2004年下發的《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各類非農業建設經批準占用耕地的,建設單位必須補充數量、質量相當的耕地,補充耕地的數量、質量實行按等級折算,防止占多補少、占優補劣。余江縣補充的耕地在余江縣平定鄉前山村上俞村小組,但這片“補充耕地”實則是一片紅土地,只能種種花生,其質量也無法與原水田相比。
如今,一些縣動輒就是“舉全縣之力”撤縣設市,政府目光所及之處,仍是農民的土地變現的“錢景”。不僅沒有心思發展現代農業、新型產業、社會服務業等,甚至連基本的城鄉公共服務也缺乏熱情。這樣“舉全縣之力”、“撤縣設市”的做法,依舊是一種以追求GDP為目的的政績工程,與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相去甚遠。
“撤縣設市”之后帶來的“土地財政”陰謀,尚需相關政府部門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