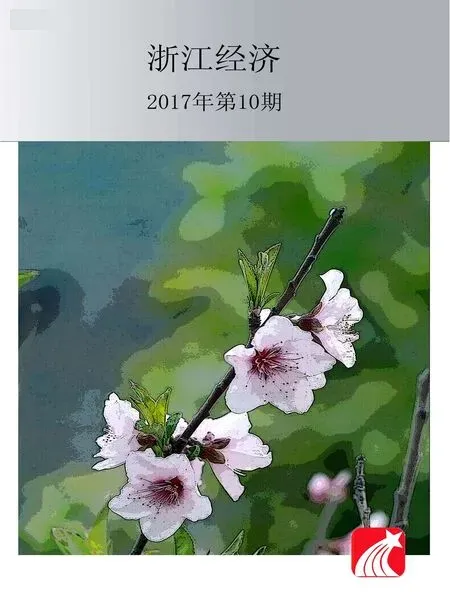浙江供給側改革的創新重點
□徐劍鋒
浙江供給側改革的創新重點
□徐劍鋒
浙江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清醒認識并克服現存的短板與不足。供給側改革創新要圍繞生產要素結構優化、產品結構升級與公共服務完善來進行。由于產品結構的調整優化主要取決于市場需求因素與生產要素構成的變化,要素供給的優化應成為浙江供給側改革創新的重中之重
在經濟新常態下,浙江經濟增長需要更多地借助供給側創新。浙江要根據自身實際,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清醒認識并克服現存的短板與不足,通過改革創新,提高浙江供給的效率、激發需求增長,從而推進浙江經濟穩定高效發展。
浙江要素、產品與公共服務供給的優勢與短板
隨著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浙江在要素供給、產品與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優劣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一)生產要素供給的優勢與短板
從生產要素的供給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浙江的要素供給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土地等自然資源與勞動力的傳統優勢已轉變為劣勢。受人口密度、生活水平以及城鄉土地二元分割等因素影響。浙江地價在全國居于較高水平,無論是杭州、溫州還是普通縣市的房地產價格基本上遠高于大多數省區,工業用地需要政府的專門優惠供給與補貼,人才引進要靠政府專門的人才用房特供,這已嚴重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
技術(人才)高級要素的供給在全國處于中上水平。但長期來浙江高校與科研院所的數量與質量相對不足,相較于京、津、滬與武漢、西安、南京等大城市,浙江技術與人才仍處于劣勢。
再從另一高級要素——“企業家”的供給看,浙江具有一定的優勢。得益于發達的民營經濟,浙江每萬人中的個私企業主數量遙遙領先于其他省市區。但也要看到,浙江在這方面也存在著很大的不足:大多個私企業主仍停留在“經營者”的層面上,遠未達到“企業家”的層級。具有長遠發展的戰略眼光、進取冒險而非投機取巧精神的“企業家”是創新的核心與基礎,這正是浙江眾多急功近利的經營者所欠缺的。
資本已成為浙江的優勢要素。但從結構上看,浙江大量的民間資本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沉浸于虛擬經濟領域,熱衷于短線炒作與投機,而中長期的產業資本與風險資本仍顯不足。
(二)產品供給的優勢與短板
浙江工業制成品的供給優勢集中于服裝、紡織、五金、輕工機械等傳統消費品領域,隨著多年來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消費類電子產品與汽車等設備正逐步建立起相對優勢。

在第三產業,浙江的優勢產品集中于商貿業,隨著多年來浙江旅游業、金融業與信息服務業的較快發展,這些服務產品優勢正在顯現。
整體而言,浙江工業制成品的構成及行業結構相對于江蘇、廣東、山東等發達省市,仍處于較低的層級。在服務業構成上,與上海、北京等發達地區相比仍有不足,但在全國省區中已建立起相對優勢。
產品供給結構的調整優化更多地取決于市場的引導,浙江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較高,在產品服務需求結構變化的基礎上,只要生產要素結構保持有效的升級轉換,浙江的產品供給結構能適時地進行調整優化。
(三)公共服務供給
作為中國的一個省區,浙江在體制與政策領域的供給與全國基本一致,但在地方性具體的制度與政策方面,浙江具有創新性與靈活性的優勢。但也要看到,這一優勢在目前其他省區不斷創新趕超的情況下,已有所淡化。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方面,浙江的辦事效率與服務一直領先于全國多數地區。
供給側改革創新的重點
浙江供給側改革創新要圍繞生產要素結構優化、產品結構升級與公共服務完善。由于產品結構的調整優化主要取決于市場需求因素與生產要素構成的變化,要素供給的優化應成為浙江供給側改革創新的重中之重。
(一)創新土地供給制度,推進土地市場化與一元化
長期來,浙江經濟的持續發展與城市化受到二元化與非市場化的土地供給制度的強制約。城鄉土地的二元化分割推高城市房地產價格,嚴重影響了市場公平競爭,并造成城鄉差距的固化。多年來,浙江在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為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提供了助力,但受制于全國性土地制度與政策安排,至今仍沒有打破二元化分割與行政化操作。
近中期看,浙江首先可以在農村住宅用地的可流轉方面創新,爭取在全國先行先試。在農村與城市戶口統合的基礎上,應允許進城農民的多余宅基地及其附屬的合法建造的房屋,在政府征收相關稅費與村集體提取適當福利的條件下,依法轉變為國有住宅用地與商品房、取得不動產權證,自主向城鄉居民轉讓。這既可以提高農村集體與村民的收益,又能吸收城市資金與人才留住鄉村,減少農村空心村與土地資源浪費現象,縮小城鄉差距,同時又增加全社會住宅用地供給,抑制城市高房價。
其次,浙江應爭取在辦公與商業用地與居住用地的統合方面先行先試。隨著電子商務與信息經濟的飛速發展,“居住”與“辦公”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而辦公用地使用年限僅有30-50年,居民不能在寫字樓落戶籍,用水用電價格高、沒有管道煤氣供應等,造成省內寫字樓庫存不斷增加,空置現象嚴重。同樣,受電子商務的沖擊,大量商業用房的庫存也不斷增加。要及早探索創新制度與政策,將部分積壓嚴重的寫字樓與商業用房,通過補交土地金、增加煤氣等設施供應,延長使用年限或轉變為居住用房。從長遠看,應打破辦公、商業與住宅用地的人為界限,由市場化發揮主導作用。
(二)抑制資本泡沫,透過市場引導資金向實業流動
近年來,浙江經濟增速放緩,實體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大量的民間資金向虛擬經濟流轉,熱衷于短線炒作,資金的短期化與泡沫化嚴重,加劇了實體經濟的困難。政府要透過市場,通過稅收調節、資金監控管理、窗口指導等方式,引導民間短期熱錢向中長期資本回歸;取消政出多門的各種補貼優惠扶持資金,建立優惠政策的“總籃子”,集中統一使用以提高效率;政府資金宜更多地通過參股風險投資資本與中長期產業基金的方式,引導與促進風投與產業基金的壯大,為浙江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穩定而堅強的助力。
(三)促進“經營者”向“企業家”轉變
在現有的“三名”(知名企業、知名品牌、知名企業家)工程基礎上和“個轉企、小升規、規改股、股上市”的企業升級工作基礎上,加快推進民營企業向現代企業過渡,加快培育職業經理人隊伍、擺脫家族制企業的束縛,促進企業的規范化與社會化轉變;鼓勵企業制度創新,根據行業與環境特點,創新有限公司制度,如新型“股份兩合公司”等公司制度,以適應主要經營管理者、股東、社會資本與消費者的新需求。
另一方面,加強對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的培育引導。主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依托市場化的中介組織,開展對企業經營管理干部的現代管理知識、經濟、科技、法律、文化等綜合培育,要使經營管理者深入了解經濟、科技的歷史與未來發展趨勢,創新思維,樹立起長遠發展的戰略與眼光,摒棄急功近利意識,培育與宣導“和合”文化與協作精神,建立起“既爭做雞頭、又甘當鳳尾”的理念。
(四)產品創新與生產方式創新應成為企業創新的兩大支柱
技術創新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效率。新產品(包括新服務)是激發新需求的主要動力,生產方式的智能化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方式。因而新產品與新工藝應成為提高供給效率的兩大支柱。一方面,浙江要進一步明確“新產品”的定義,注重新產品的功能性創新,而不是在產品包裝與改名上打爭取優惠政策的擦邊球;在有關激勵政策上,更多地引入“新產品比率”、研發投入與產出比率等考核指標;促進新產品研發更多地采用政府提供基礎研發補助、減免稅扶持等政策,對新產品銷售給予一定年限的消費稅、增值稅減免優惠,鼓勵其成長。另一方面,大力推進制造的智能與全生產鏈的智能化。著重發展工業領域以CPS為核心的物聯制造,以及3D印制、工業機器人等,同時,通過消費互聯網、產業互聯網、物聯網,將融資、物流、營銷、消費與售后服務等與生產實現智能化鏈接,從而實現全過程的智能化。
(五)全面減稅減負,鼓勵新興產業的創業創新
減稅減負是供給制度與政策創新的核心內容。浙江宜以稅收機制改革為重點,為企業減負減壓減成本,以提高其供給效率。對現有的稅費作全面的清理,在國家政策許可范圍內減稅減費,并形成長久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對鼓勵發展的新興產業領域的初創企業,應根據企業的成長周期及其特點,爭取統一地方政策與各部門政策,建立起優惠政策“總籃子”與“分籃子”,給予一定年限的減免稅與產業基金供給等扶持。
(六)完善政府服務
以“建立親清的政商關系”為目標,簡政放權,全面推行“負面清單”管理,進一步提高浙江各地政府的服務效能,從企業注冊創辦,到研發設計、生產流通、銷售全領域內,消除公務人員不作為或亂作為的現象,助力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加強各地與各部門的相關政策措施的協同,避免政出多門,落實權責利的統一;借鑒深圳、天津等地的政府創業創新服務團隊的經驗,定人定員,直接聯系企業,提高政府服務的針對性與效率,同時建立起企業與群眾的監督機制,建立新型政商關系。
作者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