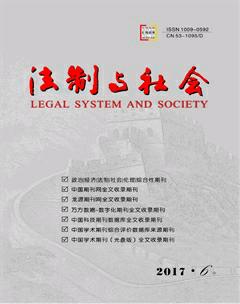高利貸的本質及其入罪問題的初探
摘 要 關于高利貸是否應該入罪的爭論中,肯定與否定兩方均沒有抓住本質,顧左右而言其他。高利貸的本質是“閻王債”,其作為一種金融模式,是“自殺式金融模式”,嚴重危害經濟發展。從危害生命和危害經濟出發,本文得出“過高利息的借貸行為一定應該入罪”的結論,并提出應借鑒國外經驗,謙抑性與威懾性相結合,盡快出臺《反高利貸法》。
關鍵詞 高利貸 本質 入罪
作者簡介:朱玳萱,中共深圳市委黨校福田分校講師,研究方向:法社會學、政府依法行政、社會基層治理法制化。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256
作為一個現實,我國關于什么是高利貸是有明確界定的。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 (以下簡稱《通知》) 中規定 “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 ,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 的4倍 。超過上述標準的,應界定為高利借貸行為 。”因此,“4倍標準”,成為界定高利貸的法定標準。
同樣作為一個現實,我國高利貸既不受法律保護,也不受任何經濟懲罰,更不入罪。《通知》明確規定“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但對超過4倍標準的,我國既沒有規定民事懲罰性法規,在刑事立法方面也沒有相應的罪名和刑罰規制。
本文主要關注“過高利息的借貸行為一定應該入罪”。本文的觀點是,過高利息的貸款,無論是機構貸款還是民間個人借貸,都應該入罪。例如,如果“4倍標準”不足以讓高利貸入罪,那么10倍、100倍標準一定應該入罪。至于究竟高到什么程度的高利貸應該入罪,可以討論,但不是本文要旨。
一、 高利貸的本質
學界很多學者討論高利貸之利弊,但并沒有緊緊抓住高利貸之本質。
(一)高利貸的本質是閻王債
民間流傳:高利貸,閻王債。所謂閻王債,簡單說就是要命的債。范才友、蔣志強在中國法院網撰文說:“筆者通過百度搜索引擎共搜得與‘高利貸、‘自殺有關的網頁約計281000個。血淋淋的事實迫使我們必須對高利貸破壞人民生活安定的現實給予高度的關注。”
可是,在中國知網中查閱大量關于高利貸的論文,無論是贊成、或是不贊成高利貸獲罪,都鮮有學者站在保護生命的高度來重視高利貸問題。毫無疑問,如果危及生命的借貸都不入罪,還有什么行為應該入罪呢?在今天,在憲法保護生命權,執政黨秉持人本關懷的今天,對高利貸行為不入罪的現狀顯然不能繼續下去。
有學者借口我國金融的制度性缺陷,如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放貸嚴重不足,為高利貸開脫其罪。但應當認識到,高利貸也是一種金融制度。如果說,我國金融存在制度性缺陷,那么高利貸必然存在“要命的”制度性缺陷!用高利貸去彌補我國金融的制度性缺陷,無疑是用冰塊堵塞螻蟻之穴,可笑之極。
也有學者認為高利貸乃意思自治所致。然而,正常人都知道這種形式上的雙意性往往掩蓋著強制性的本質,甚至是“要人命”的意思自治。事實是高利貸是非理性借貸。“任何一個理性借貸人的內心都會對高利貸深惡痛絕,除非這個人瘋了,否則沒有人會甘愿忍受高額利息的盤剝。” 對于人們深惡痛絕的非理性,刑法亦應規制。猶如超過限度的“自由”必須受刑法規制一樣。
(二)高利貸的本質是“整體模式”違法
從實然看,有一種誤解,即我國司法實踐雖然無法對高利貸予以刑事處罰,但可以通過對高利貸形成過程中的伴生性違法行為——如非法經營罪、非法拘禁罪、涉黑類犯罪等進行補漏性處罰,如此便可防止高利貸行為的發生,或言以此防止了高利貸的社會危害性。然而現實是,這種理解只是一種與實際背離的假想而已。
根據江蘇溧水縣法院受理的18 起非法拘禁案,其中15件是由高利貸引發。 同樣,“于歡案”爆出年息120%的高利貸,引發黑勢力介入進而導致人命案。竟然一些學者據此認為,“這說明非法發放貸款的‘惡并不主要在于高額利息而是‘惡在它討債過程中運用的黑惡手段。”
這顯然是本末倒置,是對高利貸本質認識嚴重不足的體現 。
首先,任何誘發放貸者鋌而走險的原因必然是追逐高利貸的高額利潤所致。因而,高利貸是源頭,鋌而走險是“末”。源頭不治理,一味治理“末”端,豈不本末倒置。
其次,我們應該認識到,高利貸同樣是一種金融模式。與商業銀行的抵押性借貸模式相比,高利貸的模式是:不需要資產證明,不需要“抵押”,甚至利率也可以口頭約定,其次,配套方法是采用各種“涉黑”手段保證其收回貸款和利息。可見,高利貸模式在構成上包括“高利貸+涉黑手段保障”。那些把高利貸與其黑手段分開,追究“涉黑”的犯罪責任,卻不追究高利貸行為的犯罪責任,顯然不具科學性。
(三)高利貸的本質是“自殺金融模式” ,嚴重危害經濟發展
當代西方經濟學部分學者如哈耶克秉持堅決捍衛自由市場秩序的理念;而另一部分學者如凱恩斯則主張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政府干預來影響市場經濟過程。關于民間借貸及其利息,我國部分學者秉持自由市場觀念,認為利息應以市場來調節。理由是,自由的市場會充分調節借貸平衡,在充分市場條件下,利息會逐漸趨于平衡,不可能太高。結論是要通過改革來完善市場,而不是限制利率。如茅于軾教授認為:民間借貸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重要途徑。應該將民間借貸合法化、公開化、透明化。并聲稱“避免高利貸最好的方法是鼓勵大家放高利貸,而不是禁止,越禁止,利息率就越高”。 這種認識有幾個方面需要商榷。
一是充分市場誤區。顯然,無論我國還是西方國家,充分市場只是理論假設,不是現實存在。因此大多數西方國家嚴禁高利貸。顯然,在不充分市場的現實狀態中,借貸均衡不可能通過市場自由調節來實現。借貸利息太高——例如“于歡案”中高于20倍標準——顯然是扼殺經濟發展。
二是混淆高利貸與民間借貸。必須指出:高利貸和正常的民間借貸有本質區別。從金融模式角度看,民間借貸作為一種金融模式,以正常的資金收益率助力經濟發展,與商業銀行等金融模式形成互補。而高利貸也是一種金融模式,但它是“自殺金融模式”。之所以稱之“自殺金融模式”是因為:(1)借貸利率高得離譜,如“于歡案”中,借貸年利120%,本身就是對財產權益的極大侵害。中小企業或借貸人,得到的不是解救,而是“被殺害”、“被搶劫”。(2)借貸利率高得離譜,本身就是對金融秩序破壞。由于高利貸獲得巨額收益,必然導致民間資金大量流向高利貸,如“于歡案”中的高利貸的放貸人是房地產商。房地產在我國經濟中占據及其重要地位,如果地產商的資金大量流向高利貸,對我國金融的破壞是不可想象的。(3)如果高利貸對發展經濟有利,那么,何以我國要對商業銀行的利率進行規制?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金融,是用高得離譜的借貸利率來發展經濟的。凡此種種,對同樣活躍在金融市場的商業銀行有何平等而言?對商業銀行在國家的金融命脈上的功能、尤其對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作用將如何保障?
三是很多小微企業事實上并沒有借高利貸,而是正常的民間借貸。2013年公布的《小微企業融資發展報告:中國現狀及亞洲實踐》調查結果顯示, 59.4%的微小企業的借款成本在 5%至 10%之間,更有四成以上的微小企業表示借款成本超過10%。10%的借款成本大致相當于“2倍標準”,遠遠達不到“4倍標準”——即高利貸標準。 由此可知嚴懲高利貸的立法對培育和發展市場是沒有多大風險的。
二、高利貸入罪研究
顯然,揭露高利貸的本質,目的是要科學管控高利貸。有學者認為,個人性質的高利貸,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只需用民事法律調節即可將其限定于無害的范圍之內。而機構性質的高利貸,具有社會危害性,應該予以刑事懲罰。 這是對高利貸本質認識的混亂。我們呼吁,盡快出臺《反高利貸法》,無論是個人性質的高利貸還是機構性質的高利貸,都應該受到刑罰。
(一)高利貸入罪問題探討不能違背人之常情
今年4月5日最高法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山東調研時指出:“司法審判不能違背人之常情”、“我國有著數千年文化傳統,天理、國法、人情是深深扎根人們心中的正義觀念,蘊含法治與德治的千古話題。所謂天理,反映的是社會普遍正義,其實質就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所向關系到執政根基。”
在我國,人們對高利貸的認識是發展變化的。解放后,高利貸一度銷聲匿跡。那時高利貸是妻離子散、剝削壓迫的象征。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資金的巨大作用日益凸顯,加之資金短缺以及我國金融的制度性缺陷,高利貸死灰復燃,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然而,從蘊藏國人心中的情理看,高利貸是“閻王債”,依然是妻離子散、趁火打劫以及不正當行業的代名詞。從“于歡案”民怨沸騰可窺一斑。“于歡案”借貸年息120%,大約是基準利率計算的24倍。很顯然,24倍基準利率只能破壞金融秩序而不是相反,并且很難讓人從情理上忍受。但法院無法從高利貸角度判案!由于放貸者是地產商,聲稱放貸資金屬于自有資金(近年來幾大高利貸案的辯護,均說是自有資金。 如果屬實,也很難判其“非法經營”。那么,就只能用非法拘禁和涉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由來判罪。試設想,在這個具體案件中,如果沒有高利貸,涉黑案件豈不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值得借鑒的是,丹麥刑法典規定了不得“趁火打劫”。其第 282 條規定:利用他人嚴重經濟和身體方面之困難、無知、無責任能力或者對行為人之依賴情狀,以圖在合同中得到或規定適當回報之外給付、 無正當理由給付的,構成高利貸罪,從重處以不超過六年之監禁。瑞典、芬蘭均有類似法規。 如果我國刑法對趁火打劫、妻離子散的高利貸熟視無睹,何談刑法的人道主義原則。對高利貸的不予刑事處罰,就是一種放縱,就意味著對大多數受害人的不人道。
(二) 高利貸入罪的規定應該考慮謙抑性與威懾性
動用刑罰必須考慮謙抑性和威懾性。刑罰雖然有威懾性,但也不能泛化并導致對社會經濟生活的過度干預,而應該通過科學立法體現出動用刑罰的謙抑性、適度性和必要性。對此,可借鑒國外和境外的經驗。
一是借鑒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 203 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周年利率為百分之五。這條規定,能夠推動民間借貸利率公開化、陽光化。大量的高利貸使用口頭約定方式,目的就是制造“取證難”之局面,規避法律制裁。把利率放到陽光下,這是利率規制的基礎性工作。
二是借鑒日本做法,分別對機構型民間借貸與個人型民間借貸的利率予以規制。日本相關法律規定,對于貸款業者而言,處罰高額利息的上限是年20%,對于一般債權人即一般私人貸款而言,處罰高額利息的上限則是 109.5%。 這樣,只要行為人簽約或領受超過上限利息,就應受到刑事處罰。
三是借鑒美國經驗,經濟性規制與刑罰相結合。美國法律規定,如果放貸人索取的利率高于所在州的法定最高利率,則該借貸合同無效,如果借貸人不償還借貸,放貸人沒有追索借貸人償還貸款的權力。美國《反欺詐腐敗組織法案》規定:如果利率超過各州規定的法定最高利率的2倍,不管是金融機構借貸還是民間借貸,都構成“放高利貸罪”,屬于聯邦重罪。
四是關于“4倍標準”的規定。我國2017年基準貸款利率大約是年息百分之四點多,取整數5%計算,4倍標準就是年息20%以內,10倍標準就是年息50%以內。現實中的個人高利貸遠遠超過50%。即便按照10倍標準規制高利貸,也能拯救很多高利貸者的性命。加拿大刑法規定,年利率超過60%即構成高利貸罪。德國最高合法利率為20%,美國新澤西州個人利率超過30%被認定為高利貸。可見,各國對個人借貸的利率均有規制。即便4倍標準不刑罰,10倍或20倍標準一定應該刑罰。
綜上所述,看不到高利貸的本質,就容易顧左右而言其他。應借鑒國外經驗,在立法方面應當堅持謙抑性與威懾性相結合的基本理念的前提下,盡快出臺《反高利貸法》。
注釋:
范才友、蔣志強.論高利貸的刑事責任.中國法院網.[2008-02-03].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8/02/id/287329.shtml.
潘庸魯、周荃.民間借貸、高利貸與非法發放貸款疑難問題探究——兼對“非法發放貸款”入罪觀點之批駁.金融理論與實踐.2012(1).95,94.
劉慶傳.重拳打擊“高利貸”.新華日報.2009年12月22日.
葉檀.高利貸是自殺金融模式.財經網.[2012-04-06].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95-34756.shtml.
姜琳琳.茅于軾:避免高利貸最好方法是鼓勵大家放高利貸.南方人物周刊.[2011-06- 24].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626/4194240.shtml.
金逍宏.高利貸的界定應考慮交易成本.理論觀察.2013(8).66.
龔振軍.民間高利貸入罪的合理性及路徑探討.政治與法律.2012(5).49,48.
劉偉.論民間高利貸的司法反正化的不合理性.法學.2011(9).133-135.
劉植榮.全球高利貸的合法式生存.鳳凰財經網.[2013-01-14].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114/7551797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