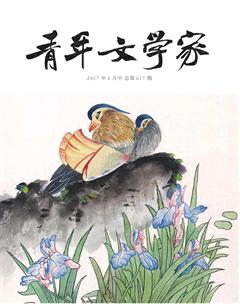“三美論”下《葬花吟》英文譯本對比賞析
摘 要:《葬花吟》是《紅樓夢》中最經典的詩篇之一,以其絢麗的意境、悲憤的格調、優美的文辭、鏗鏘的音韻傳唱至今,它是林黛玉感嘆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帶有一種黛玉式哀傷,其精湛的藝術價值值得進一步挖掘和探討。本文從許淵沖詩歌翻譯的“三美論”角度出發,對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和霍克斯的《葬花吟》兩英文譯本(以下簡稱“楊譯”和“霍譯”)進行對比賞析。
關鍵詞:“三美論”;《葬花吟》;詩歌翻譯
作者簡介:閆晴(1996-),女,漢族,遼寧錦州人,四川農業大學人文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英語專業。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7-0-01
《葬花吟》是《紅樓夢》經典詩詞的名篇之作,以豐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畫面,濃烈而憂傷的情調,展示了黛玉在冷酷現實摧殘下的心靈世界,奏響了黛玉感嘆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血和淚凝結成的五十二句的《葬花吟》曾被中外學者翻譯多次。而“三美”論是由中國著名翻譯家許淵沖提出來的詩歌翻譯理論,即意美、音美,形美。
一、意美
意境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靈魂。《葬花吟》作為“紅詩”中代表性最強的一首,是黛玉自作的暗示其悲劇命運的詩讖,將凄婉哀傷的意境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原詩開篇用花謝,花飛,紅消,香斷,游絲,春榭,落絮等意象奠定了全詩悲涼凄婉的情感基調。對于“紅消香斷有誰憐”這一句,楊采用反詰語直譯原詩,再現原詩的情感,而且“the fade red”更是體現出中國古典詩歌那種落紅滿地的傷春之感,而霍將“香”和“紅”分別譯為 fragrance 和 bright hues,缺少了原詩的意味。“荷鋤歸去掩重門”和“青燈照壁人初醒”這兩句中,“掩重門”楊譯為“the lodge is locked and still”,lodge 兼有“寄居”和“監禁”的含義,再現了原詩庭院深深、處境凄涼的聯想意義,而霍譯為“goes in at door”,只譯出“門”的字面意思。“青燈照壁”楊譯為“A green lamp lights the wall”既突出了照的動作又突出了青燈這一意象,而霍譯“the lamp lit walls”的中心詞是 walls,沒有譯“青”字,損失了清幽,冷清的意境。原詩結尾兩句楊采用反詰句,加強原詩的感情力度,用 care for 譯“知”更能傳達黛玉內心的悲傷與孤寂的情懷,使原詩悲涼凄楚的意境得以再現。而霍譯最后一句采用陳述句句式,用詞過于平實,減弱了整首詩的凄涼哀怨之感。
二、音美
《葬花吟》原詩在語言風格上效仿初唐體的七言歌行,而且平仄韻交替,抑揚錯落,音韻自然,節奏明快。全詩共由十三個四行詩組構成,四句一韻,前八節韻式上主要采用中國古典古詩慣用的單韻形式aaba。霍譯本每一個詩行均采用了英詩中慣用的五步抑揚格,運用英雄體對偶句,即aabb,實現了aa或bb的連韻,彌補了英詩節奏緩慢的缺憾,使音節回環復疊,韻律更加整齊。而楊譯本采用的則是隔行押韻的韻式,即abcb,更能體現中詩的抑揚頓挫,更有節奏感。兩譯者采用的押韻方式不同主要是因為譯者的文化語言背景不同,除了二者都運用了的基本的尾韻和頭韻之外,霍譯本還運用了更多的半諧韻和輔韻,使譯文更加朗朗上口,音律和諧自然。
三、形式美
原文為古體詩,以七言為主,詩歌詞句整齊,只有三行字數不同,即第16行,第39行,第40行。第16行,有十言,“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第39行,有三言,“天盡頭”第40行,有五言,“何處有香丘”。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斯都采用了以詩譯詩的方法,使用格律詩的形式,盡量與原詩保持相同的結構,最大程度的忠實于原文,再現了原文的形式之美。霍譯本中47行含有10個音節,3行含有9個音節,只有2行含有11個音節,基本還原了原詩形式上的整齊和勻稱。但霍在追求形式上的高度一致之后卻損失了意境上的美,這使譯文難免有些遺憾之處。而楊的譯文對此沒有給予太多關注,譯文中出現了從7個音節到14個音節不等的詩行。
四、總結
本文通過詩歌翻譯的“三美”理論,對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斯的《葬花吟》兩英文譯本進行了對比賞析。楊多用直譯,保留原文的中國詩歌特色,更加忠實于原文的意境和精神,而霍多用意譯,轉變形式,使譯文更符合英美文化,更易于外國讀者接受。所以,意境與風格的再現楊更勝一籌,音韻和形式美的展現霍譯堪稱典范。中國古典詩歌非常重視意境和音律,翻譯中既要譯使文精美,又要傳達原文的意境格律,使音、形、意的美感得以再現,因此譯者需要不斷探尋更合適的翻譯方法和策略。
參考文獻:
[1]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2]許淵沖.文學與翻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楊憲益.戴乃迭.A Dream of Red Mansion[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4]David Hawkes. John Minford. The Story of the Stone[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5]隋婧文.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簡評黛玉哀音《葬花吟》兩個英文版本[J].齊齊哈爾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5):34-35.
[6]周陽.基于詩歌翻譯“三美論”的《葬花吟》兩英譯本評析.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17,(1):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