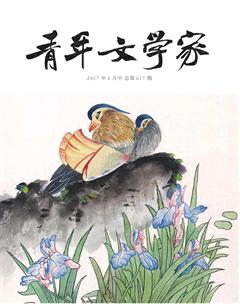巴黎中的漫游
摘 要:《地平線》是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玄學性色彩最強的一部小說。其中最典型的場景是主人公在巴黎大街小巷的“漫游”。時間和空間重合的漫游,是現實狀態,也是心理狀態。主人公漂浮不定的漫游正是作者透過巴黎的時間追憶,也源于童年記憶和二戰戰后氛圍的影響。《地平線》中的“漫游”的深層次含義也是一個隱喻,它是現代人精神世界和生存狀態的縮影,也代表了人在世界中的一種潛在和可能狀態,更是關于當代社會人類“自我失落”的孤獨寓言。
關鍵詞:《地平線》;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巴黎;漫游;時空隱喻
作者簡介:全文(1993-),女,漢族,湖北荊門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7--02
2014年,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折桂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了世界文壇中的一匹黑馬。《地平線》就是他后期風格轉向最有代表性的小說之一。正如徐和瑾在譯后記中所言:“《地平線》也許是莫迪亞諾的小說中玄學色彩最強的小說。”[1]本論文以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小說《地平線》中的巴黎背景為切入點,探究主人公現實和心理的時空漫游之旅,透過巴黎的時間追憶,追溯“漫游”狀態的根源,深入解讀“漫游”背后的隱喻。
一、巴黎的時空“漫游”
巴黎,是莫迪亞諾一系列小說中最主要的背景,是他最偏愛、最眷念和最執迷的地方。巴黎,在莫迪亞諾的記憶深處,是一座隱匿著危機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猶太父親為躲避法國法西斯警察的追捕,隱姓埋名,茍且偷生。戰后,幼小的莫迪亞諾仍能感受到那種特殊的氣氛。于是在他的小說中,巴黎成為一座盤根錯節的地理迷宮,連主人公的回憶都變得支離破碎、撲朔迷離。但在《地平線》中,隨著博斯曼斯的步伐,莫迪亞諾想象中的巴黎漸漸成為一個有序的空間。
首先,以星形廣場為中心,沿著輻射的街道開始漫游,尋覓每一個被遺落在角落中的往事回憶,如地鐵口、林蔭大道、旅館等。在《地平線》中,博斯曼斯最初的回憶便是從瑪格麗特居住的十六區開始的,之后又穿越了十四區和十二區,慢慢揭開了一系列迷霧般的人物命運。其次,在莫迪亞諾的筆下,巴黎是一個具有中心和邊緣之分的圓形結構。巴黎的中心是繁華和熱鬧,人來人往,卻無一處可供他們安身的地方;邊郊卻是一個沒有身份的漫游者躲避過去的佳處。瑪格麗特為了躲避潛在的危險,而不停地更換住所,終于在奧特伊的佩爾尚街十六區找到了一個偏遠卻安全的房間,博斯曼斯也愿意待在這所安靜的房間寫作。此外,還有法國和瑞士的對立。在《地平線》中,主人公認為,瑞士是一個安全的中立國家,沒有經歷劫難和痛苦,擁有陽光和寧靜生活的世外桃源,是一個理想的避難所,但并非如此,瑪格麗特從巴黎前往瑞士當家庭教師,卻仍在瑞士遇到了一直追趕她的布亞瓦爾,于是她重新回到了巴黎。
這個有序的自然空間,隱含在莫迪亞諾的小說深層,同時也是他內心精神世界的反映。隨著空間的變換,時間也在變更。三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后、四十年后,一個時間點就是一個故事的開始。時空重合,形成一道“時間走廊”,通往“地平線”。
生命就是不斷地追索過去和期待未來。與瑪格麗特的相戀讓博斯曼斯相信,他們依然可以成為幸福的擁有者,依然可以成為擺脫過去、前往“地平線”、開始新生活的自由人。他在內心深處明晰,“在懷疑時,至少還有一種希望,有一條逃逸線朝地平線逝去。我們心里在想,時間也許沒有完成它摧毀的工作,以后還會有見面的時候”[2]。在時間走廊里,雖然彼此已不在同一條時光走廊里,如同隔著魚缸玻璃,并行待著卻再無交集。但博斯曼斯相信,有朝一日,當他們再次迎面相遇時,他依然能一眼認出瑪格麗特,他將穿越時間走廊中那一道道看不見的界限,在同一條時間走廊中與瑪格麗特重新開始他們的愛情。
漫游終止的地方,就是“地平線”。它是天與地的盡頭,是一個真善美的新世界,是一個人人夢寐都想要抵達的世外桃源,通往一個未知的美好未來。抵達“地平線”,就能擺脫過去、克服遺忘、抓住幸福。這是一場時空之戰。在心理時空與現實時空的全息對應中,主人公內心深處的漫游狀態也不斷展現在我們眼前。
二、巴黎的心理“漫游”
巴黎漫游,是地理上的漫游,同時也是心理上的漫游。
巴黎,這座國際性的大都市,包容著各種各樣的人,卻又對這些來來往往的可憐人們不聞不問,她冷漠的懷抱中只殘留下了孤獨、匿名和遺忘。在巴黎,博斯曼斯和瑪格麗特就是漫游者、無根者、局外人。沒有父母、沒有國籍、沒有過去的他們,在漂浮的無根性、潛在的焦慮感和無形的隔閡感中漫游,卻又不斷向往著幸福的“地平線”。
這對戀人相依為命,卻也有著未曾告知對方的過去,彼此只是熟悉的“陌生人”。正如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所言:“哪怕在最密切的關系里,也很容易出現一種陌生的特色。”[3]因此在一定意義上,這種疏遠性和陌生感的特質是一般人類的共性,存在于任何關系中,這對戀人也只是熟悉的“陌生人”。他們是群體中的一種特殊元素,既近在眼前,卻又遙不可及;既在其中又在局外;既近又遠。他們只是群體之內的外來人、多余人、圈外人和無身份者。他們既不確定過去也無法看到未來;既身處社會群體之中又無法真正融入。“外來人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已經無家可歸、注定四處漂泊的現代人的生存樣式。”[4]
《地平線》中的主人公是典型的漫游者,具有漂浮的無根性特征。他們沒有在一個幸福的家庭中長大,成年之后也與他人有一種疏離感。他們都很不幸,一直在逃離著原來的生活。直到遇到彼此,惺惺相惜,他們才開始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為了抵抗漂浮和遺忘,博斯曼斯試圖從曾經殘留的記憶碎片中重溫過去的美好、尋回遺失的愛人。但是“他感到自己患有遺忘癥。他對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已忘得一干二凈”。[5]失去過去,他與瑪格麗特的相遇也變成了模糊的記憶,是否一切都注定要被遺忘?曾經的美好也遺忘在了記憶里,曾經的愛情也埋進了塵埃中,一切都隨時間而被淡忘。“現實事物總是破碎的不完整的。有時候人們遇到一個人,之后就再也見不到他了。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忘卻了某些東西。人們對自己說謊。這一切形成了一大堆支離破碎的東西。”[6]現實中的生活往往充滿了不確定的印記,毫無根基的狀態又讓博斯曼斯陷入了迷茫,他感覺生活處處充滿了壓抑感。
博斯曼斯依然是一個潛在的漫游者,城市中的“陌生人”,只能孤獨地漂浮在這座繁忙的都市中,只能在一股茫然若失的感覺中焦慮不安,卻找不到屬于自己的立足之地,無法找到生活的根基點。時空中和內心的漫游成了博斯曼斯生活的方式。從巴黎的一個街區走向另一個街區,他在遺忘的角落中尋找缺失的身份、對抗生命的孤獨、抵御遺忘記憶。
三、時空“漫游”隱喻
二戰結束之后的西方世界社會安定。巴黎作為文化時尚之都,也迅速從戰爭中恢復過來。物質文明快速發展,人們享受著戰后的富足與太平盛世。但一種對生命、過去和未來無法把握的無根性和空虛感仍然深深隱藏在人們的內心深處,人的精神世界潛伏著深深的危機。人的行動、思想和生活都面臨著解構,人在這個現代社會中早已失去了自我,只是一張紙(身份證)、一個符號、一個都市漫游者。
同時,西方社會青年人的生存狀況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沒有自主性,在無依無靠中隨波逐流,惶惶不可終日,面臨著進退兩難的生存困境,卻又無能為力,只能不斷地逃離困窘局面。莫迪亞諾的小說便著重關注這些飄忽不定的猶太青年人。面對人類命運中這一悲劇性的生存狀況,莫迪亞諾時常會引領我們探求人物謎一樣的過去,在消逝的時光中尋找迷失的身份和自我,揭露出人類生存的荒誕與悲哀。他曾說過:“我力圖寫出一個沒落的世界,而法國被德國占領時期正提供了這樣一種氣氛,但是實際上,我所表現的卻是今天世界的一個極度擴大化了的形象。”[7]莫迪亞諾的《地平線》只是這個沒落世界的冰山一角,他筆下人物的存在狀態也只是現代人生活的部分縮影,但卻折射出我們這個時代人所處的生活狀態的無奈與荒誕性。
《地平線》中的“漫游”狀態就是現代人精神世界和生存狀態的縮影。孤單、恐懼、生活的荒誕,這就是現代人生存的悲哀。在莫迪亞諾看來,我們的悲劇也在于命運的不確定性和荒誕性。人被周圍的環境所壓迫和異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有著深刻的隔閡,人甚至無法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運。這個世界變得混亂和反常,這個時代變得不可理喻和荒誕不經,人也變得越來越渺小和卑微。荒誕才是生存的現實。莫迪亞諾反抗荒誕的策略就是揭下歷史虛偽的面具,從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揭示人類生存的真實狀態。
“漫游”的狀態也是關于當代社會人類“自我失落”的孤獨寓言。正如莫迪亞諾所言:“我飄飄無所似,不過幽幽一身影。”[8]人類生存的本質便是孤獨。在《地平線》中,作者所描寫的兩個青年戀人的境遇就是在描述關于21世紀人類的生存寓言。最后,作者筆下的“漫游者”已經經歷了人生的磨難和洗禮,不再渾渾噩噩地讓短暫的人生從虛無和荒誕中走過,而是執著地尋找生命的美好時光,走向幸福的“地平線”。
參考文獻:
[1]徐和瑾:《<地平線>譯后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頁。
[2](法)莫迪亞諾:《地平線》,徐和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頁。
[3](德)齊美爾(Simmel ,G):《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林榮遠編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頁。
[4]陳伯清:《格奧爾格·齊美爾:現代性診斷》,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
[5](法)莫迪亞諾:《地平線》,徐和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頁。
[6](法)洛朗斯·利邦:《莫迪亞諾訪談錄》,李照女譯,載《當代外國文學》,2004年第4期,第163頁。
[7]小禾:《“神秘的年輕人”——法國當代作家莫迪亞諾》, 載《讀書》,1986年第2期,第111頁。
[8](法)莫迪亞諾:《尋我記·魔圈》,李玉民等譯,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