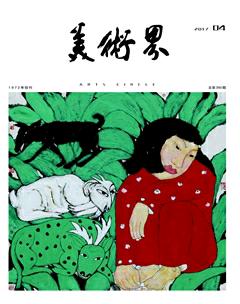無用的標(biāo)準(zhǔn)

我覺得中國畫最突出特點(diǎn)是其氣質(zhì),這種氣質(zhì)區(qū)別于西方的藝術(shù),也正是因?yàn)槲覀兊奈幕邆涞莫?dú)特氣質(zhì)導(dǎo)致我們成了西方眼中的補(bǔ)充部分,也常被看做一種異域風(fēng)情。當(dāng)然,我相信這種差異與作品本身并無太大關(guān)系,和某種經(jīng)濟(jì)政治的關(guān)聯(lián)更密切。再把視線再移回繪畫本身,在審美中國畫的時候,人們常常會根據(jù)藝術(shù)語言的不同報以兩種不同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事實(shí)上,很多好的作品遠(yuǎn)不是這兩個簡單的標(biāo)準(zhǔn)所能闡釋的。一個是某種意義上的傳統(tǒng)眼光,主要以“六法”為基礎(chǔ),從作品的格調(diào),用筆的高度,山水畫中的各種基礎(chǔ)技法的熟練程度,人物畫中的基礎(chǔ)造型能力,畫面的形式把控能力等;二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當(dāng)代眼光,比如說其風(fēng)格形式的獨(dú)特性,主要從感覺出發(fā)。但只有這兩種視角的話難免會簡單理解了一些作品,一開始就給觀看樹立了框架,利用了一種二元對立的分類法。其實(shí)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恩格斯的“合力論”,就是綜合因素和結(jié)果的關(guān)系。其實(shí)我覺得中國畫所追求的極致是微妙、散淡,那么對作品的欣賞和批評也不應(yīng)泛泛而談,粗糙一視,要更深入地體會其語言的魅力。一筆兩筆不嫌少,千筆萬筆不嫌多;規(guī)矩處見活潑,生動處見力度,磅礴處見嚴(yán)謹(jǐn);寧拙毋巧,寧厚毋薄,寧重毋輕,寧大毋小,寧遲毋速;用筆用墨中也應(yīng)有“生”味,要在熟中求生,以免“滑,飄,輕,油”的問題,而初學(xué)則有嫩氣,久久則蒼老,蒼老太過,則入霸悍,必須由蒼老漸入于嫩,似不能畫者,卻處處到家,斯為上品,寧有稚氣,毋涉市氣,寧有霸氣,毋涉野氣;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也要去看一幅畫的“筆性”,天分第一,多見次之,多寫又次之,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俗塵,二要學(xué)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養(yǎng)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如燕居靜坐,讀書品茗,養(yǎng)生調(diào)息,以使精光內(nèi)斂,待使用之時神采飛揚(yáng),精光四射;以筆墨運(yùn)氣力,以氣力驅(qū)筆墨,以筆墨生精彩;在學(xué)習(xí)傳統(tǒng)的時候,要善學(xué)古人之長,毋染古人之短,方漸入佳境;再看古今作品,骨骼氣勢,理路精神皆在筆端而出,唯靜穆,風(fēng)韻,潤澤,名貴為難,等等這些詞匯都是從其筆墨層面,也可以說是藝術(shù)語言方面的一些分析。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一再強(qiáng)調(diào)“筆墨當(dāng)隨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丟棄傳統(tǒng)。我聽說一些人“反傳統(tǒng)”,主要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水墨在歷史上已經(jīng)達(dá)到了無法逾越的高峰,所以這條路繼續(xù)走沒什么必要,也走不太通了。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藝術(shù)的高峰沒有唯一性。就好像唐宋的山水畫已經(jīng)達(dá)到了高峰,但元明清仍然各有精彩,到了清朝還出現(xiàn)了石濤、八大山人這樣的著名畫家。我們再回頭看黃賓虹的畫,他的筆墨功夫又和石濤、八大山人有很大不同,說明傳統(tǒng)筆墨一直在隨時代發(fā)生變化,但“變化”并不意味著一切要推翻重來,或者說我們不能因?yàn)闅v史上有高峰的存在,就否定了繼續(xù)朝前走的意義。中國傳統(tǒng)的水墨意境,背后有一整套儒、釋、道的哲學(xué)觀念作支撐——所謂的“自然詩學(xué)”。它跟城市文化、科技的關(guān)系,是一個關(guān)于自然的現(xiàn)代性課題。一百多年來,現(xiàn)代水墨一直在走形式主義的技術(shù)突破的路線,要么是把油畫的寫實(shí)主義引入國畫,要么是吸收西方抽象藝術(shù)的成分。前者其實(shí)已經(jīng)背離了水墨精神,而后者的實(shí)驗(yàn)空間也已被探索殆盡。


交融是當(dāng)下國際藝術(shù)發(fā)展的趨勢,中國畫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交融,科技與藝術(shù)的交融;還有各種形式上的跨界,把媒介混合。舉個例子,劉小東剛從美院畢業(yè)時到現(xiàn)在的藝術(shù)家的轉(zhuǎn)變之點(diǎn)就在交融,他脫離了油畫媒材進(jìn)入藝術(shù),和團(tuán)隊的運(yùn)作導(dǎo)致他的作品不僅僅只是最后所完成的那一幅畫。還有一些藝術(shù)活動也體現(xiàn)了這一種趨勢,如譚盾的《有機(jī)音樂》《撕紙為樂》;蔡國強(qiáng)的《我想要相信》《九級浪》;等等。在當(dāng)代,表達(dá)水墨精神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徐冰的《天書》,它以一種非常超前的方式,將中國的文化內(nèi)涵、水墨精神傳達(dá)得淋漓盡致。這樣的一種趨勢正在從各個方面打破各種各樣的框架局限,加大了很多可能性,但是在七八十年代以前的很多藝術(shù)家往往所表達(dá)的是一種集體經(jīng)驗(yàn);這時中國當(dāng)代水墨是在反思“文革”、社會的現(xiàn)代化變革,以及西方文化的沖擊下發(fā)展起來的。雖然這些因素并沒有對當(dāng)代水墨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但作為一股合力,共同營建了當(dāng)代水墨發(fā)展之初的社會與文化語境。事實(shí)上,80年代的水墨變革從一開始就不單純是一個藝術(shù)形態(tài)問題,而是一個涉及社會學(xué)、文化學(xué),甚至是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之所以反叛與顛覆會成為那個時期的基本文化特征,其核心之處還在于藝術(shù)家對文化、主體性、藝術(shù)的功能與意義等問題有了新的認(rèn)識。而到了“85后”,很多藝術(shù)家把眼光從遠(yuǎn)方拉回來,回到自己過去的影子,堅持保留個人意見,假設(shè)和想法,遠(yuǎn)距離地審視過去的學(xué)術(shù)成果,以另一角度看待現(xiàn)實(shí)課題,不輕信盲從。90年代以來,現(xiàn)代水墨繪畫來勢洶涌,其特點(diǎn)除強(qiáng)調(diào)筆墨結(jié)構(gòu),符號形態(tài)和繪畫程式以外,還更多關(guān)注了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作品反映的個人精神和體驗(yàn),對于欣賞作品的人而言,強(qiáng)烈的視覺沖擊,顛覆性的筆墨形態(tài),夸張的語言結(jié)構(gòu),或激進(jìn)或尖銳的繪畫精神理念,都使得現(xiàn)代水墨繪畫面臨著中國畫不能全盤視覺化的問題。隨著主體意識的覺醒與增強(qiáng),隨著現(xiàn)代社會文化批判對自身的反思,水墨繪畫的創(chuàng)作由陳述帶有強(qiáng)烈政治色彩的“集體意識”轉(zhuǎn)變?yōu)樽髡咦陨韺ι?jīng)驗(yàn)的個性表達(dá),同時繼承傳統(tǒng)文人繪畫重內(nèi)心情感表述的特點(diǎn)。但是,與傳統(tǒng)文人畫遁世逍遙、潔身自好的心靈獨(dú)白不同的是,當(dāng)代水墨畫創(chuàng)作則是建立在對現(xiàn)實(shí)弱勢群體的關(guān)懷,對世俗的不公現(xiàn)象的鄙棄,所有的情感的宣泄都來源于作者對現(xiàn)行社會種種現(xiàn)象的切身體會和深刻思考。由此而產(chǎn)生的對當(dāng)代社會文化的詰問、質(zhì)疑和批判,成為了當(dāng)代水墨在審美藝術(shù)功能上的激進(jìn)品質(zhì)。
那么我認(rèn)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好的中國畫作品,同樣是優(yōu)秀的當(dāng)代水墨作品,優(yōu)秀的當(dāng)代藝術(shù)作品,優(yōu)秀的行為藝術(shù)作品,這種古老的媒介同樣具有先鋒性,這種不浮于表面的形式,暗流洶涌。其實(shí)由于中西方哲學(xué)體系的不同,中國畫和所謂的西方架上藝術(shù)、西方當(dāng)代藝術(shù)又有著核心上的不同,我更欣賞藝術(shù)作為一個無意義、無批判、無題材,同樣也可以是毫無意思的東西,我也不認(rèn)為藝術(shù)要什么創(chuàng)造性,要讀這個書那個書,文字、藝術(shù)就是一個人真正本自具足的。中國畫也是這樣,無中生有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吧。
夏溢
1991年生于九江。
2013年畢業(yè)于北京服裝學(xué)院。
2014年結(jié)業(yè)于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國畫造型創(chuàng)作班。
2014年至今于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中國畫學(xué)院攻讀碩士學(xué)位,導(dǎo)師李洋教授。江西省美術(shù)家協(xié)會綜合材料繪畫藝術(shù)委員會委員。
九江畫院特聘畫家。
作品多次入選全國性美術(shù)展覽并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