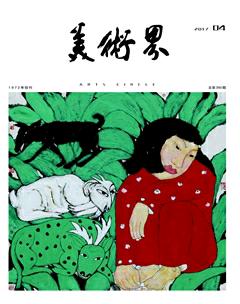構建“似曾相識”的圖式
張曉東

就藝術創作而言,主體的表達欲是創作的首要火種,如果缺失了這種基本的創作沖動,其所固有的學識、素養、技法都將流于形式,黯然失色。于我而言,之所以如此固執地選擇“花卉”這一題材,主要還是因為在廣州生活學習多年的緣故。
廣州被譽為花城,一年四季,無論是大街小巷,還是江畔湖邊,都是一派岸芷汀蘭、鮮花常開的景象。無疑,這是一劑清新劑,讓身處擾攘塵世,與各色人群頻繁交往的我們得到了些許安寧。把這種感受清晰地浸潤到作品中是我一直所渴求的愿望,正是這種欲望迫使我時時懷有表達的沖動,于是花卉這一主題成了我無怨無悔的選擇。沉舟側畔,千帆過盡,十幾載一晃而過,我的創作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蟬蛹似的蛻變。
時至今日,創作形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讀研伊始之際為創作早期階段,如《暖春》《好日子》等作品,側重表現花卉本身的肌理與形態之美,沒有太多的立意與想法,所謂的觀念也只是一個牽強的詞匯。研究生畢業創作可謂是我藝術成長的第二階段,也是相當重要的階段,因為正是這個階段奠定了我創作的基本取向。花卉依然是我堅守的主題,但這一階段的我所追求的不是再現花卉的美而是表現花卉的魂,尋找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于是,我更多地把對生活、歷史、人文的理解貫穿到作品中,想藉此表達對當下現實中一些問題的個人真切體悟,它既不是現今流行的小資情緒或語言游戲,也不是空有姿態而不得要領的社會、文化評判。當然僅有創作沖動與社會認知、文化觀念,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對藝術家而言,語言才是立身之本。所以,在創作中我首先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是繪畫的語言問題。因此我更加注重藝術語言的錘煉,人文關懷的表達與趣味的追求,用獨特的綜合版畫的藝術語言,將自然中的花卉轉化為充滿詩意的意象。如《花魂》系列,這組創作從畫稿時我就有意識地“逃離”花卉的自然形態,著意將內心的花卉與自然界的花卉形式拉開距離,并置于兩個不同的層面,“試圖”有著精神意義的拔高與跨越。繁密、錯雜甚至有些凌亂的線條反復而又隨意地穿插于古舊泛黃的頭像照片之中,組織成繁花之形,似是而非,難以分辨,放棄了花卉的規律性與純潔性。這就是我當時的感受,也是我想要的。其中《黃花崗·花魂》以具有嶺南特色的植物作為創作元素,把芭蕉葉、三角梅和木棉花等植物的花瓣打散后重新組構形成花環狀,以此來喻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在廣州。而花叢中直接繪刻英烈們的頭像則強化了主題,畫面主體部分采取圓弧形的構圖,似花環又似圓形的墳冢,既希望先烈們能魂歸故里、魄有所依,又表達了對英雄們的沉痛緬懷。在這一過程中,導師李全民的藝術觀及其藝術修養,無疑對我的這一轉變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人的心理活動是繪畫的母體,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藝術的創造從造成形式的沖動和感情表現的熱望中躍起來。藝術的目的是要表示事物內部的意義,因為這一點才是他們的實在。”到深圳大學任教后,正是如畫的校園環境,學生的活力以及他們新潮的觀念煥發出了我的創作靈感,心靈深處又有了些許變化,于是除了表達主觀的意象之外,我想賦予更多畫面背后的思索,在花卉這一唯美的主題下,最終呈現的卻是現實的無奈。通過豐富的肌理、現代的構成、抽象的符號,營造一種表面的和諧,其實從畫面中依稀可以聽到花卉沉重的嘆息,讓人心潮隨之起伏,既想撲入,又欲逃離,正如這個浮躁的現實帶給人們的誘惑。花卉主題依舊,但已然醉翁之意。與研究生畢業創作相比,不難看出,那時的作品雖然打破了花卉的自然生長形態,但還是以花卉的形象為依據,局限在花“形”的限域內,而在近幾年的作品中,形象已退居次要地位,花“形”已隱遁于抽象的符號之中,它們已不再是自然界中的花卉,而是心靈的花卉。我如此堅定地選取花卉這個題材來呈現現實,并非宣泄對當前浮躁的不滿和抨擊,因為我真心地愛著這樣的生活,執著地相信浮躁的背后孕育著更大的能量與希望。我只是更愿意聆聽并表達真實的生活,那純然的、不加修飾的自然魅力。因此在《有一天》系列中,雖然表現的還是花卉,但選擇花卉的用心一目了然。我希望選擇當下最普通常見的花卉做為心理和意識的噴發點,以求凝練地把握當下社會的種種現象,發揮綜合版畫語言的本體優勢,力求在畫面中通過看似簡單的造型手段來把花卉解構,與時代符號重組,將輪郭線刻意簡化,甚至無法清晰辨識,但攜帶特意情緒的豐富多樣的肌理材料來傳達種種難以言傳的意味,以材料的獨特的具象痕跡與抽象造型交相輝映,構成新的意境,賦予新的內涵,諸多因素的結合,讓畫面形成一種特有的氣勢和沖擊力,與觀眾共鳴:此花非彼花,似曾相識。



從單純地忠實記錄到自由意向的表現,我通過用線的穿插,用幾何形的組合,用肌理的變化,不拘泥于真實的花卉風貌,來追求一種主觀抽象的意境。借助于花卉的表現來反思當代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誠然,這種反思不是邏輯的推演,不是哲學的抽象玄思,而是在以一種個人化的歷史觀、現代的責任感對花卉進行了重新組合和重新解讀。通過各種肌理的鋪陳、組合來表達心中的意念,原本具象的花卉變得愈發模糊和抽象起來,而幾何形、現代符號、肌理越來越成為畫面中主要的視覺語言元素。
其實,只為了讓自己的藝術有一個更加寬廣的視野,實現“花卉”的符號在我的藝術生命源泉中隨處流淌。當然,真正的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讓觀者與我一起體會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1975年出生于湖南省溆浦縣,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版畫系,獲文學碩士學位。深圳大學師范學院美術系教師,美術系副主任,廣州畫院特聘畫家。《六祖慧能》入選由中國文化部、財政部、中國文聯聯合主辦的“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
作品被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奧林匹克藝術中心、中國版畫博物館、上海世博會藝術中心、廣東省美術館、黑龍江省美術館、深圳觀瀾美術館、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莞城美術館、廣東省科技館、湛江市博物館、深圳美術館等機構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