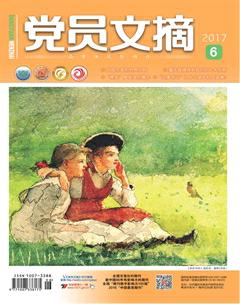周恩來:不能容忍親屬搞特殊化
余瑋
周恩來是國務院總理,管理著一個“大家”,他始終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勤務員。在自己的家里,雖然他沒有孩子,但其胞弟周恩壽的孩子周秉德、周秉鈞和周秉宜因家中房小住不開,曾跟著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生活了十幾年。周恩壽的其他幾個年紀較小的孩子,周秉華、周秉和、周秉建也曾在西花廳見證過許多親情往事。作為與周恩來夫婦關系最為密切的晚輩,周家的第二代人都認為伯父給他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不能容忍親屬搞特殊化。
要求后輩
始終把自己看作普通人
“什么時候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能上北戴河避暑了,你們才可以去”
周秉宜來到北京時才5歲。她回憶:“伯伯關心我們的成長和進步,他是我們這個家的大家長。當然他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又是非常的與眾不同,自有他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老共產主義戰士的角度和方式方法。”
當年,中央領導人并沒有什么更多的特殊待遇,無非是周末中南海的禮堂放映一場電影,或者首長們暑假期間去北戴河開會時可以把家屬子女順便也帶去避暑等。然而,“伯父堅持不允許我們沾邊,堅持我們和老百姓的生活保持一致,他從不允許我們去看電影。至于暑假去北戴河,七媽(鄧穎超)曾對我們說,‘你伯伯說了,什么時候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能上北戴河避暑了,你們才可以去。”
在周秉德的回憶里,“在生活上,伯伯對我們一家,都要求極為嚴格,而生活上的關照又極為深切”,“伯伯對我父親周恩壽工作的安排,一開始就指示父親的領導說:‘給他的工作安排,職務要盡量低、薪水要盡量少。他說因為他是國務院總理,對自己的弟弟就應嚴格對待。我全家來到北京安家是在東城區遂安伯胡同的兩間小屋,而我們兄弟姐妹六人根本住不下,伯伯就讓我們已經上了學的三個大孩子住到他的家——中南海里的西花廳,而在西花廳,我們也是三個孩子住一間屋里。我們父母的收入很低,孩子多,經濟上有困難,伯伯就用自己的工資來補助我們。直到伯伯、七媽去世后,從他們衛士的回憶中,我才知道,他們對我們家的經濟補助占到了伯伯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占了二分之一!其實,伯伯在世時,我看他著裝總是整潔、筆挺,哪知他的內衣、睡衣是補了又補啊!作為紀念,我分到了這樣的衣服,我拿在手里,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
由于長期的艱苦斗爭和緊張工作,1952年夏天,鄧穎超生病了,身體十分虛弱,住在頤和園聽鸝館后面的一個院落里養病。周秉德記得:“伯伯帶我們去頤和園看七媽時,在園內走路,常與老百姓擦肩而過。那時人少,遠處的游人看到,認出了就招招手,近處的就跑過來握握手、說說話,非常自然,非常親切。”
周秉德等跟在周恩來身后走進頤和園,進門前周恩來總不忘提醒工作人員:一定要買門票。
在周恩來的教誨和影響下,周家后人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么特別,始終把自己看作普通人。
要為工農服務
“我支持你去農村插隊落戶,做一個農民”,“你敢向我保證嗎?”
1965年夏,周秉宜即將從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畢業,準備報考大學。她想到應該去向伯父請教,相信他一定會給自己一個最好的指導。
“伯伯,我們畢業馬上就要報志愿了。這次我們附中同學可以報考的大學有浙江美院、戲劇學院舞美系和工藝美院,我決定報考工藝美院,可我還是想聽聽您的意見。”
周恩來聽后隨之問起工藝美術學院有哪些專業。周秉宜說,有染織、陶瓷、建筑室內裝飾,還有工業設計。周恩來沒有直接表態,而是認真地對她說:“工藝美院學的這些專業,都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系,都可以直接為工農兵服務。現在我們國家的出口商品包裝設計粗糙,在國際市場上我們的商品價格就是上不去,影響了我們國家的換匯率,我們還需要在包裝設計上下很大功夫才行。”一聽,周秉宜心里有了底,就不再多問什么,只點點頭“嗯”了一聲。
幾天以后,浙江美術學院先于工藝美院來到附中進行招生考試,幾乎座無虛席。只有周秉宜獨自一人留在空蕩蕩的宿舍里埋頭看書,因為她的高考報名表上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染織系。
1965年“五一”節,周秉華去西花廳看望伯伯。周恩來得知周秉華即將高中畢業,馬上問他畢業后有什么打算。周秉華說準備和班上幾個同學一起去山西插隊落戶。周恩來對這個回答顯然很滿意,他說:“我支持你去農村插隊落戶,做一個農民。”不過周恩來似乎還有一點兒不放心,又追問了一句,“你敢向我保證嗎?”周秉華說:“當然敢,我保證畢業以后去農村。”
周秉華滿懷信心地開始進行去農村插隊的準備,卻不料隨后的一次全市征兵任務把他的計劃打亂了。當時,凡應屆初、高中畢業生,都得先去參加體檢。周秉華從小在八一學校練出來的那副好身板一下子就被西城區武裝部相中了,不多久,一份入伍通知書就直接寄來了,于是周秉華去向伯伯、七媽告別。周恩來第一句話就問:“秉華,原來你跟我說要去插隊當農民,我是很支持你的。現在又要去入伍,這個情況是怎么回事?”
周秉華把畢業生去向的原則簡單介紹了一下,周恩來聽后想了一下,說:“我知道了。既然組織有這么個要求,你還是要服從組織分配。不過,你想當農民,將來從部隊復員以后還可以去農村,實現你的理想。”
如今,周秉華回憶起這件事情時說,他感覺伯伯對他沒有能去成農村,很有點不甘心的意思,他特別能理解伯伯對六妹秉建去內蒙古插隊為什么寄予了那么大的希望。
一切都要符合政策規定
“你這次上大學在家庭出身上雖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沒有走什么門路呢?”
1969年初,周秉和作為北京知青到陜北延安農村插隊落戶,當時剛過17歲。
插隊的第二年,新疆軍區到陜北招兵,周秉和所在的棗園村只有他是唯一體檢合格的人,于是他滿懷豪情身著軍裝踏上了新的征程。
到了新疆南疆軍分區目的地,周秉和趕忙給伯伯、七媽寫信匯報:“我參軍了,我將在解放軍這座革命大熔爐里煉顆紅心,為保衛祖國站好崗放好哨……”由于郵程遠和其他原因,周秉和收到七媽的回信時已離三個月新兵連訓練結束期不遠了。
這是一封猶如巨雷轟頂的回信,鄧穎超在信中說:“秉和,接到你的來信得知你已經參加解放軍,我們當然很高興,但是你伯伯專門查閱了國家征兵的有關政策,按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審查的子女,不可參軍。你父親現正接受審查(注:周秉和的父親周恩壽受“四人幫”迫害從1968年到1975年被關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況屬于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違反了政策就應改正。你伯伯已經向送你參軍的陜西省和軍區領導交代了,讓他們派人去接你,還與新疆軍區領導聯系了,讓他們放你回,你要做好思想準備,脫去軍裝復員,繼續回陜北插隊當農民……
周秉和說,伯伯、七媽肯定知道他剛剛當了三個月的兵,又送回農村插隊對他是多么大的打擊,“所以七媽說:秉和,你要堅強,想開些,還有那么多的知青不是都在農村當農民嗎,對你的困難伯伯和我仍會繼續幫助解決,但違反政策的事一定要改正,這是我和你伯伯對你最起碼的要求……”
由于剛剛從環境比較優越的部隊回到條件艱苦的陜北農村,伙食相差很遠,農活消耗體力很大,周秉和的身體一時適應不了這些巨大變化,加上心情不順,剛剛下農田干了三天的農活兒就病倒了。
在醫院治療期間,周秉和給伯伯和七媽寫信匯報了自己的情況,七媽親自給他回信:“伯伯和我覺得能有你這樣的侄兒和小六侄女而非常高興!不知你是否病好?病后身體怎樣?我們都在惦著。希望你接信后先來一信告知,以慰我念……”周秉和手捧這封信,淚流滿面。
1972年,全國范圍開始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周秉和聽說招生政策里有規定“可教育好的子女”(即父母正接受審查,或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現較好的孩子)也允許上大學。經過報名申請、貧下中農推薦、領導批準,周秉和于當年4月進入清華大學,學習自動化專業。
5月的一個星期天,周秉和時隔三年又在西花廳見到了日夜思念的伯伯和七媽。伯伯顯得更老了、更瘦了,但眼睛還是那么有神。周恩來問:“秉和,你這次上大學在家庭出身上雖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沒有走什么門路呢?”聽到周秉和說是貧下中農推薦、招生單位審核批準、正規錄取上的大學沒有走門路的回答后,周恩來放心地笑了。
(呂麗妮薦自《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