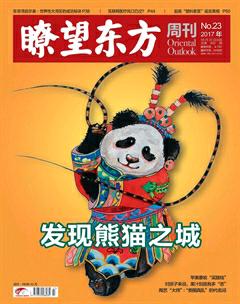新雅安的生態經
金風++單素敏
“農旅結合”的發展思路,讓重建后的新雅安充分發揮了自己最突出的生態優勢
沿著兩公里長的曲折山路盤旋而上,行至海拔1300多米的半山腰,一片有著傳統川西建筑風格的特色民居赫然入目。這就是四川省雅安市寶興縣穆坪鎮雪山村。
村民李勇的家就是其中的2號房。
他所在的雪山村新江組共有38棟青瓦黃墻的4層小樓,全部依山勢分排而建,錯落有致。遠望過去,像群山環繞中凌空懸掛的“世外桃源”。誰又能想到,這里在3年多以前還是一片廢墟。
李勇曾親歷2013年“4·20”蘆山地震,而今,他不僅住進了政府統一規劃、村民自建的新房,還把自己建造的民宿出租給村里的合作社,留在家鄉做起了旅游接待生意。
在震后的斷瓦殘垣上重獲新生的雪山村村民有264人。
從“地薄桑麻瘦,村貧屋舍低”的窮鄉僻壤轉變為游客盈門的民宿,雪山村這樣的村子,僅在寶興縣就有19個。
“生態優勢是雅安最突出的優勢,要圍繞這個優勢大力發展生態文化旅游產業,把這一特色產業做大做強。”正是秉持這樣的發展思路,雅安義無反顧地進行著積極探索。

俯瞰四川省雅安市寶興縣雪山村
在災后重建的過程中,雅安立足全市旅游資源,以“推動資源變資本、生態變業態,促進旅游與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發展,加速讓生態資源向旅游經濟轉變”為基本思路,推動區域資源有機整合、社會共建共享。
“這樣的發展理念和模式讓雅安有了面目一新的改變。”四川省副省長、雅安市委書記葉壯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
單靠“老天爺”和前人賜予是不夠的
作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貓的科學發現地、命名地和模式標本產地,以及最早有人工栽培茶樹的地區(在蒙頂山上種茶的雅安人吳理真被認為是有明確文字記載最早的種茶人),雅安的“熊貓家源,世界茶源”是其最為外界熟知,也最具國際吸引力的兩大名片。
“除此之外,雅安還是自然、人文資源的寶庫。”雅安市旅游發展委員會主任曹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雅安地處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過渡帶,海拔垂直高差5000余米,旅游資源極為豐富,目前雅安境內擁有國家4A級旅游景區18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個、國家森林公園3個;而碧峰峽、蒙頂山創建國家5A級旅游景區工作也在積極推進中。
此外,東靠成都、西連甘孜、南界涼山、北接阿壩的雅安還是名副其實的“川西咽喉,西藏門戶,民族走廊”,城市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全市有省級歷史文化名城和名鎮 5 個,有國家級、省級、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處。
以牛背山、二郎山、青衣江、喇叭河等為代表的壯美大山秀水;歷史悠久的茶馬文化、少數民族風情;雨城區的碧峰峽、中國藏茶村、上里古鎮,蘆山的烏木根雕,滎經縣的黑砂,寶興的漢白玉,漢源的水果、蔬菜、中藥材等景區、工藝產業和特色農業,共同構成了雅安獨特的旅游、康養、休閑資源。
去名山采春茶,在山高林密、溪谷縱橫的碧峰峽風景區避暑,到大熊貓基地觀賞國寶吃竹子,去“花海果鄉”漢源品嘗紅透了的大櫻桃,或是盤旋兩公里山路入住峭壁上的雪山村民宿,看窗外云霧繚繞、山巒壯闊、山下的寶興河奔騰不息——雅安對游客來說有著豐富多彩的選擇可能。
“在大眾旅游興起的時代,生態人文資源條件得天獨厚的雅安迎來了絕好的發展時機。但我們很清楚,要持續地吸引游客,單靠‘老天爺和前人賜予的先天資源稟賦還遠遠不夠。”雅安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徐一心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雅安要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既要充分發揮已有優勢,結合本地特色挖掘產業發展潛力,更要繼續在基礎設施、服務提升等方面做好配套。”
賣鮮茶葉的“天花板”怎么破
雅安市名山區是全國區縣范圍內茶園種植面積排名第二、人均種茶面積和綠茶產量全國第一的產茶區。但在過去很長時間,這里的茶農主要靠賣最初級的鮮茶葉為生,產品附加值低,鮮葉價格下跌時,收入只能隨之縮水。
災后重建過程中,名山區開始了產業轉型升級之路。
“如果還是像原來一樣僅僅圍繞茶葉種植、銷售本身做文章,一眼就能看到‘天花板,茶園面積、茶葉產量增加很困難。而在茶葉品牌格局幾乎已經確定的情況下,我們要是光沿著老路走,就很難再有所突破。”雅安市委常委、名山區委書記吳宏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2013年之后,名山區依托豐富的茶業資源和淺丘地貌型茶園的獨特旅游景觀優勢,一改往日以種茶、賣鮮葉為主的傳統產業模式,探索出了“茶+旅游”“茶+科技”“茶+互聯網”的特色發展路徑。
依靠“1+6+N”的空間發展布局,名山區實現了“茶區變景區、茶園變公園、勞動變運動、產品變商品、茶山變金山”的轉變。
“這樣的輻射帶動了走廊沿線12個鄉鎮近15萬群眾共同致富。”吳宏說。
僅茶旅融合這一塊,2017年前4個月全區接待游客達140.5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實現12.05億元,同比分別增長了61%和71%。
“從群眾的收入結構來看,2016年旅游方面的收入占到了五成;而在2012年,這一比例僅為一成,90%的收入還是來源于鮮茶葉。”吳宏告訴本刊記者。
類似的轉變還發生在雅安的其他區縣。
震前,距離名山區直線距離20公里的蘆山縣龍門鄉的多數老百姓,主要靠種植水稻、油菜等傳統農作物或家庭養殖為生,生活并不富裕。
而今,龍門鄉建成了白伙、王伙、河心等7個特色新村,打造出一條22公里旅游環線相串連的4A級龍門古鎮鄉村旅游線,沿線村民則把客房出租給新龍門客棧等民宿、酒店經營者,每年不僅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和可觀的利潤分紅,自己還可以通過給民宿提供服務再賺一份錢。
上世紀90年代之后力推產業結構調整的漢源縣,如今已經從一個無法大規模種植農作物的盆周山區,轉變為名副其實的“花海果鄉”。時值6月,甜櫻桃、紅富士蘋果正是紅遍滿山遍野的季節,不過它的“豐收”季遠不止于新鮮果蔬的上市期。
漢源縣以“農業景觀化、景觀生態化、生態效益化”為引領,打造從河谷、山腰到山頂梯次展現的農田景觀,將鄉村、自然、歷史、田園、家園的“畫卷”融入新村和產業,一年四季可以觀賞“一步一景、一天一景、一片一景”。
“我們的目的是讓游客既能‘飽口福、又能‘飽眼福,還可以‘享清福。”漢源縣縣長鄭朝彬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3個月旅游業分紅是種地年收入的10倍
力推鄉村旅游、生態產業發展,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
2015年9月21日,雪山新村民宿正式開始運營。截至當年底,3個多月時間村里每戶人家就分到了幾千元,幾乎是原來一年種地收入的10倍。
“2016年全年我自己分了2萬元,今年肯定會超過3萬元。”李勇對《瞭望東方周刊》介紹,村民從民宿里獲得的收入由房租、房費分成和合作社收入結余的年底分紅三部分組成,在合作社打工的12個人除此之外還能拿到每月1000元~1800元不等的工資,而其余留在家鄉就業的鄉親要么開了超市、餐館,要么種地之余,在自家農地里運營游客采摘、體驗的項目。
2013年之前,名山區萬古鄉紅草村村民劉林還只是一個普通茶農,如今他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家茶樓的老板。
“靠給游客提供住宿、品茶、采茶體驗等服務,每年能比原來增加三四萬元的收入。”劉林對《瞭望東方周刊》透露。
“其實剛開始我們搞茶旅融合,很多人包括本地老百姓都會擔心游客不足,但現在我們最應該擔心的是接待能力不足。”吳宏告訴本刊記者,“一到節假日,僅成都和重慶來的游客就已經把所有的停車場、酒店全部擠滿了。”
而2017年“五一”小長假期間,劉林家的茶樓僅出租騎游的自行車一項,一天的收入就超過了1000元;而賣小吃的鄰居,光是土豆串一天就賣了4000串。
“農旅結合”的發展路徑在增加百姓收入的同時,還對引導農民返鄉就業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解決了農村“空心化”的問題。
“以前老百姓種花椒、玉米的年收入不足1000元,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產業結構調整之后,外出的人紛紛回來,因為他們看到了家鄉發展的新機遇。”鄭朝彬告訴本刊記者。
而今,依托總面積達66萬畝的十大特色產業基地,漢源縣建成了116公里的“百里果蔬走廊”精品鄉村旅游環線,現在農民僅賣水果的收入就能達到每畝2萬~3萬元,有些村民還做起了農家樂。
漢源縣大田鄉鄉長任雪玲對《瞭望東方周刊》介紹,如今大田鄉老百姓人均年收入達40萬元以上的占5%,30萬~40萬元的占10%,10萬~30萬的占到了80%。
把“女兒”先打扮起來,再嫁出去
“雅安在過去4年的災后重建過程中,生態旅游業之所以能夠形成規模,離不開企業的開拓。”徐一心告訴本刊記者。
以名山區為例,為落實“茶旅融合”的發展理念,區政府與雅安市有關單位共同出資組建了一家國有企業,它既是利用災后重建資金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主體,也是名山 “1+6+N”旅游規劃的具體實施人。其中,其所建設經營的蒙頂山國家茶葉公園是國內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以茶產業為主題的公園。
“現在農業部所屬的中農茶促會以我們為樣板,把蒙頂山國家茶葉公園作為了未來制訂國家茶葉公園的標準。”吳宏介紹。
從整個雅安市的情況來看,2013~2016年,雅安旅游項目簽約金額超過了500億元,引進了東方園林、能投集團、中業集團、港航集團等一批集團企業共同做大旅游的“盤子”。
這背后,政府的引導作用不可或缺。
“這種引導不僅僅限于‘書記、市長親自帶隊推介雅安旅游項目,關鍵是要利用好災后重建資金,做好本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規劃、配套政策的制定,也就是通常說的‘筑巢引鳳,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徐一心說。
政府做好規劃、服務、政策引導和基礎設施建設,由龍頭企業帶動,吸引更多的優質投資者進入,形成企業聯盟、基地聯盟和品牌聯盟共同推動雅安的生態旅游業發展。吳宏把這種政府與企業的分工合作比喻為“嫁女兒”,“相當于我有個女兒長得比較漂亮,但是缺乏美譽度,我們先把她打扮起來,讓她更有氣質和素養,然后再嫁出去。”
康源農產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源)董事長付德彬是位于蘆山縣的龍門鄉生態農業園的投資人,他對此感觸頗深。
“剛開始,龍門鄉連車都很難開進去。從成都拉種苗、物資過去,200多公里路程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時間。直到蘆山縣政府把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修通,我們才打開了局面。”付德彬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為了吸引企業投資,龍門鄉在土地流轉方面還開創了一種嶄新的“農戶+合作社+企業”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農民把土地交給鄉里或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合作社則把土地流轉給企業。農民獲得固定的土地租金,在企業經營產生利潤之后再坐享一份分紅,同時還能在企業打工賺錢。
“每畝土地的租金是2000元,他原來一畝地才收入幾百元錢。如果是打工,一個人一年掙2萬元沒問題。”付德彬對本刊記者介紹。
在雅安市委常委、蘆山縣委書記宋開慧看來,這樣的發展模式讓地方實現了產業轉型升級,更重要的是改變了當地老百姓的收入和觀念。
“人的改變是最顯著也是最要緊的。” 宋開慧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造福百姓”不只是安置生活
“政府‘搭臺、企業‘唱戲,說到底為的是造福一方百姓,這里說的‘造福不光是安置他們的生活,還要幫助他們安排好生產。而無論是生活還是生產,尊重老百姓意愿、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都是我們嚴格遵循的準則。”徐一心對本刊記者介紹。
習近平總書記曾對雅安的震后重建作出了重要指示:“探索出一條中央統籌指導、地方作為主體、災區群眾廣泛參與的恢復重建新路子。”
這一指示精神為雅安的探索指明了道路。雪山村正是“群眾廣泛參與”的典型案例。
“所有的房屋建設、裝修,民宿的經營管理,收入的分配等,都由村民自己來作主。”寶興縣縣委書記石章健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為了改變過去災區重建更為注重建“消費品”的做法,中國扶貧基金會對雪山村的重建一開始就確定了發展鄉村旅游的路子——房子既要老百姓自己住,還要能作為精品民宿來經營。
于是,來自70多個國家的900多位設計師為雪山村免費設計了128種方案。雪山村成立了村民的自建組拍板,從中選出了一種,并結合自己的居住需求作了戶型改動,最終實現了“一二層自住、三四層出租,入口不同,生產生活互不影響”的效果。
自建組完成房屋建設、裝修任務之后,接下來的民宿運營則由村民合作社統籌。
接待游客的前臺、打掃房屋的服務員均為村民應聘上崗,為游客提供標準化的服務;為避免拉客搶客的現象發生,游客的入住需求被隨機安排到有空余房間的家庭;宣傳推廣工作則由政府旅游主管部門承擔。
“房租是按照房屋面積而定,分紅則根據客房裝修時村民與合作社分擔的費用比例來分。”李勇告訴本刊記者,“在裝修家里客房時,我自己花了10萬元,合作社拿扶貧基金給我出了10萬元,這樣我能獲得的分紅是民宿經營收入的一半。到年底如果還有結余,全村人均分。”
這樣的村民自建自管模式,在戴維新村、蒙山新村等雅安其他鄉村旅游示范村,已經成為范例。而雪山村模式,如今已經成為國內很多地區學習的樣本。
更有突破意義的是,這種新村聚居點的管理模式如今已經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作為雅安市的第一部實體性地方法規,《雅安市新村聚居點管理條例》已經于2017年4月10日發布,7月20日起將正式實施。
“與汶川的災后重建相比,雅安被關注和被寄予厚望的不僅僅是災民安置,而是如何發揮產業的‘造血機能。而統籌協調政府、企業、群眾等各方面的力量來推動雅安生態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最終目的正是要‘保護一方山水,傳承一方文化,促進一方經濟,造富一方百姓。”葉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