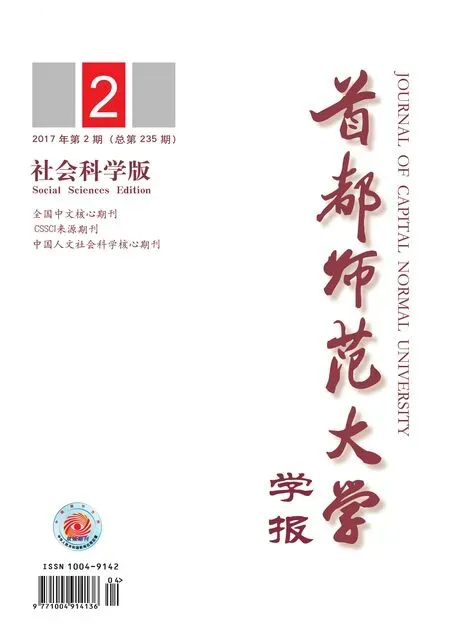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蘇聯式”建筑與“新北京”的城市形塑 —— 以1950年代的蘇聯展覽館為例
李 揚
隨著檔案資料的開放與研究領域的拓展,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與文化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熱門領域。共和國史研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即是蘇聯的影響。無論是以蘇聯為師或是以蘇聯為鑒,蘇聯始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文化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對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蘇聯背景研究,以往研究多集中于高層政治、外交、軍事等層面,對其在社會、文化方面的影響研究不夠。近年來這一局面有所改觀,從蘇聯專家到市政建設以及蘇聯模式影響下的宣傳策略與方式等,讓我們對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有了更豐富的理解。
建筑遺產是一個時代的公共表達。據建筑學者的說法,“建筑是界定城市空間的主要因素,建筑形體和建筑相互之間的關聯組合,決定城市空間的大小、形式和用途”[注]田銀生、劉韶軍編:《建筑設計與城市空間》,天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頁。。城市改造與景觀建設往往伴隨著不同的施政理念與都市現代性的實踐, 19世紀的巴黎即是西方城市史上改造的典范。其中奧斯曼對巴黎的改造就被認為是巴黎進入“現代城市”的標志,法國學者弗朗索瓦茲·邵艾(Francoise CHOAY)指出,盡管有眾多批評,但今天的巴黎幾乎全是奧斯曼的作品,它打造了全新的巴黎形象。而這正是建立在奧斯曼“處心積慮的對景觀透視的基礎上,其每一個作品都具有紀念性意義”[注][法]弗朗索瓦茲·邵艾:《奧斯曼與巴黎大改造》,鄒歡譯,《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5-136頁。。 德國學者本雅明關于巴黎的“拱廊研究計劃”也是極好的例證。巴黎拱廊是現代大型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的先驅,成為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巴黎最重要的景觀之一。本雅明由拱廊來研究整個19世紀的巴黎與當時文人的精神狀態,漂泊的“波西米亞人”形象讓我們印象深刻。[注][(德]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的首都》,劉北成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由建筑景觀出發,揭示其背后的時代變遷與特定群體的精神狀態正是本雅明給我們的啟示。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政府很快即確立了“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政府”的城市建設方針。在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看來,這正是他們所期待的“新北京”。[注]北京市文聯創作委員會編:《我熱愛新北京》,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新北京”建設中的重要內容就是對城市景觀的改造。意大利建筑師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的《城市建筑學》一書中認為“住房和紀念物是城市中兩個主要的經久實體”。[注][意]阿爾多·羅西《城市建筑學·英文版編者序言》,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序,黃士鈞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本文所論述的蘇聯展覽館正是具有公共空間性質的紀念物。 這種具有鮮明時代印記的建筑物很快成為地標,構成了1950年代“新北京”城市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將以蘇聯展覽館為個案,揭示地標性建筑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對城市景觀、文化認同、大眾消費及社會生活的影響。
一、蘇聯展覽館:“蘇聯式”文化景觀的構筑
蘇聯模式在1950年代的北京城市建設過程中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從最初的城市規劃方案到具體的建筑設計,蘇聯專家多參與指導。
蘇聯展覽館正是這種背景的具體實踐。1952年時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李富春訪問蘇聯。在中蘇談判中,蘇方提出愿在中國展示蘇聯的建設成就,包括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建筑技術與建筑藝術等。為此,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上海建設蘇聯展覽館。中方成立了三人領導小組,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任組長,另外兩位為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冀朝鼎與建筑工程部常務副部長宋裕和。同時,北京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趙鵬飛受彭真委托,具體參與展覽館的建設工作。[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二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1頁。事實上,當時的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哲人、中央建筑工程部部長萬里都曾直接過問此事,他們還專門向周總理報告工程預算與設計問題。[注]北京檔案館藏:《彭真、萬里等同志關于工程概算設計工作等問題給總理的報告》,1953年7月26日, 檔案號:1-6-783。檔案顯示,蘇聯展覽館的交工日期經北京市市長彭真與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商定,各項工程將在1954年七八月間陸續完工。[注]北京檔案館藏:《李哲人副部長與米古諾夫同志談話紀要》,1954年6月10日,檔案號:1-6-784。據宋裕和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展覽館于1953年10月15日開工。蘇聯方面負責建筑與設計的專家主要有安德烈耶夫、吉斯洛娃與郭赫曼。據北京市市長彭真的說法,該工程中方具體負責人為宋裕和、冀朝鼎、王光偉、汪季琦、趙鵬飛。[注]北京檔案館藏:《蘇聯展覽館工程問題座談會紀要》,1954年3月10日,檔案號:1-6-784。蘇聯的建筑藝術與風格、技術標準等成為展覽館最主要的參照系。彭真就展覽館建筑與施工問題在與蘇聯專家的談話中說到,“一切要用莫斯科的標準,……我們過去在山溝,沒有建筑力量,進城后才有。技術人員中很多對蘇聯先進經驗還是抗拒的,有的還持保留態度,也有不少是虛心學習的。……可以像在莫斯科一樣地管理這個企業,完全不要有顧慮”。[注]北京檔案館藏:《彭真同志與展覽館施工專家多洛普切夫同志的談話紀要》,1954年2月11日,檔案號:1-6-784。展覽館的整體設計方案及施工方法等由蘇聯專家主導,中方協作配合。
作為大型公共建筑的展覽館,修建起來并非易事。據《蘇聯展覽館》宣傳手冊記載:“蘇聯展覽館占地面積約十三萬五千平方公尺,建筑體積是三十二萬八千立方公尺。”[注]《蘇聯展覽館介紹》,載接待蘇聯來華展覽辦公室宣傳處編:《蘇聯展覽館——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宣傳資料之一》1957年版,第1頁。1957年,由接待蘇聯來華展覽辦公室宣傳處編輯出版的《蘇聯展覽館》宣傳手冊稱:“它的設計圖紙有一萬五千張,加上曬的藍圖總共有五萬張。如果把這些圖紙一張接一張地擺開,按一公尺寬來計算,足可以擺一百里長。”[注]《蘇聯展覽館是怎樣建設起來的》,載接待蘇聯來華展覽辦公室宣傳處編:《蘇聯展覽館——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宣傳資料之一》1957年版,第15頁。巨大的建筑體量以及設計方面的精益求精,以至該建筑被稱為“當時國內造價最為昂貴的俄羅斯式建筑”[注]《建筑創作》雜志社編:《建筑中國六十年·作品卷(1949-2009)》,天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頁。。
在中央的全力支持與各地軍民的努力奮戰之下,展覽館如期完工,1954年10月2日舉行了開館儀式。蘇聯展覽館建筑平面呈“山”字形,左右對稱,軸線明確而嚴整。整個建筑群以中央大廳為中心,中央前廳左右分兩翼,中央軸線上由北到南分別是中央大廳、工業館、露天劇場,西翼是農業館、莫斯科餐廳、電影院,東翼是文化教育事業展覽廳,另外還有東西廣場。[注]魏琰、楊豪中:《解讀北京展覽館》,《華中建筑》2015年第4期,第33頁。(圖1)

圖1 北京展覽館平面圖資料來源:魏琰、楊豪中:《解讀北京展覽館》,《華中建筑》2015年第4期,第23頁。
建成之后的展覽館,很快成為西直門外的地標。據當時建工部設計局編寫的展覽館建筑參考資料介紹:“蘇維埃的人民建筑師在這一展覽館的創作中,通過所創造出的建筑形象把自己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烈情感,把蘇維埃國家的光榮和偉大傳達給中國人民。這一形式美麗、體積巨大的建筑物,顯示了蘇聯建筑藝術和建筑科學的輝煌成就”;從建筑效果來看,“當人們走出西直門,便看到那高聳入云、閃閃發光的87公尺高的鎏金尖塔,一顆巨大的紅星,在塔的頂端閃耀著。在典型的俄羅斯建筑形式的尖塔下面,是一排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縮寫字母CCCP;塔座正中有蘇聯國徽,塔基座下面的中央前廳正立面拱券門廊上都是毛主席親筆題寫的‘蘇聯展覽館’。整個建筑物坐北朝南,以中央尖塔作為中心,它的東西中央軸線穿過西直門城樓,南北中央軸線通過垂直在廣場前邊的林蔭大道直對遼代建筑——天寧寺塔”。[注]建筑工程部設計總局北京工業及城市建筑設計院蘇聯展覽館設計組編著:《北京蘇聯展覽館建筑部分》,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年版,第1-2頁。(圖2)

圖2 區域規劃平面圖資料來源:建筑工程部設計總局北京工業及城市建筑設計院蘇聯展覽館設計組編著:《北京蘇聯展覽館建筑部分》,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年版,第2頁。
建成之后,梁思成先生對蘇聯展覽館的建筑藝術也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該建筑的整體布局與北京城市的整體規劃尤其是與西直門外至阜成門外一帶的總體規劃是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該建筑也實現了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該建筑很好地體現了蘇聯建筑的民族形式與民族傳統,同時結合中國傳統建筑的一些做法,創造出高度的藝術效果,符合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精神。[注]梁思成:《對于蘇聯展覽館的建筑藝術的一點體會》,載接待蘇聯來華展覽辦公室宣傳處編:《蘇聯展覽館——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宣傳資料之一》1957年版,第8-13頁。
二、景觀重塑與文化認同
建筑與景觀的重塑確實是一個城市文化變遷的重要體現。20世紀30年代,莫斯科城經過大規模規劃與改造,1940年7月,蘇聯建筑師克·斯·阿拉比揚院士在蘇聯建筑師協會的講話中稱:“自1935年7月以來的五個年頭,代表著莫斯科歷史整個的一個時代。”因為“一個巨大而復雜的城市有機體再生了”。街道的加寬、廣場的開辟、莫斯科地鐵與蘇維埃宮、卡盧日街的建筑組群等都是例子。進而他認為聯共(布)中央通過的莫斯科改建總計劃必將在人類建筑史上載入史冊。[注]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編:《關于莫斯科的規劃設計》,建筑工程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143頁。可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在其建國之初大力改造舊的城市空間,重塑新的社會與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族主義的集體認同。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新北京”建筑景觀的營造,也可以重塑城市空間,并促進城市文化認同。
蘇聯展覽館建成之后帶給人們的震撼是巨大的。曾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并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回國的翁文灝在參觀蘇聯展覽館后曾賦詩一首:“規模輪奐復堂皇,物力人工耀眼光。新教宏開遍眾庶,機聲機制富琳瑯。籌謀增進人民福,生產能從根本昌。三十年來雄樹立,已超舊制越千邦。”[注]翁文灝:《游蘇聯展覽館》,載《翁文灝詩集》,團結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頁。翁氏認為這一建筑美輪美奐,可以預見新中國能夠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生產進步。從“已超舊制越千邦”來看,他感覺新政府的壯舉乃前無古人,開創了一個新時代。1954年10月2日展覽館開館當天,著名科學家竺可楨也參觀了展覽館。他在日記中寫到:“午后二點多和楊克強赴西郊蘇聯展覽館參加開幕禮。該屋于10個月當中造成。1500工人的努力,完成偉大友邦展覽會的陳列處所。外觀極為莊嚴而美麗,柱系白大理石。……在文化館介紹了最新測量器,光學如顯微鏡、分光照相儀、照相機、滾珠軸承。三點半入內參觀,因各陳列地點東西很多,而人擁擠,只能走馬觀花,隨大眾環繞一圈,可說好似劉姥姥入大觀園……。”[注]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1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頁。除了自發參觀的群眾外,各單位也踴躍組織觀眾參觀,據一份工作簡報,展覽館自1954年10月2日開館到12月16日停止一般群眾參觀,開館兩個半月參觀人數共2614000余人。平均每天參觀人數達42000余人。其中本市各系統組織的觀眾共1600000人,外地集體觀眾271000人,臨時前來的零散觀眾743000人。[注]北京市檔案館藏:《接待蘇聯來華展覽辦公室參觀組織處工作簡報》第10號,1954年12月15日,檔案號:38-2-147。最后的工作總結中統計的總參觀人數更是達到了2760000余人,已經突破了原定計劃中兩個半月觀眾2600000人的目標。[注]北京市檔案館藏:《接待蘇聯來華展覽辦公室參觀組織處工作總結》(草稿),1954年12月28日,檔案號:38-2-147。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很多文學作品以城市景觀再造為主題揭示“新北京”的變化,這其中就包括“蘇聯式”建筑。如壽儒的《北京地圖》一文用“女兒改地圖”的方式讓我們感受新時代北京景觀的日新月異。作者從舊書鋪買回一張北京的地圖,被女兒要走。而當他想用地圖找一個地名時,發現地圖被女兒改得面目全非。他于是生氣地質問女兒為何在地圖上胡亂涂改。女兒笑稱,地圖很多地方都不對,諸如范家胡同已成為一片大樓,善果寺已經成為公園,原來的刑部街、報子街、丘祖胡同已經被打通修成了一條大馬路。地圖上畫著的紅五星是蘇聯展覽館,一片墨色則是東郊工業區,畫著蝴蝶結的幾個姑娘代表三個棉紡廠的女工,西北方向的方格子則代表著學院路與西北郊的幾大高校諸如鋼鐵學院、石油學院與航空學院。作者對此驚喜不已,因為“七年來(1949-1955),在北京已經建造了一千四百多萬平方公尺的房屋。這個數字相當于北京幾百年積累下來的建筑的十分之七……”。作者不由感嘆:“北京,空前迅速的建設腳步,把舊的北京古城,打扮得多么輝煌壯麗。”[注]北京市文聯創作委員會編:《我熱愛新北京》,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42-45頁。除蘇聯展覽館外,這里的東郊工業區、學院路高校建筑群等都是“蘇聯式”風格。如酒仙橋地區的774廠,即北京電子管廠以及北京熱電廠,均是蘇聯在“一五”期間援建新中國的工業項目。[注]張久春:《20世紀50年代工業建設“156項工程”研究》,《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09年第3期;劉伯英、李匡:《北京工業遺產建筑現狀與特點研究》,《北京規劃建設》2011年第1期。清華大學主樓的設計也曾仿照莫斯科大學主樓。景觀的變化除給人們帶來感官的沖擊之外,也有心理的變化。散文家楊朔的筆下也呈現了對蘇聯展覽館所展示的社會主義圖景的向往。他寫道:“北京城的上空新矗起一座金色的尖塔,塔尖鑲著顆閃閃發亮的紅星。清晨陽光一照,金塔便射出光芒,那顆紅星像火焰似的燃燒起來。紅星下面是蘇聯展覽館,館里擺著蘇聯人民所創造的生活,所創造的事業。奶奶想望著這顆紅星,北京城的人誰不想望著它。望見紅星,我們就望見了自己的理想,望見了明天。紅星——正是人類生活里最美的東西的結晶啊!”[注]楊朔:《京城漫記》,載北京市文聯創作委員會編:《我熱愛新北京》,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而文學家鄒荻帆也在其詩作《兩都賦》中歌頌北京與莫斯科對人類解放的巨大意義及其各自偉大的建設成就。[注]《北京的詩》,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118頁。可見,20世紀50年代,在中蘇同盟的背景下,全社會形成了學習蘇聯的文化氛圍。這些“蘇聯式”建筑也成為當時北京市重要的文化和社會空間,許多建筑至今仍發揮著重要的文化功能。
三、“蘇聯式摩登”:休閑與消費文化
正如著名學者李歐梵所指出的,“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產物”。在他所描繪的“上海摩登”景象中,城市公共構造與空間占有著重要位置。諸如上海外灘的建筑、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與跑馬場等均是民國上海現代性的體現。[注][美]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毛尖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頁。蘇聯展覽館建成之后,在完成蘇聯成就展覽的使命之后很快也成為北京公共空間的組成部分,其作為展覽館與文化單位的身份開始凸顯。蘇聯展覽館及其附屬建筑諸如莫斯科餐廳(即俗稱的“老莫”)、電影院、露天劇場等在當時也刮起了一股“蘇聯風”,引領著當時的娛樂文化與消費時尚。
1954年12月初北京市副市長薛子正提出接管蘇聯展覽館的方案。其中第一套方案是由各部委與北京市聯合組成管理委員會,第二套方案是全部展覽館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社會福利事業管理局接管。他認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機構編制與經費開支過大,希望財政支持。對于餐廳、劇場、電影院的經營方針問題,他的初步意見是:“如果餐廳交給市福利公司經營管理,除緊縮編制節省開支外,擬將現在廚房的電氣設備暫時封閉不用,改設中國式的煤爐灶,減少勤雜人員等,這樣就可以降低成本,但恐蘇聯專家不同意(當時有十五位蘇聯專家,擬留聘二至三位廚師專家作顧問)。在餐類方面,除繼續經營俄式餐食外,應增設中餐部,亦以小吃為主,并向西郊公園開門,使公園游人進出方便,營業亦可望擴大而不致于虧累。露天劇場和電影院交給市文化局戲曲管理委員會接管,除改善經營管理外,向西郊公園開門,并專設售票處,并與公園業務相結合。”[注]北京檔案館藏:《薛子正同志關于接管蘇聯展覽館的意見》,1954年12月1日,檔案號:1-6-944。中央采納的應該是第一個方案,后來蘇聯展覽館專門成立了管理處,負責展覽館的經營與管理。到1957年,蘇聯展覽館向北京市委申請改名,原因是因名稱問題使其對外活動受限:“自1954年底蘇聯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在北京結束后,蘇聯展覽館即擔負著接待國內外各種展覽和各種政治文化活動的任務。莫斯科餐廳和電影館自1955年實行長期對外營業以來頗受中外人士的歡迎。但某些對外活動,由于‘蘇聯展覽館’名稱的關系,常受到一定限制。為了今后各種活動更加方便起見,擬將蘇聯展覽館更名為北京展覽館。”更名后,莫斯科餐廳名稱不變,電影館更名為北京展覽館電影館,劇場更名為北京展覽館劇場。[注]北京檔案館藏:《蘇聯展覽館改名為北京展覽館的請示》,1957年10月4日,檔案號:2-9-157。
據此可知,當時莫斯科餐廳與電影館尤其受到熱捧。新中國成立初期,主宰北京電影市場數十年的西方影片逐漸退出中國市場。蘇聯影片及兄弟國家的影片占據了北京電影市場外國片的主要陣地。[注]周靜:《新中國“十七年”北京大眾的娛樂生活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未刊),第17頁。據統計,“我國所發行的蘇聯影片(新片),從1949年起到1957年上半年止,共計發行長片265部(其中藝術片206部、紀錄片59部),短片共203部;同期觀眾的總數達十四億九千七百八萬余人次”[注]沙浪:《蘇聯電影與中國觀眾》,《中國電影》1957年11、12月號合刊,第81頁。。北京展覽館的蘇聯電影放映引領著當時北京城的文化與藝術潮流。
另外,電影館的建筑藝術與裝飾風格在當時無疑是領先的。據當時建工部編寫的資料,“電影館紅色的絲絨盤金花的大幕,燦爛的天花彩畫,金色花紋的柱頭等,都做到了適度的裝飾”;而這種裝飾風格也吸取了中國傳統建筑的形式與紋樣,“電影院的希臘花紋柱頭結合了中國的如意花紋”[注]建筑工程部設計總局北京工業及城市建筑設計院蘇聯展覽館設計組編著:《北京蘇聯展覽館建筑部分》,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年版,第4-5頁。。可見,建筑師對此頗為用心。當時對蘇聯展覽館電影館的介紹稱:“它是一個吸引大量觀眾的地方。觀眾們在這里可以看到自己一向喜好的蘇聯電影,并親身體驗到蘇聯人民的文化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和幸福……電影館舞臺的上端,高懸著一塊紅底金花的圓匾,上面鐫刻著六個輝煌的金字:‘藝術屬于人民’——這是整個電影館的主題。”電影館開館后,早期主要放映反映蘇聯經濟文化建設成就與文化生活的紀錄片。1954年10月至12月放映的電影包括:《莫斯科在建設中》、《中國展覽會在莫斯科》、《蘇聯滑雪者》、《科學宮》、《少先隊夏季生活》、《伏爾加河—頓河運河》、《莫斯科的郊區》等。[注]《藝術屬于人民——介紹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的電影館》,載接待蘇聯來華展覽辦公室宣傳處編:《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紀念文集》,時代出版社1955年版,第130-131頁。此后,這里的電影展映與宣傳活動也持續進行。如1955年11月7日,“蘇聯電影周”在北京開幕,映出《忠實的朋友》、《培養勇敢精神》和《瑪利娜的命運》3部影片。14家影院參加映出,共計映出1328場,觀眾60.90萬人次。影院當中就包括新增的專業電影院—蘇聯展覽館電影院,隸屬展覽館。[注]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電影公司合編:《北京文化史資料選集——北京市電影發行放映單位史》(下冊)1995年版,第110-111頁。次年11月7日,蘇聯電影工作者代表團一行四人抵京,蘇聯演員瑪列茨卡婭、莫爾久闊娃、潘尼奇與烏茲別克導演魯柯夫等分別前往首都電影院、蘇聯展覽館電影院與觀眾見面并接受了觀眾的獻花。[注]《蘇聯電影工作者代表團四位團員和北京觀眾會面》,新華社新聞稿,1956年11月8日。
事實上,由于1950-1960年代物質相對匱乏,北京群眾的娛樂生活也相對貧乏。由于新中國對電影事業的支持,改變了舊社會電影票價昂貴的現象并擴大了放映范圍,使得電影愈來愈走向平民大眾,于是看電影成了人們最主要也廣受歡迎的娛樂方式。一位北大畢業生回憶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學生活稱,當時大學的課余娛樂活動,主要以看電影為主。當然,那時候的電影不能說是純粹的娛樂活動。入學后看過蘇聯黑白電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彩色電影《保爾·柯察金》,當時也是非常自覺地去接受教育。國慶十周年學校還專門在學校操場放映一批“獻禮片”,包括不少蘇聯電影。[注]王則柯:《五十年前讀北大》,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4頁。據一位曾在冶金工業部工作的老同志的口述實錄,他稱自己的主要娛樂方式在新中國“十七年”時期主要是看電影,包括在展覽館的觀影活動、到中山公園聽音樂茶座等。[注]梁景和編:《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第四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頁。很多知識分子也觀看大量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電影。考古學家夏鼐1958年1月28日的日記中亦有到展覽館觀影的記錄,“下午工會發起參觀北京天文館,偕秀君、炎兒前往,此系第一次參觀北京天文館。先參觀展覽室,3時開始天象儀表演,約30分鐘。散場后,赴蘇聯展覽館電影場,觀朝鮮電影《祖國的兒子》”[注]夏鼐:《夏鼐日記》(第5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50頁。。有意思的是,作為晚清遺老的許寶蘅[注]許寶衡(1875-1961)的介紹及相關史實參見馬忠文:《許寶衡與溥儀》,《博覽群書》2011年第9期。在其日記中也有參觀蘇聯展覽館并觀看電影的記載。1956年8月14日 “(初九日癸丑)八時到蘇聯展覽館,參觀原子能展覽,并看電影,不能有所獲,于此事毫無知識,莫名其妙,等于盲人捫檠,即在莫斯科餐廳午餐”[注]許寶蘅:《許寶蘅日記》(第5冊),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883-1884頁。。即使看不明白,遺老們仍愿一探究竟,這正說明了蘇聯展覽館電影館在當時對人們的吸引力。正如戴錦華指出的,“20世紀中葉,電影不僅是大眾社會的世俗神話的源泉,而且影院幾乎成了最輝煌的塵世‘教堂’:人們在影院中獲得教益,獲得日常生活的信念與價值,獲得生活方式與時尚的信息”[注]戴錦華:《電影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蘇聯電影在當時也有這樣的作用。
觀影活動之后,很多人的選擇即是到展覽館的莫斯科餐廳就餐。可以說,蘇聯展覽館的莫斯科餐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成為北京最著名的幾家西餐廳之一,也引領著當時的飲食風尚。王蒙在談到莫斯科餐廳時說:“五十年代北京蘇聯展覽館建成,莫斯科餐廳開始營業,在北京的‘食民’中間引起了小小的激動。份飯最高標準十元,已經令人咋舌。基輔黃油雞卷、烏克蘭紅菜湯、銀制餐具、餐廳柱子上的松鼠尾花紋與屋頂上的雪花圖案,連同上菜的一絲不茍的程序……都引起了真誠的贊嘆。”[注]王蒙:《吃的五要素》,載郭友亮、孫波主編:《王蒙文集》第9卷,華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頁。除正餐之外,莫斯科餐廳的蘇式糕點也長期供不應求。1958年5月,展覽館管理處向北京市委提出請求,要求增加食品原料的供應。該報告稱:“莫斯科餐廳自制的蘇式糕點,除餐廳日常營業用以外并長期供應蘇聯大使館和王府井百貨大樓的一部分,但因面粉、白糖、花生油等原料供應不足,其點心生產總是供不應求,由于目前天氣漸熱,餐廳營業量增大,急需增加糕點和冷食的生產。因此,請糧食局通知西四區糧食科自1958年5月15日起每月增加供應富強面粉20袋,花生油250斤,請副食品商業局通知糖業糕點公司每月增加供應白糖1500市斤。”[注]北京檔案館藏:《蘇聯展覽館管理處關于莫斯科餐廳請求增加富強粉、白糖、花生油的供應問題》,1958年5月16日,檔案號:2-10-080。可見其受歡迎程度之高。
直到20世紀60年代,正如一本小說的描述:“1968年的北京,諾大的一個城市,只有兩家對外營業的西餐廳,一家是北京展覽館餐廳,因為北京展覽館是五十年代蘇聯援建的,當時叫蘇聯展覽館,其附屬餐廳叫莫斯科餐廳,經營俄式西餐。……以后才改成現在的名字,但人們習慣了以前的名字,一時改不過口來,北京的頑主們干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廳是位于崇文門的新僑飯店,經營的是法式西餐。這兩家西餐廳是當時京城頑主們經常光顧的地方。”[注]都梁:《血色浪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頁。我們在很多描寫20世紀50-70年代北京的文學作品中都能看到“老莫”的形象,很多精英及子弟的光顧,使這里已成為一個象征性的文化符號。[注]劉心武:《“大院”里的孩子們》,《讀書》1995年第3期。可見,俗稱的“老莫”在20世紀50-60年代的北京消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一位1950年代出生的人所說:“莫斯科餐廳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甚至超過了展覽館”,而且“事情有時很奇怪,統一建筑體系,展覽館留給人們的,是地道的蘇聯文化氣息,而‘老莫’卻要復雜得多。它見證了中國社會階層的區別,見證了特殊歷史條件下特殊人群的悲歡聚散……莫斯科餐廳對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長,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很難詮釋,但至少注解了他們在特殊時代氛圍中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浪漫”。[注]黃新原:《五十年代生人成長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64-65頁。于是,“老莫”作為標志性消費文化的符號,成為幾代人共同的集體記憶。
四、結 語
北京自晚清民國時期開始,雖然也有不少城市近代化的探索,但當時的北京一直以“文化古都”的形象示人,與“摩登上海”形成鮮明對比。新中國成立后的“新北京”如何塑造新的城市文化?這可能需要我們從城市史與社會文化史等多角度對此加以解讀。近年來城市文化史中的一個新的研究趨勢是將“日常”(everydayness)作為一種分析方法。“日常”的概念是歷史、現代性和文化實踐關系中的一個關鍵構成部分。[注]董玥主編:《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導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北京展覽館(蘇聯展覽館)的營建,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城市新的地標空間的誕生,營造了新的城市文化氛圍,豐富了大眾的休閑娛樂生活,讓我們感受到了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的“日常”,也揭示出當時北京都市文化中的“蘇聯印記”。此外,北京展覽館(蘇聯展覽館)的個案也提示我們,在城市文化建構過程中空間的意義。在20世紀50年代“新北京”的文化敘事中,“蘇聯式”建筑景觀成為重要的書寫對象,建筑景觀的營建有助于重塑城市空間并進一步促進城市文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