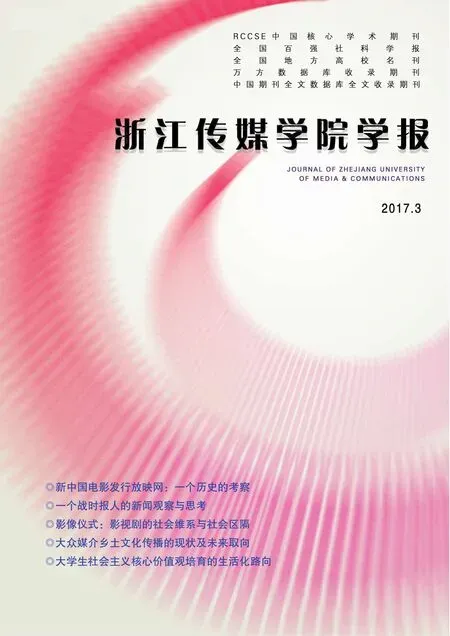中國居民媒體使用對其環境認知及環保參與行為的影響分析
沈 珺
中國居民媒體使用對其環境認知及環保參與行為的影響分析
沈 珺
通過對中國期刊網和EBSCO-CS(大眾傳媒學全文數據庫)有關環境傳播文章的主題分析,得出國外研究重視環境專業知識的教育涵化,國內研究多理論探討,少量化分析。基于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環境模塊的數據,圍繞中國居民媒體使用對于環境認知及環保參與行為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研究發現:使用傳統媒體比新媒體更能提高中國居民的環境知識水平,但新媒體使用比傳統媒體使用更有助于增進中國居民的環保意識;傳統媒體比新媒體更有利于促進中國居民的環保參與行為;環保認知越高的中國居民行使更多的環保參與行為。研究進一步提出,提高中國居民的環境認知水平,專業的環境教育須先行;促進中國居民的環保參與行為,新舊媒體融合、線上線下互聯是正解。以提高個人經濟水平與教育程度為基礎保障,以環境修辭為話語導向,以環境關心為倫理標桿,以環境友好行為為價值準心,把行為變做習慣,把綠色意識融入身份認同,才能建構環境友好型社會。
媒體使用;環境認知;環保參與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我國深受多種環境問題的困擾:霧霾肆虐,黃河斷流,湖泊富營養化加劇,白色污染蔓延各地,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嚴重,旱災水災頻發,多種生物瀕危等等,居民的生活安全不斷遭到威脅,保護賴以生存的環境的呼聲也越發高漲。事實上,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關注環境問題,1972年,周恩來總理派代表團參加了聯合國在瑞典舉行的人類歷史上首次全球環境會議。[1]隨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相繼設立環境專業。1973年,第一份環境期刊《環境保護》創刊。1979年,第一部環境法律——《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這標志著我國正式將環境保護工作納入國家法制化軌道。環境保護是一項重要的社會事業,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光要靠科學的政府監管機制,更要依靠公眾參與環境保護。[2]然而,根據由國家環保總局指導,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組織編制的國內首個環保指數——“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顯示,中國公眾的“環保意識”、“環保行為”、“環保滿意度”三項指標自2005年起持續下降,2007年的指數僅在40分左右,無疑為中國的環境保護治理拉響了警鐘。[3]如何提升公眾的環境意識、積極調動公眾的環保參與行為是近年來國內環境傳播學科亟待探索的話題。
環境傳播自20世紀60年代發展至今,已成為與科學傳播、健康傳播、風險傳播鼎足并立的傳播學重要分支學科。[4]我國的環境傳播研究由狹義的環境傳播——對環境新聞報道的范式研究[5-6]延伸到廣義的環境傳播層面(分為環境新聞意義框架、功能主義意義框架、社會建構意義框架等認知取向),大概也就數十年,且真正以“環境傳播”為名開啟此學科的研究探索始于2009年,此前多為“環保傳播”。為了更準確地把握中西方針對環境傳播的研究現狀及趨勢,筆者對比分析了中外兩大數據庫(EBSCO-CS大眾傳媒學全文數據庫,中國期刊網)關于環境傳播研究類論文,以便更深入地比較國內外環境研究的差別。對于國外環境傳播論文的分析,基于從EBSCO Communication Source數據庫中以“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為關鍵詞共搜到論文1257篇,取排名前20的關鍵詞詞頻分布制圖如下:

圖1 EBSCO-CS關于“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的主題分析
國際上對于環境傳播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對環境問題本身的關注,對于生態學、環境科學、氣候因素、環境保護、環境政策、可持續發展這些議題都有深入細致的探討。環境傳播學科的開創者Cox說過,環境傳播是一個構建公眾對環境信息的接受與認知,以及揭示人與自然之間內在關系的實用主義與建構主義并存的工具手段。[7]可見在環境議題下探究人與自然內在關聯的前提是構建公眾對環境信息的認知。圖1所示,國外對于構建公眾對環境信息的認知層面尤為重視,尤其注重環境教育問題,在系統實踐上重視傳播專業的環境信息與知識,呈現出環境實用主義的取向。
以“環境研究”為關鍵詞,在中國期刊網“傳播學和新聞學”學科分類下共搜到213篇論文,提取論文關鍵詞,再由excel生成如下柱狀圖:

圖2 中國期刊網關于“環境研究”的主題分析
圖2證實了中國當下的環境傳播研究注重理論層面的建構,[8-9]強調媒體特別是新媒體對環境傳播的影響作用[10](絕大多數的實證分析也集中于這一主題),注重環境議題的話語框架研究。[11-12]對比可知,我國的環境傳播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究內容單一、研究問題淺表化,對于理論層面的建構討論頗多,而在應用實踐層面的研究不足。
二、研究問題
針對國內環境傳播研究領域實證分析少、量化研究弱的現象,本文選取中國國家數據庫公布的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為分析數據,展開環境傳播功能主義意義框架下的量化實踐探索,系統檢視媒體使用對于中國居民的環境認知行為(環境知識水平、環境問題意識),以及環保參與行為的影響。具體來說,本研究將針對以下幾個問題展開探討:(1)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使用如何影響中國居民的環境認知?(2)如若有區別,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使用分別對中國居民環境認知的兩個層面:環境知識水平、環境問題意識有何影響?(3)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使用對于中國居民的環保參與行為有何影響?(4)中國居民的環境認知行為和環保參與行為是否存在相關性?
三、研究假設
國內有關環境傳播的案例分析表明,公眾環境專業知識的缺乏,是造成公眾參與環境傳播諸多問題的重要原因。盡管有些學者認為,掌握豐富的環境科學知識并不必然促成環保行動或決策,[13]有學者通過對《人民日報》自2003年至2012年10年間涉及環境議題的報道進行內容分析發現,傳統媒體所涉及的常規報道,諸如生態保護與監管、節能減排等常規性議題占據了絕大多數,這種長期秉持自我中心式的、自上而下強調告知與說服的環境宣傳難以獲得公眾的持續關注和深度關心。[14]另外根據PNAS上的一項研究,[15]人們獲取科學知識的決定因素相當復雜:媒體接觸時間、知識互聯性、社會網絡關系、個性特點等因素都將影響科學知識的獲取,相對傳統媒體的單一性,新媒體塑造的多元知識景觀模式更利于提供個性化、多維度的知識供給。對此,我們做出如下假設,H1: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使用與中國居民環境知識水平掌握正相關程度更高。
基于環境量表設計機理,單一的客觀環境知識不足以測量人們對于環境的認知,公眾的環境理念體系(Belief System)也是測量環境認知的重要評判標準,具體可體現在公眾對于環境問題意識的主觀感知變化。[16]一些研究發現對于科學知識的認知框架不僅建立在人們已有的科學知識基礎上,某種程度上也依賴于人們的價值取向和信任程度。而取得人們信任維度的方法之一是透明化科學知識的可溯研究來源并公開科學分析的研究過程。[17]有關新媒體的研究表明,新媒體構建的社會網絡環境更為開放,[18]信息生產和意見表達的門檻更低,[19]用戶能獲取更透明性的科學信息。因此,我們認為新媒體更有助于獲得公眾特別是對敏感環境議題的信息信任維度,從而更關注環境問題。故假設如下,H2: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使用與中國居民環境問題意識成正相關程度更高。
國內有關環保公眾參與的案例大多圍繞環境突發事件,調研媒體在危機處理中與公眾的互動機制。研究發現,新媒體信息的共享與言論自由分散了社會權力,提升了公眾參與社會的能力。[20]李春雷通過對昆明PX事件發生地及其周邊的實證調研,發現新媒體實現了環境傳播機制的新塑形,即實現了網上網下信息聯通和情感聯動,新媒體在紓解傳統媒體所帶來的信息阻滯的同時,也促進了民眾間的信息互動,新媒體對底層群體的認知、態度與行為的攪動推動了底層民眾的環境參與。[21]對于公眾的環境參與行為,亦可視為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或環境友好行為的一種具體實踐。環境友好行為是指個體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主動參與,并積極行動做出與環境直接相關的友好行為。[22]有學者在研究性別構成的親環境行為差異時,指出親環境行為有兩種導向:以家庭為導向(私人)的環境友好行為(如物品循環利用)以及以團體/社會為導向(公眾)的環境友好行為(如抗議運動)。[23]Stern也曾將環境行為分為公共領域的非激進行為和私人領域的環保行為。[24]因此,我們形成如下假設:
H3: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使用與中國居民環保個人參與行為正相關程度更高。
H4: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使用與中國居民環保公共參與行為正相關程度更高。
環境心理學者將“人們意識到諸如資源過度使用或環境污染等問題,并支持解決這些問題的程度,或為解決這些問題表達的個人意愿”定義為環境關心(Environmental Concern),[25]并認定環境關心意識越強烈,個人會表現出更多的親環境行為。[26]Clare J.Dannenberg等人的一項實驗性研究證明了通過媒體構建的環境修辭的正確疏導,人們對于環境知識的倫理反思會上升發展為可持續環保價值觀,制約并敦促人們的環保行為。[27]因此,我們做出如下假設,H5:中國居民環境認知越高,其行使的環保參與行為也越多。
四、研究方法及數據分析
本研究選取的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中的環境模塊。該調查以18周歲以上的中國居民為研究總體,調查時間為2013年,最終有效問卷為10724份。
(一)變量測量
1.因變量及其測量
中國居民環保參與行為:本研究用于測量中國居民環保參與行為的是10個題項,答案均采取三級量表(從不、偶爾、經常),經KMO檢驗得出值為0.8,Sig=.000,統計顯著,說明所有題項適合做因子分析。隨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煉為兩個不同因素。一個因素可稱為中國居民的環保個人參與行為(alpha=.66),其中包括的陳述有:(1)垃圾分類投放;(2)與自己的親戚朋友討論環保問題;(3)采購日常物品時,自己帶購物籃或購物袋;(4)對塑料包裝袋進行重復利用;(5)主動關注廣播、電視和報刊中報道的環境問題和環保信息。另一個因素可稱為中國居民的環保公共參與行為(alpha=.78),包括:(6)為環境保護捐款;(7)積極參加政府和單位組織的環境宣傳教育活動;(8)參與民間環保團體舉辦的環保活動;(9)自費養護樹林或綠地;(10)參加要求解決環境問題的投訴或上訴。
本研究探討的中國居民的環境認知是指對環境及其相關問題的各種認識和基本理解,包括環境知識水平和環境問題認知兩方面。其中環境知識水平的測量含10個題項:(1)汽車尾氣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威脅;(2)過量使用化肥農藥會導致環境破壞;(3)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會造成水污染;(4)含氟冰箱的氟排放會成為破壞大氣臭氧層的因素;(5)酸雨的產生與燒煤沒有關系;(6)物種之間相互依存,一個物種的消失會產生連鎖反應;(7)空氣質量報告中,三級空氣質量意味著比一級空氣質量好;(8)單一品種的樹林更容易導致病蟲害;(9)水體污染報告中,Ⅴ類水質意味著要比Ⅰ類水質好;(10)大氣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會成為氣候變暖的因素(正確、錯誤或不知道)。信度分析表明環境知識量表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alpha=.87),可看作單一量表構成,因此通過對問題的正確回答得分加總構成知識水平指數,分數越高則表明受訪者環保知識度越高。對中國居民的環境問題認知通過對空氣污染、水污染、噪聲污染、工業垃圾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綠地不足、森林植被破壞、耕地質量退化、淡水資源短缺、食品污染、荒漠化、野生動植物減少等12個方面環境問題(alpha=.95)的嚴重性進行檢測,重新編碼為6級量表(1=不關心,6=很嚴重),最后加總取均值得出環境問題意識指數。
2.自變量及其測量
媒體使用:用于測量居民媒體使用情況的媒體分類共6種,均以五級量表測試(1=從不,5=經常),根據主成分分析法提煉出兩個因素。將居民使用的報紙、雜志、廣播、電視歸類傳統媒體使用組(alpha=.61),將互聯網(包括手機上網)、手機定制消息視為新媒體使用組(alpha=.67)。
3.控制變量及其測量
通過對數據缺失值替換序列平均值處理,本研究的樣本總量為10724,人口統計變量包括性別(男性=50.4%);年齡(MIN=21,MAX=101,M=52.7,SD=16.4);教育(8級量表,分為沒受過教育、私塾、小學、初中、高中、高職、本科、研究生以上;M=3.98,SD=1.66);收入水平(8級量表,從0元到百萬以上;M=4.31,SD=1.23),樣本收入水平較集中,54.9%的居民個人年收入在1萬元至10萬元之間。
(二)數據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假設檢驗,所有數據均使用軟件spss22.0進行分析和處理,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預測環境認知和環保參與行為的回歸分析(N=10724)
注:#p<.10,*p<.05,**p<.01,***p<.001,回歸系數為標準化系數β。
(三)研究結果
研究發現,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收入等變量前提下,傳統媒體分組中報紙(β=.128,p﹤0.001)、雜志(β=.054,p﹤0.001)與中國居民環境知識水平顯著正相關,廣播(β=.018,p﹤0.1)呈現微弱正相關,而在新媒體分組中互聯網與中國居民環境知識水平顯著正相關(β=.173,p﹤0.001)。傳統媒體使用變量解釋了知識水平指數2.2%的變差,對比新媒體解釋比例為1.4%,可見傳統媒體的效果略勝一籌。因此,假設1未被證實。
傳統媒體分組中,報紙(β=.045,p﹤0.01)與廣播(β=.063,p﹤0.001)對中國居民的環境問題意識具有顯著正面影響,出人意料的是,電視的使用卻對環境意識起反作用(β=-.029,p﹤0.01)。在新媒體分組中,互聯網與中國居民的環境問題意識顯著正相關(β=.059,p﹤0.001),手機定制消息起到了微弱的正面效應(β=.020,p﹤0.1)。相較傳統媒體分組(R2增量=.6%)與新媒體分組(R2增量=2.0%)的模型解釋力,可知后者所起的正面效果更佳。因此,假設二得到了經驗性支持。
接觸媒體越多,中國居民行使的環保參與行為也越多,且個人參與行為受到的影響更大。但有趣的是,傳統媒體無論對中國居民的個人環保參與行為(R2增量=4.9%)還是公共參與行為(R2增量=3.9%)的模型解釋力均要大于新媒體(R2增量=.4%,R2增量=.7%),這一發現駁斥了假設三和假設四。
無論是中國居民的環境知識水平,還是環境問題意識程度,都能影響人們參與環保行動,且環境認知模型對于個人環保參與行為模型的解釋力更強(R2增量=3.9%)。因此,環境認知與環保參與行為存在正相關,假設五成立。
研究還發現,中國居民的環境知識水平普遍偏低(M=4.66,SD=2.92),環境保護意識淡漠(M=3.15,SD=1.6),環境認知水平低下。女性及年輕人掌握更多的環境知識,也更樂意參與公益環保活動。受過良好教育的居民,以及高收入人群更具有環境意識,具備更高的環境常識,也參與更多的環保活動。
五、討論和結論
總體而言,中國居民的環境知識水平與環保個人參與行為受媒體影響的效果較為顯著,而模型中環境問題意識和環保公共參與行為模塊,相對而言解釋力偏低,也從側面反映出環境問題意識和環保公共參與受影響因素更具復雜性。此外,本研究還得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發現。
提高中國居民的環境認知水平,專業的環境教育須先行。雖然本研究證明中國居民使用媒體能顯著提高環境知識水平,但國內的環境報道的突出痼疾為“有事則抓緊,無事則放松”,環境議題存在熱點聚焦持續力低的現象,環境突發性事故稍有緩解,新聞報道也隨之茶涼。[28]故而一味依靠媒體宣傳,難以持續性提供環境知識供給。且有研究發現,多數針對科學話語的不信任事件源于缺乏科學專業知識背景下,專家話語的缺失或信息解釋不及時,[29]而造成認知框架模糊從而發展成風險常態化,[30]引發普遍信任危機。若以教育建構生態環境的先驗知識,構成個人環境綠色思維,便會減少因對環境突發事件的不確定性導致的信任危機,規避知識盲區造成的偏見行為。另一方面,本研究設計的環境意識模塊證實媒體只是影響中國居民環境意識的小概率因素,多項研究表明,價值觀、倫理道德、教育背景、經濟地位等多元環境素養因子皆能影響公眾的環境決策。價值觀等影響因子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形成,唯有靠春風化雨般的教育涵化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公眾的環境素養,畢竟要公眾形成綠色身份認同,主觀的意識能動大于客觀的限制條件。[31]再者,發揮媒體本身的教育功能也不容忽視。大眾媒體在傳播知識、價值以及行為規范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早在萊斯提到大眾媒體的社會化功能時便有詳細的陳述。[32]媒體應該通過細水長流的新聞傳播、典型問題剖析、解讀環境管理文件、監督批評破壞環境的事件等方式提升公眾環保意識[33],轉變公眾既有的環境價值觀念,提高公眾自覺關心環境、介入環保行為實施的環境素養。最后,無論是教育層面的環境知識供給,還是媒體層面的環境宣傳,提高環境科普知識的透明度、增加公眾的信任感均是提高環境認知行為行之有效的著力點。
促進中國居民的環保參與行為,新舊媒體融合、線上線下互聯是正解。新媒體提供的更多元化用戶內容生產機會,更寬泛的環境話題參與機制使得多數人認為新媒體在勸服公眾行使環保義務方面更具優勢。然而本研究的數據卻提示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依然是督促公眾實施環境友好行為的權威渠道。但同時互聯網在鼓勵個人環保參與活動,手機定制消息在促進環保公益活動的貢獻揭示出新媒體在提升公眾環保參與熱情的功效,因此,唯有以媒體融合的視角重塑環境傳播的格局,在繼承每一種媒體優勢的基礎上,去創造能更好地符合環境信息傳播規律、更具靈活效應的新媒體互聯機制。削減傳統媒體自上而下的報道環境新聞的范式距離感,提升新媒體自下而上報道環境新聞的模式的權威性,扭轉媒體只是政府圍繞環境事業展開的官方宣傳,或是應對環境議題時被動解釋的刻板印象。線上線下同時營造保護生態環境的輿論氛圍,切實拓寬公眾參與的途徑,提高公眾參與的便利性,以提高個人經濟水平與教育程度為基礎保障,以環境修辭為話語導向,以環境關心為倫理標桿,以環境友好行為為價值準心,激發中國居民全方位參與環境保護的行為。只有把行為變做習慣,把綠色意識融入身份認同,那么“人人參與,創建綠色家園”便不再只是愿景。
[1]占光.國際環境體制有效性與中國環境治理——以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為例[D].復旦大學,2010.
[2]楊超.關于我國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思考和建議[J].環境保護,2016(11):61-63.
[3]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綠皮書[EB/OL].http://www.tt65.net/zhuanti/zhishu/2007minshengzhishu/mydoc004.htm,2007-01-07.
[4]劉濤.“傳播環境”還是“環境傳播”?——環境傳播的學術起源與意義框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7):110-125.
[5]張威.環境新聞學的發展及其概念初探[J].新聞記者,2004(9):18-21.
[6]程少華.環境新聞的發展歷程[J].新聞大學,2004(2):78-81.
[7]Cox,R.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andPublicSphere[M].London:Sage,2006:12.
[8]李淑文.環境傳播的審視與展望——基于30年歷程的梳理[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0(8):39-42.
[9]劉濤.環境傳播的九大研究領域(1938-2007):話語、權力與政治的解讀視角[J].新聞大學,2009(4):97-104.
[10]于美娜.微博意見領袖的輿論影響力現狀及原因分析——以新浪微博環境傳播為例[J].現代傳播,2015(8):132-136.
[11]劉濤.接合實踐:環境傳播的修辭理論探析[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8-67.
[12]薛可,鄧元兵,余明陽.一個事件,兩種聲音:寧波PX事件的中英媒體網絡報道研究——以人民網和BBC中文網為例[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64-68.
[13]Leiserowitz,A.& Smith,N.KnowledgeofClimateChangeacrossGlobalWarming’sSixAmericas[M].New Haven,CT: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2010.
[14]黃河,劉琳琳.環境議題的傳播現狀與優化路徑——基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比較分析[J].國際新聞,2014(1):90-102.
[15]Brossard D.New Media Landscapes and the Science Information Consumer[J].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2013(suppl.3),Vol.110:14096-14101.
[16]Riley,D.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From Maginality to World Use[J].TheJournalofEnvironmentalEduaction,Vol.40,2008(1):3-18.
[17]Dietz,T.,Bringing Values and Deliberation to Science Communication[J].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Vol.110,2013(suppl.3):14081-14087.
[18]Potts,L.& Jones,D.Contextualizaing Experiences:Trac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Social Web[J].JournalofBusinessandTechnicalCommunication,Vol.25,2011(3):338-358.
[19]Wei,L.Filter Blogs VS Personal Journals: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Producation Gap on the Internet[J].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Vol.14,2009(3):532-558.
[20]陳力丹.把握新媒體對社會交往結構的影響——《互聯網時代的新聞傳播》序言[J].新聞愛好者,2013(2):82-83.
[21]李春雷,舒瑾涵.環境傳播下群體性事件中新媒體動員機制研究——基于昆明PX事件的實地調研[J].當代傳播,2015(1):50-54.
[22]羅艷菊,張冬,黃宇.城市居民環境友好行為意向形成機制的性別差異[J].經濟地理,2012(9):74-79.
[23]Blocker,J.& Eckberg,D.GenderandEnvironmentalism:Resultsfromthe1993GeneralSocialSurvey[M].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97:78.
[24]Stern,C.TowardA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J].JournalofSocialIssues,2000,56(3):407-424.
[25]Riley,D.& Jones,R.EnvironmentalConcern:ConceptualandMeasurementIssues[M].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2002:482-524.
[26]Schultz,P.& Zelezny,P.Values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 Five-country Survey[J].JournalofCross-CulturalPsychology,1998(29):540-558.
[27]Clare D.et al.The Moral Appeal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The Implication of Ethical Rhetorics[J].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2012(2):212-232.
[28]賈廣惠.中國環境新聞傳播30年:回顧與展望[J].中州學刊,2014(6):168-172.
[29]賈賀鵬,劉立,王大鵬,任安波.科學傳播的科學——科學傳播研究的新階段[J].科學學研究,2015(3):332-336.
[30]Beck,U.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M].New Delhi:Sage,1992:28-30.
[31]Christian,K.ThePsychologyofPro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BeyondStandardInformationStrategies[M].London,UK:Palgrave Macmillan,2015:89.
[32]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14.
[33]林瀚,童兵.新聞傳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互動及環境新聞工作者的責任[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6):44-48.
[責任編輯:趙曉蘭]
沈珺,女,助理研究員,博士。(浙江大學 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浙江 杭州,310028)
G206
:A
:1008-6552(2017)03-00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