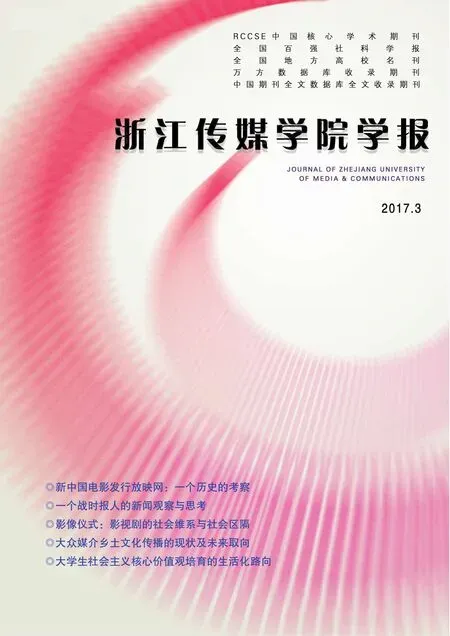大眾媒介鄉土文化傳播的現狀及未來取向
——基于浙江文化禮堂儀式報道的樣本分析
習少穎
大眾媒介鄉土文化傳播的現狀及未來取向
——基于浙江文化禮堂儀式報道的樣本分析
習少穎
近三十年來,中國鄉土文化在城市化進程中受到明顯沖擊,作為鄉土文化保存較為完整的浙江省同樣面臨這一困境。文章以浙江媒體在報道文化禮堂中的禮儀活動新聞為分析樣本,提出大眾媒介對鄉土文化的傳播面臨外力與內生、統一與個性、現代與傳統的三對現實關系,建議在未來的傳播取向上突出鄉土文化生產的內生力量,鼓勵本土的原生儀式傳播,并強化培育現代國家及公民意識的現代禮儀傳播。
鄉土文化;儀式;文化禮堂;日常生活
近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猛,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與之相伴的,則是傳統鄉村經濟凋敝,人口空巢化嚴重,村民生活單調,社會松散無序。因為這種現代化以城市、市民為核心,相對忽略和沖擊了鄉土文化的存在基礎,其中包括人口流動性遷移導致文化傳承缺乏對象,經濟凋敝帶來鄉土文化傳播缺乏經濟基礎,村落破敗致使作為日常生活的鄉土文化失去生存環境等。這一現象即使在鄉村經濟相對較為發達、鄉土文化保存較為完整的浙江省也不例外。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2016年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居全國前三位;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066∶1,是全國均衡性發展最好的省份。但鄉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對城市居民來說,顯得單調和貧乏。2007年浙江省首次發布農民文化生活調查,顯示農民最期待村文化活動場所具有的5項功能分別是:健身鍛煉、圖書閱讀、科技培訓、觀看戲曲和棋牌娛樂。農民內在的文化需求排在前五位的是:電影放映、地方戲劇演出、歌舞演出、圖書上門和文藝輔導培訓。調查表明富起來的鄉村居民對精神產品十分渴求。
中國傳統文化的起源即在鄉村和鄉土,鄉土文化的衰落和鄉村精神生活的空虛現象受到各級政府的關注。2012年至2016年間,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文化部等先后公布了4批共4153個中國傳統村落名單,對這些中國傳統文化和農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實施保護。浙江省也從2011年起設立了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專項補助資金,2013年5月,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推進農村文化禮堂建設的意見》,確認未來5年內在全省行政村建成一大批集教學型、禮儀型、娛樂型于一體的農村文化禮堂1000家。截至2015年底,全省已建成4959家文化禮堂,其中一些是在舊祠堂、閑置校舍、老廠房等的基礎上修繕改擴建而成的。為推進這項工作,浙江省每年都要召開現場總結會,并通過大眾媒體傳播文化禮堂的建設情況,最終目的是讓農民在“身有所棲”后“心有所寄”,實現傳承優秀文化、弘揚文明鄉風、培育農民素養等社會目標。這項對鄉土文化的培植和傳播工作,在全國都走在前列。因此本文認為選擇浙江省的文化禮堂作為研究鄉土文化傳播的載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同時,為研究大眾媒介傳播鄉土文化的現狀,本文選擇了浙江省最大的新媒體——浙江在線為數據來源。一方面浙江在線作為省級媒介機構,在刊載文化禮堂相關報道的數量、范圍上最為全面,另一方面因其同時集納了報紙、網頁、微信、手機客戶端等多種傳播平臺,在新聞表現形式上也最為全面。本文的數據分析時段為2013—2016年,即文化禮堂開始建設至今的4個整年度。
一、基本概念:鄉土文化傳播,儀式,文化禮堂
本文的鄉土文化傳播是指以傳播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為主要目的的傳播行為和傳播活動,其核心是對中國傳統鄉土文化的關切及傳承。傳播主體在人際傳播領域是鄉土文化傳播的實踐者(既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組織),在大眾傳播領域是大眾媒介。有學者從社會學角度,將文化定義為某一特殊社會生活方式的整體,由表層結構、深層結構和意義結構三層組成,并由此界定鄉土文化也可以劃分為鄉村物質文化、鄉村規范文化和鄉村表現文化三類。[1]筆者采納此種劃分,并將關注重點放在屬于鄉村規范文化的儀式活動部分,原因在于鄉土儀式活動既意味著生命的延續,也有文化記憶、群體規范的作用,是鄉土文化傳播中最有生命力和傳承性的部分。
儀式最初的普遍用意,在于宗教中的規范和程序。美國傳播學者羅森布爾在《儀式傳播》一書中認為,儀式是適當的規范行為的自愿表演,其象征性地影響和參與嚴肅生活,同時容納人類認為重要的、規范的所有象征行為。宗教的、世俗的儀式或禮儀活動都具有傳播特性,甚至是一種強效的傳播機制,因而儀式是維護社會秩序的人性化途徑,對人類共同生活很有必要。*轉引自劉建明.“傳播的儀式觀”與“儀式傳播”概念再辨析與樊水科商榷[J].國際新聞界.2013(4).從這個角度看,儀式的通常功用有利于人們對共同體的認同,有利于團體的精神和文化生存。因此也有學者認為,儀式是人類文化的核心及縮影。[2]首創傳播與儀式關系研究的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著作《詹姆斯·凱瑞:一個批判性讀者》中認為,人類社會其實充滿了混亂和偶然,在創造了文化之后,才得以實現秩序。而儀式在其中創造了社會關系形式,建構了通行的社會規則,通常被看作是一種標準化的、象征性的、由文化傳統規定的一整套行為規范。[3]
中國的諸多文化習俗特別是來自歷史傳承的文化儀式,是與巫術、宗教、道德觀念、生活習慣、地域特點等雜糅在一起的。中國鄉村文化乃至本土文化的傳統精神,便正是以此程序化的儀式繁衍下來。更多時候,人們將此種儀式統稱為民俗或傳統文化。錢穆先生曾十分精辟地指出:“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轉引自張志剛.錢穆的宗教觀與中西文化比較研究[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6).這個“禮”在鄉村的呈現,就是村民在鄉村生活的整個人生階段以及與其他村民交往時所涉及的各種禮儀。這種禮儀既有個人的也有建構社會關系的,即通常所說的禮尚往來。因此,本文認為要探討大眾媒介傳播鄉土文化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從基于各地習俗的鄉土儀式活動入手顯得十分必要。
二、大眾媒介對儀式活動的樣本呈現
學者陳力丹認為,新聞作為一種儀式,為人們提供了日常生活的秩序、調子和樣貌,其作用是對儀式承載的環節和內在思想、觀點、價值的確認。[4]這一概念與丹尼爾·戴揚對儀式研究的延伸——媒介事件的研究有相似之處。媒介事件理論中,事件的素材或腳本大致可劃分為“競賽”、“征服”、“加冕”三大類,它們決定著每一媒介事件內人物的角色分配及其扮演的方式。在其“加冕”儀式中,觀眾的角色變成與統治者或核心政府的重新協作、宣誓效忠、喚起社會的基本價值。[5]在媒介事件理論的“加冕”環節,主演和觀眾都要經歷分裂和重新進入,號召觀者參與、分享情感并表現出關心,其中包含強化價值的主題和大眾意識的主題。新聞對儀式本身的報道,就是一種潛在的規劃和秩序傳播。正如前文所說,鄉村凋敝不僅表現為經濟的衰敗,還體現為道德禮儀的沒落。因此,浙江省在2013年開始建設文化禮堂時,就定位為“教學型、禮儀型、娛樂型于一體”,禮儀活動成為三大設定任務之一,并在各地文化禮堂建設中成為日常運作內容,目的在于在傳播現代與傳統禮儀過程中,吸納更多人參與、接納、傳承儀式中的文化內涵,重建對鄉村社會的信心。浙江省委宣傳部為此專門編制了《文化禮堂操作手冊》,對鄉村政治與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禮儀進行專門指導和規范。
為探求大眾媒體對文化禮堂舉行的禮儀活動的傳播現狀,作者在浙江在線數據平臺輸入“文化禮堂”和“禮儀”兩個關鍵詞,搜索出266條符合規范新聞要求的樣本。篩除工作性、概括性及無實質內容等報道,共得到詳盡描述各地文化禮堂舉辦的禮儀活動的新聞樣本29篇,內容大致包括四類:(1)與人的生命周期有關的儀式:出生儀式、滿月賜名禮、啟蒙禮、成人禮、新婚儀式、重陽節敬茶禮;(2)與時令有關的儀式:送年儀式、清明祭祖、祭祖燈會等;(3)與地域或行業有關的儀式,如抲魚啟蒙禮、船模拜師禮、“謝龍王”禮儀、敬魚節、祭橘神、迎新人禮;(4)與現代國家治理有關的儀式:尊憲守法儀式、新兵入伍壯行禮。以單項禮儀統計,最多的是開蒙儀式,有8篇;其次是結婚、敬老、迎新人,各有3篇;再次是祭祖有2篇,最后是當地各種行業或地域儀式,各有一篇,共計8篇;與當代社會有關的禮儀如尊憲守法和新兵入伍壯行禮,各有1篇。
為更客觀準確地分析大眾媒介對鄉村禮儀傳播的現狀,作者使用谷尼輿情圖悅picdata.cn熱詞分析工具對樣本進行詞頻分析,得出排名前30位的熱詞結果,其中排名靠前的禮儀分別為:耕讀、敬老、守法、端午、新婚、迎新、新兵。

表1 浙江在線對鄉村禮儀傳播的詞頻分析
2015年,浙江省委組織部印制了《文化禮堂操作手冊》第四版禮儀活動指南,其中列出了指導推廣的15項禮儀:春節祈福迎新禮儀、婚禮禮儀、七歲開蒙禮儀、國慶禮儀暨成人禮、國家憲法日“尊憲守法”禮儀、端午節禮儀、嘗新禮儀、新人入村、拜壽禮、重陽敬老、崇德禮儀、新兵入伍“壯行”禮儀、拜師禮儀、耕讀禮儀、村干部就職禮儀。其中,加入新的流程或內容的傳統禮儀占11項,全新的現代禮儀有4項。筆者將官方指導禮儀與現實舉辦禮儀樣本進行對比,并結合樣本統計及詞頻分析,發現基于浙江在線的禮儀樣本呈現如下特點:
(1)從禮儀的類型看,與村民日常生活相關的禮儀成為文化禮堂舉辦儀式活動的主體。如開蒙禮的舉辦數量占全部樣本的27.5%,在單項禮儀中排名第一。8篇樣本都詳盡描述了啟蒙教育中的儀式,包括正衣冠、行拜師禮、朱砂啟智和開筆破蒙。本文分析此類儀式數量龐大的原因,一是兒童在中國家庭中的地位僅次于長者,是家族的希望;二是傳統鄉村教育的起源是分散的私塾,沒有宏大的受教育儀式,讀書與生活毗鄰而居。此種儀式不僅講讀書,也講做人,是謂知行合一。詞頻分析軟件結果也證實如結婚、敬老、迎新、祭祖等與人的生命周期相關的禮儀,在總樣本中占到相當份量。
(2)從禮儀的時代性看,現代禮儀樣本數量很少。如上文所述,浙江文化禮堂推薦的現代禮儀中,包括了國慶儀式、入伍壯行禮、憲法儀式和村干部入職儀式等。但在樣本統計中,偏向法治、理性、創新和國家觀念的現代禮儀只舉辦了尊憲守法和新兵入伍壯行禮2項,國慶儀式、村干部入職儀式的樣本為0。而強調長幼層級的開蒙、尊師、敬老、祭祖等儀式有13項,占到樣本總量的近一半。這顯示出現代禮儀進入鄉村的某種困境。
(3)從禮儀的文化特色看,各地禮儀的區域差異不明顯。在29個儀式樣本中,呈現行業或區域文化特色的樣本有8篇,在總樣本中比例偏小。如2014年4月24日報道《啟村民智 濃鄉鄰情 聚萬人心》的文化禮堂普陀樣本,介紹舟山市普陀區蝦峙鎮沙峧村作為遠近聞名的漁業村舉辦“抲魚啟蒙禮”,表現了海洋村落獨有的漁民之術和風俗文化。浙江在地理上地形多元,文化與語言也非常多樣,但在各地文化禮堂舉辦的禮儀活動卻顯得比較統一,缺乏個性。
三、大眾媒介傳播鄉土文化的現實問題與解決的路徑
進入大眾媒介報道范圍的內容選擇標準,既有政府的政治取向,媒介自身的選擇,也有村民的喜好。如前文所示,在今天鄉村人口減少的情況下,鄉土文化的傳播者除了村民、參觀者外,就是大眾媒介。而真正吸引人們了解、參與、傳播并推進傳統禮儀成為現代儀式,融合成為新文化的一部分,大眾媒介起到了主要作用。文化正藉由呈現人的生命周期、傳統的節日與祭奠儀式,通過大眾媒介的圖像與文字,以準制度化的程序演繹下去。這其中,有舊的框架和新的含義的融入,亦或直接有新的框架和新的內容加入,形成更符合當下社會價值觀和鄉村社會發展需求的新禮儀。基于這個考慮,本文對抽樣文本做了進一步的分析,發現鄉土文化傳播在大眾媒介報道中呈現出一些關系及取向,這對未來鄉土文化傳播至關重要,值得關注。
(一)外力與內生:進入日常生活的禮儀更有生命力,大眾媒介應關注鄉土文化的自我發掘和創造
樣本呈現的第一個明顯特點,就是與村民日常生活相關的儀式占到樣本數量的相當大的比重,這反映了大眾媒介在傳播鄉土文化中面對的第一對關系:外力與內生。鄉土文化的恢復或振興,不外乎本體創造和外來輸送。在文化禮堂這個新興的鄉村公共空間中,目前外部輸入的力量比較明顯,而自身發掘或創造的能力較弱。這既有現實中鄉村空心化的因素,也與政府慣性地認為鄉村民眾是弱勢群體,鄉土文化較城市文化落后等因素有關,因此大眾媒體介入鄉土文化傳播行為,也表現出一定的“傳”與“受”、上級和下級、先進與落后的二元關系。在本文最初抽樣的266篇文章中,有相當多的樣本呈現出這種關系。在現實調研中,也有一些村民表示,雖然喜歡各級政府機構“送文化”下鄉,但這類活動通常集中在特定時段如節假日,以至離開這個時段,本村的文化禮堂就會閑置。而對于“送文化”下鄉的被動等待狀態,也使得“送”下來的文化不能成為鄉土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本文的樣本選擇標準——詳盡表達鄉村禮儀的新聞報道——實施后篩選下來的29篇報道,無形中也反映了鄉土文化發展需要內生動力的規律。
例如其中有一篇描述滿月賜名禮的樣本新聞,詳盡陳述了由告祖、迎子、佩璋、賜名、指認、祈福、賀成、答謝、栽種等九個環節組成的完整儀式,蘊含了人們對新生命的美好祝愿,體現了家族對新生命的重視。而另一篇逢重大時節舉辦的祭祖儀式,程序繁雜精巧,還結合了民間廟會的傳統。如衢州市龍游縣大公村紀念徐偃王的清明祭祖燈會已有四百多年歷史,祭祀徐偃王時,四鄉八村以社為單位,龍燈、花燈、舞獅、走馬燈、采茶燈、高蹺、十番鑼鼓等爭奇斗艷,歌舞達旦,既熟絡鄉里關系,又凝聚家庭人心,同時也顯示家族或區域興旺,成為一年一度的盛會。這些受村民喜歡的居家生活式的儀式,經由大眾媒介報道,呈現出與村莊和村民共同成長的鮮活樣貌,既是娛樂也是共同文化的體現。
筆者認為,鄉土文化本就是一種活的日常狀態,不是也不應該是博物館里的文物或商業活動的表演。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在文化層面上大多呈現出市民、城市為中心—鄉村、農民為邊緣的文化傳導模式,鄉俗民風成為被教育和改進的對象。但鄉村的空巢化狀態并不意味著鄉村缺乏文化,而是鄉村文化不同于城市文化的類型。浙江文化禮堂實踐啟用了鄉賢、“文化能人”等鄉村意見領袖,發掘和恢復了區域文化,并在禮儀傳播中體現其凝聚和帶動作用,但在現實操作中,村落鄉土文化的自我創造和發掘能力還遠遠不夠。從這個角度看,大眾媒介在未來報道中對如何引導和強化鄉土文化內生的創造力,仍有巨大的挖掘空間。
(二)統一與個性:特定儀式成為“稀罕”物,大眾媒介要關注鄉土文化的個案與特殊性
浙江文化禮堂建設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夯實農村文化建設基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摘自2013年5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農村文化禮堂建設的意見》.因此從政府的角度而言,活動舉辦的最終目的是國家層面的統一價值觀傳播,表現為《文化禮堂操作手冊》每年都會及時更新,以便和中央保持一致。但這些統一推行的禮儀如果都強制成為鄉村禮儀的標準,就會使文化本身失去活力。從本文的分析樣本看,真正原生態的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禮儀,在總量上并不多,但恰是這些當地獨有的禮儀,因延續了區域文化內涵,強化了區域社會認同,而受到當地村民的歡迎。這一現象顯示出大眾媒介在傳播鄉土文化的統一與個性關系上,仍需在有特殊性的個案上著力。
如下述樣本的禮儀呈現,在大眾媒介報道中就比較少有,也是鄉土文化禮儀的珍貴遺存。2014年1月28日《東沙文化禮堂演繹“送年”習俗》的報道,介紹了舟山市岱山縣東沙鎮東沙社區的送年儀式,“廿三祭灶,廿四撣塵,廿五廿六搡點心(年糕),廿七廿八謝年神,除夕團圓守歲人。”新聞詳述了現場如何擺設桌椅,放置菜品內容,具體的送年儀式程序、動作等。“三拜九叩是以前最高的一種禮儀。儀式前后都要放鞭炮,代表‘請神’和‘送神’的意思。”2013年12月6日報道的《姜衙,傳承崇學向善的禮儀之村》,描寫了金華市婺城區竹馬鄉姜衙村對新生兒、嫁娶新人等村落新成員的歡迎禮儀,體現了非常豐富的文化記憶和集體認同感。其儀式包括為新生嬰兒手腕系上紅絲帶,追隨姻緣想要扎根村落的人必須將家鄉的土壤與本地水混合,再澆于村中“樟樹娘”的腳下,還要在村中長輩指點下誦讀村規,表示真正融入當地人的亙古秩序。
學者柯文在有關中國研究問題上建議:“應當把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于掌握的單位”。*轉引自邵培仁,王昀.本土化方法革新:一種認知傳播視角的回應[J].現代傳播.2016(5).這樣的研究意識同樣適用于大眾媒介對鄉土文化的傳播。如今的本土是一種開放的空間,而本土文化若要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得更遠,必然要思考如何能貢獻被世界所進一步接納的文化命題。大眾媒介對鄉土文化的傳播,也要在尋求宏大敘事,傳達國家、民族觀念的同時,認真思考如何不遮蔽地方文化的特性,在推進統一意識的同時凸顯地方文化的個性,從而協調并推進文化共同體與本土認知的共處關系。在實踐操作層面,筆者認為大眾媒介在傳播政府指導的儀式活動的同時,應更多地突出報道本村落原汁原味的個性化禮儀,重建農民作為當地儀式傳播的主角地位。這既保證了文化的多樣性,也強調了鄉土文化的自主性。
(三)現代與傳統:現代禮儀嚴重缺乏,大眾媒介在傳導新觀念上仍任重道遠
樣本分析的第三個特點是現代禮儀的嚴重缺乏。現代鄉村的秩序重建,不僅要鞏固傳統秩序傳統儀式以吸納人心,還要加入新的社會治理儀式,以適應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在現實操作中,強調公民的國家意識、社會責任及法制、理性、科學觀念的禮儀,因與鄉村靠自治完成的鄉村治理方式及村民日常生活完全不同,在文化禮堂活動中比較少見。如以2014年11月30日報道的臺州市路橋區新橋村《“尊憲守法”禮儀活動進新橋村文化禮堂》為例,區及村兩級行政官員組織村民在文化禮堂中完成了公開朗讀憲法、鄭重分發憲法讀本、根據憲法修改村規民約等儀式流程,儀式中,無論村民作為參與者還是旁觀者,都無形中加強了對憲法及相關法律的認識。儀式同時還是青年村民的成人禮儀,參與的青年表達了跨過青年進入成年及成為守法公民的價值認同。但是這樣的現代禮儀在研究的樣本中卻非常稀少。
學者梁漱溟曾指出,中國社會有家、國兩個層面,中間并沒有宗教、種族、工業或農業社團等集體存在,談家太小,談國太大,所以“中國人的自私,正因其太公,正因其沒有較大范圍的團體,所以絕培養不出他的公共觀念”。[6]學者馬良燦將當前中國鄉村社會治理形態分析為“鄉政村治”,即傳統的村治被融匯到鄉政中,基層政權的利益共謀引發了新的治理危機,解決方案是將農民社會權利置于鄉村治理的核心,通過社區組織建設,實現國家治權與鄉村治權間的協商共治。[7]無論是鄉土文化的禮俗還是鄉村治理的危機,都傳遞了一種現實,即鄉土文化要實現新的發展和延續,必須通過包括大眾媒介在內的一定外力來強化新觀念的引入和刺激,引導村民對現代觀念包括公民意識、法制社會、科學與理性精神等的認同。文化禮堂作為現實的生活公共空間,可以通過大眾媒介對現代觀念的儀式化傳播,實現鄉村的人情風俗與現代社會規制的漸進式融合和互為規范。費孝通先生曾指出,“有形的事實是鄉村,無形的道理是理性。這兩個地方,原來就是中國社會的根,除此外都不算。”[6](117)只有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現代化的東西才能“下鄉”。
四、結 語
對于文化禮堂的關注源于筆者在浙江省委宣傳部為期一年的社會實踐,筆者出于理論應對現實社會有所關照的研究宗旨對這一課題進行了調研,發現雖然文化禮堂是作為政府的一項惠民工程和執政任務在推進,但現實中鄉土文化傳播也確實需要一定的外力扶持和刺激。本文通過抽樣量化分析得出大眾媒介對浙江省鄉土文化傳播呈現出的一些共性特點和問題表明,鄉村日常生活禮儀成為文化禮堂舉辦活動的主體,具備本土特色的傳統儀式雖有但不多,傳遞現代社會法治和理性觀念的新式禮儀明顯缺乏。為此,建議大眾媒介應推進鄉土文化生產的內生力量,鼓勵本土的原生儀式傳播,強化培育現代國家及公民意識的現代禮儀傳播,以實現中國鄉土文化的重生和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1]胡映蘭.論鄉土文化的變遷[J].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2013(6).
[2]閏伊默.“禮物”:儀式傳播與認同[J].國際新聞界,2009(4).
[3]劉建明,徐開彬.“儀式”作為傳播的隱喻之原因探析[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7).
[4]陳力丹.傳播是一種信息傳遞,還是一種儀式?[J].國際新聞界,2008(8).
[5]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麻爭旗.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41.
[6]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82.
[7]馬良燦.中國鄉村社會治理的四次轉型[J].學習與探索,2014(9).
[責任編輯:詹小路]
習少穎,女,主任記者,文學博士。(浙江傳媒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浙江 杭州,310018)
G206.3
:A
:1008-6552(2017)03-009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