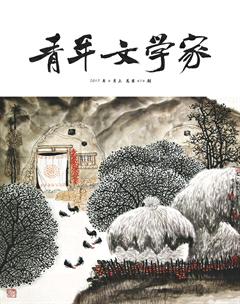孤獨的本能
周凡琪
總是有人把孤獨和寂寞等同,落單時腦海里便浮現出這兩個詞,頓時多愁善感起來。周國平曾說:“無聊、寂寞、孤獨是三種不同的心境。庸人無聊,天才孤獨,人人都有寂寞的時光”。其實孤獨與寂寞本是一對反義詞,孤獨促人離群索居,寂寞則讓人渴望融合與親近。人人都會感到寂寞,可鮮有人認為自己孤獨。
但其實每個人都是孤獨的。
站在城市最高的塔樓上往下看,各個路口,街道上的人們,他們總是三五成群,手挽手共同前行,一些善良的人們聚在一起,周圍的空氣會變得溫暖融合。他們可以分享昨夜的流星雨,晨曦里的滿月,或者在街角某家小餐廳的玉米濃湯,但他們一定不會聊到童年時在銀河下瞥到的淡綠色的星星,不會分享月亮在他們心里引起的潮汐或是多年前母親親手端出一碗蛋羹時眼里的溫柔。極致的美好,是無法分享的,也許是因為美麗到無法言表,也許是因為喜歡到只想私有。
小時候我們總是想擁有許多朋友,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講給他們聽,和他們分享自己的彩色蠟筆,慢慢才發現,在“分享”之后,你的美麗仍是你的美麗,你的哀愁也仍是你的哀愁。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寫道:“在世間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各自關在青銅塔里,只能打手勢與同類溝通,但各有各的打法,手勢的含義模糊不定。我們可憐巴巴想把自己內心的珍貴想法,傳達給別人,對方卻沒有能力接受。我們只好孤獨前行,肩并肩卻不是同伴,既不能理解旁人,也不能為旁人理解”。這也正是為什么我們與人同行卻沒有知己,常常傾訴卻不懂得傾聽。
這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莫過于“閱讀理解”和“藝術賞析”,我們不是馬爾克斯,怎么去解釋《百年孤獨》是對南美的影射?我們不是達·芬奇,憑什么斷言蒙娜麗莎的笑意中蘊含的是柔情?文學與藝術只是一個窗口,每個人都只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或許創作者會在作品中吶喊,但我們永遠聽不清。
在生物教材中我們學到,細胞具有獨立的生命,但也是某一高層次生命體的一部分;劉易斯·托馬斯告訴我們,雖然螞蟻是生物,但它們也是隸屬于“蟻群”這一生命的一部分,“當他們聚成大群之后,彼此觸碰,交換信息,它們就成了一單個動物”,“當心這一點,這是種貶值,是個性的失落”。而我們呢?人類會不會因為隸屬于某個鋼筋水泥的社會體系,而成為機器上的一個齒輪呢?當我們被時代的潮流單一的教化,長者的勸誡推著前行時,我們的自我意識還值得信任嗎?
人是由動物性和靈性構成的,前者讓我們寂寞,而后者讓我們孤獨。孤獨是某種神秘的存在,只有高貴的人,才能真真切切地感知到它是具體的,但他們從不回避孤獨,因為孤獨會讓人成就真正的自己,在孤獨里,他們會“自洽”——一種圓潤愜意的平衡,這樣的人,不會被世界改變,不會隨波逐流,他們永遠是一個完美的個人,純凈而高貴,不是任何人的投影。
是的,分享是人的本能,因為我們渴望被認同,但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找到社會的歸屬感與認同,出眾者之所以出眾,就是因為在面對與他人相悖的念頭時,他們不是刻意改變自己去迎合多數人,而是保留自己的思緒。我想孤獨也是一種本能,一種離群索居的渴望,一種抽離世俗尋覓真我的趨向。世界上那些被人仰望的人,大多是孤獨的人,他們甚至不需要什么職業來限制他們,黑澤明不是導演,畢加索不是畫家,莫扎特不是音樂家,卡夫卡也不是小說家,他們只是他們,世界上只會有一個黑澤明,不需要任何標簽來定義,他們就已經足夠耀眼。
我們依然總是要詢問身邊的人:“你喜歡當水手嗎”?或者“你相信世界是由意大利面統治的嗎”?這類問題,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你就高興去吧,因為你又擁有了一個只屬于自己的小小秘密,抑或是一個固執可愛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