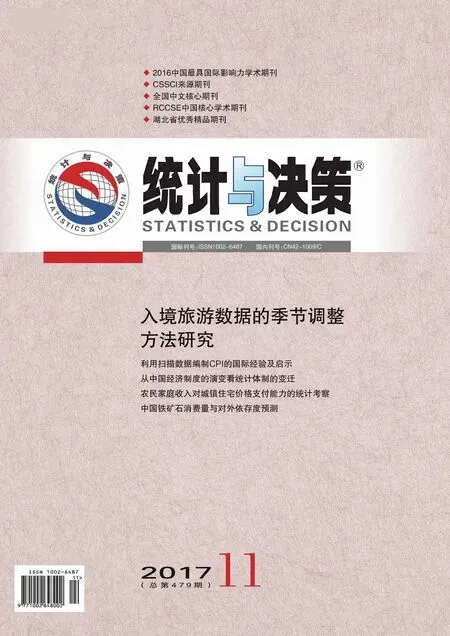基建投資績效與經濟增長集約化的溢出效應分析
艾麥提江·阿布都哈力克,白洋,b,鄧峰,卓乘風
(新疆大學a.經濟與管理學院;b.旅游學院,烏魯木齊830049)
基建投資績效與經濟增長集約化的溢出效應分析
艾麥提江·阿布都哈力克a,白洋a,b,鄧峰a,卓乘風a
(新疆大學a.經濟與管理學院;b.旅游學院,烏魯木齊830049)
文章借助DEA方法和空間杜賓模型,比較分析全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段沿線地區硬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及其對經濟增長集約化的空間效應。研究顯示:絲綢之路經濟帶硬性基礎設施投資處于較高的技術效率水平;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呈明顯的空間相關性;與全國比較,硬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對經濟帶的效應明顯,尤其是對西北地區產生的本地和溢出效應最大;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雖然明顯提高整個經濟帶的集約化水平,但對西北地區產生負向溢出效應。
絲綢之路經濟帶;集約化;基礎設施投資績效;空間效應
0 引言
2013 年我國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這雖然將為國內外沿線區域創造優勢互補的合作平臺,為資源的自由流轉、科教文衛事業等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但是,順利推進此戰略所需要的投入巨大,尤其是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所需要的投資要求很高。完善的基礎設施是加強國內外貿易合作、優化要素稟賦結構,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保障。鑒于此,近年來中央不斷增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尤其是高度關注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基礎設施的發展。雖然基礎設施投資作為政府資源配置機制,有利于擴大內需和區域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但是在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下,不僅要重視基礎設施的經濟增長作用,更要重視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充分發揮基礎設施投資效益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過程中的積極效應。
盡管國內外很多研究者分析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的重要意義,僅有少數學者研究其績效的經濟效應。尚未發現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對經濟增長集約化影響的相關文獻。鑒于此,本文擬選取全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段9省(市、自治區)西北5省區(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及西南4省區市(廣西、重慶、四川、云南)為研究對象,先采用DEA方法評價各地硬性和軟性基礎設施投資效益,再運用空間杜賓模型檢驗投資績效對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的本地效應和溢出效應。
1 數據和變量的選取
考慮到數據的統一性,本文選用2003—2014年全國30省(市、自治區)(除西藏外)、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9省(市、自治區)相關數據展開研究。相關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市、自治區)歷年統計年鑒。
被解釋變量:本文利用趙文軍等(2012)采用的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指標進行測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gq表示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gtfp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Eg為經濟增長的變化率,Gl和Gk用來反映勞動和資本的變化率,α和β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的產出彈性;借助公式及索羅剩余方法來測算出全要素生產率。利用張軍等(2004)的計算方法,確定α、β的值為0.3、0.7。Y表示總產出,即用實際GDP來表示(以2003年為基期利用各省區市歷年GDP折算指數進行調整)。L代表勞動力投入,即用年底全社會從業人員數表示。K代表物質資本存量,以公式進行測算,其中Kt表示t年的資本存量,表示t-1年的資本存量,表示當年的實際投資,表示t年的資本折舊,并根據張軍等(2004)的方法選取9.6%折舊率(以2003年為基期采用各地區固定資產價格指數進行折算)。
核心解釋變量:不同的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產生不同的作用機制。通過目前我國的硬性和軟性基礎設施比較可知,硬性基礎設施投資比率大于軟性基礎設施,短期內其對要素投人產生明顯的刺激,可對經濟質量的作用有限,長期將導致經濟增長更偏重于粗放型。相反,軟性基礎設施投資長期對經濟集約化產生的顯著的促進效應。因此,為了更清楚地估算基礎設施投資績效的影響,本文選取硬性(YJS)和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RJS)等兩個核心變量,并借助DEA方法計算得出的綜合技術效率來代替。
首先,將30個省(市、自治區)作為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的決策單元,選用硬性、軟性基礎設施投資實際資本存量作為投入指標。再次,為了更好反映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的發展、社會形態的變化發揮的重要作用,選取如表1所示的兩種產出指標。

表1 投入-產出指標
最后,用投入為導向的BCC模型分別計算全國各地歷年硬性、軟性基礎設施平均投資績效值,見圖1。

圖1 全國各地基礎設施投資平均績效
由圖1可知,上海的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青海、寧夏的硬性和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處于技術效率前沿面,反映出這些地區投資配置最合理,其對促進城鎮化和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作用很顯著;其他地區均具有較大的改進空間。尤其是四川,河南,河北,湖北等幾個省的投資績效不容樂觀。接下來,通過表2來對比分析全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硬性、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的變化歷程。

表2 硬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的變化
由表2可見,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硬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高于全國的平均績效,并且呈現逐步提升的勢態。而全國投資績效從2004年起快速下降,從2009年到2013年保持平穩趨勢,2014年略微上升;從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的演變來看,經濟帶沿線績效均高于全國,2003年開始逐步提高,2009年達到其峰值0.715后開始出現逐步下降的趨勢,而全國基本保持較穩定的演變趨勢。
其他控制變量:考慮所選取的影響經濟增長集約化指標的統一性和針對性,選取產業結構優化、對外開放度、外資技術溢出等三種變量。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能夠有效提升經濟發展速度,此外,通過調整各產業間的資源配置效率可提高經濟增長的集約化程度;對外貿易的不斷增加有利于資源的利用率和產品的競爭力,而引進跨國投資強化企業間的競爭,為國內企業創造學習先進外資技術的條件,使企業爭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而助推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本文選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表示產業結構優化程度,即將某地區三次產業由高向低排序,用公式計算,為產業產值;對外開放度(KF)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的比例來表示,其中美元對人民幣按當年的匯率折算;外資技術溢出(TI)以外資參與度來表示,即實際FDI與全社會固定投資的比重來衡量。
2 模型的設定
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會影響本地區經濟增長集約化,也會通過擴散效應進一步影響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方式。鑒于此,本文將空間因素納入模型中,并且選取更能清楚反映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對經濟增長集約化的直接和間接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展開分析,其基本公式為:

其中,Y、X分別表示因變量和外生自變量指標,ρ、γ是分別表示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的溢出效應和本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對鄰區經濟增長集約化的溢出效應,代表隨機干擾項,ε是殘差項,ε~N(0,,W是空間權重矩陣。將已選取的變量引入基本模型中,為減小共線性問題,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最終建立如下模型:

式中,K、C代表核心變量和控制變量,β1、β2、β3、β4為彈性系數,W為反映兩個地區之間“相鄰”程度的如下兩種權重矩陣:
(1)經濟距離空間權重矩陣(W1)

其中,Y0j表示j地區2003年的人均GDP,dij表示地理距離:
(2)地理空間鄰接權重矩陣(W2)

3 實證分析

式中,X、Xˉ用來表示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及其均值。Moran's I取值范圍[-1,1],如果其值越接近于1表示區域間存在較強的空間相關性,見表3。在不同的兩種空間權重矩陣下的Moran's I呈現全國及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存在明顯的空間依賴性。
本文用Moran's I指數來判斷區域間的空間依賴性度量,其基本公式如下:

表3 Moran's|、LR和Wald檢驗結果
通過對比LR、Wald檢驗值及其顯著性,進一步確定運用空間杜賓模型的合理性。根據豪斯曼檢驗值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見表4。

表4 空間杜賓模型檢驗結果
由表4可知,空間權重系數都為正且至少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可判斷區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具有顯著的積極溢出效應。如,模型1顯示,全國和經濟帶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變動的空間溢出效應系數為0.504、0.618、0.305、0.413,說明臨近區域間存在著示范效應,即本地受惠于外地所采取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舉措的積極溢出效應。
(1)硬性基建投資的績效對經濟增長集約化的本地效應均為正顯著,并且大于全國的效應,尤其是在模型1中對西南、西北的效應系數較大,分別為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的1.103、1.186;其溢出效應對經濟帶沿線地區產生較顯著的積極作用,如,在模型1中呈現系數為1.236的顯著作用,而對全國未能產生顯著的輻射效應。究其原因可能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大部分是欠發達地區,由于該地區硬性基礎設施相對不足,不斷擴大的投資有利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快勞動力、科技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流轉,從而使得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受惠于本省和外省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效益的積極影響。
(2)軟性基建投資的績效對整個經濟帶產生顯著的積極本地效應和溢出效應。比如,在模型2中,存在系數為0.356,在10%水平上顯著的本地效應,且在5%水平上顯著的0.638單位的正向溢出效應,超過其本地效應;但是,其對西南、西北地區經濟集約化存在逆向間接效應,彈性系數為顯著的-0.130、-0.522。究其原因可能是,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而言,軟性基礎設施的作用周期比較長且存在滯后效應,進而呈現虹吸效應;雖然其對全國引起不顯著的直接效應,但具有顯著的,系數分別為0.098、0.396左右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表明臨近區域通過擴散效應互動提升經濟增長集約化程度。
(3)控制變量中的產業結構對經濟帶沿線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產生較顯著的積極效應。如,由模型2可知,產業結構優化產生效應系數分別為顯著的0.613、0.502、0.885。在不同權重矩陣下,對全國彈性系數的顯著性存在差異。從其對西南地區產生的較大的積極溢出效應可知,在此區域內臨近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對本省經濟集約化具有示范效應,而在其他區域內存在不顯著的溢出效應或競爭效應;區域開放度,除了整個經濟帶的溢出效應外,未呈現積極的本地或溢出效應。如,在模型1中,開放度對全國和整個經濟帶經濟增長集約化的直接和間接效應系數分別為-0.178、-0.287和-489、0.550,均在10%水平下顯著。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國仍然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兩頭在外、中間在內”的貿易結構及引入的先進技術轉移有限等因素加劇經濟向粗放型發展;外資技術變化,除了模型2中對整個經濟帶和西北地區產生的負溢出效應外,顯著推動了區域經濟向集約型方向發展。這表明引進外資有利于緩解資本壓力,為企業創造提升生產技術水平和模仿學習的便利條件,加強企業快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實際能力。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2003—2014年的面板數據,采用DEA方法和空間杜賓模型,比較分析全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硬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及其對經濟增長集約化的直接和間接效應。結果表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硬性基礎設施投資呈現較高的技術效率水平;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之間存在著鮮明的空間依賴性;硬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對經濟帶沿線經濟增長集約化產生較大的影響,其中對西北地區的本地和外溢效應最明顯;軟性基礎設施投資績效雖然對整個經濟帶集約化水平呈現促進效應,但西北地區產生消極溢出效應;產業結構具有正向直接效應,但對整個經濟帶產生逆向或不顯著的溢出效應;開放度均具有抑制影響;外資技術溢出基本呈現正向直接和間接效應,尤其是對西南地區的外溢效應較顯著。
目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基礎設施薄弱仍然是制約轉型該區域經濟發展的短板之一。因此,在供給側改革協調作用下,有機結合區域經濟發展集約化趨勢,對投入力度實施有針對性的調整,著重提升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績效;促進西北、西南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地理空間聯系與互動,更加完善與合理化鏈接彼此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其在轉型經濟發展的輻射效應。充分發揮西北、西南地區的區位優勢,為加強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外沿線區域之間的全方位合作、交流和貿易提供便利條件。
[1]Aschauer D A.Public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Group of Seven[J].Economic Perspectives,1989,13,(9).
[2]Jeffery C P,Catherine M P.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Inter-State Spatial Spillovers,and Manufacturing Cost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4,86,(2).
[3]Thoung C,Tyler P,Beaven R.Estim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Infrastructure to National Productivity in Europe[J].Infrastructure Complexity,2015,(12).
[4]Roy A G.Evidenc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ment Size[J].Applied Economics,2009,41,(5).
[5]Anselin L,Rey S.Properties of Test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i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J].Geographical Analysis,1991,(23).
[6]徐智鵬.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J].統計與決策, 2013,(21).
[7]吳福象,沈浩平.新型城鎮化、基礎設施空間溢出與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基于長三角城市群16個核心城市的實證分析[J].財經科學,2013,(7).
[8]沈春苗,董梅生,陳東.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偏向與經濟增長[J].上海經濟研究,2015,(3).
[9]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
[10]郭慶旺,賈俊雪.政府公共資本投資的長期經濟增長效應[J].經濟研究,2006,(7).
[11]趙文軍,于津平.貿易開放、FDI與我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基于30個工業行業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12,(8).
(責任編輯/浩天)
F062.6
A
1002-6487(2017)11-0124-0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06JJD80009);新疆創新管理研究中心基地招標項目(202-61098);新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絲路》基金項目
艾麥提江·阿布都哈力克(1985—),男,新疆喀什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經濟學。白洋(1982—),男,新疆鄯善人,博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旅游經濟學。(通訊作者)鄧峰(1970—),男,湖北黃陂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西方經濟學。卓乘風(1991—),男,湖北安陸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術經濟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