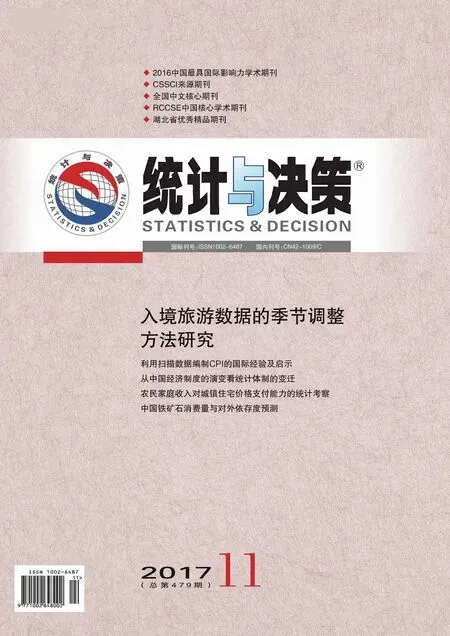我國制造業技術創新效率分析
任冶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南京210023)
我國制造業技術創新效率分析
任冶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南京210023)
文章運用DEA及Malmquist方法,以我國2011—2015年15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技術創新數據為樣本,測算了該行業技術創新的效率。研究表明:我國汽車制造業技術創新效率仍處于較低水平,且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動態看,我國汽車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呈“增長—下降”趨向,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來自于技術進步的驅動,而技術效率惡化卻造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
DEA;Malmquist;創新績效;技術創新效率
0 引言
我國已建成全球門類最為齊全的完整工業體系,取得了制造業第一大國的地位。但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存在核心技術缺失、高端產品依賴進口受制于人、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由此,《中國制造2025》更加突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篇把創新作為核心競爭力。在制造強國建設“三步走”戰略中,創新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把創新擺在制造業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力爭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等重要、關鍵領域,集中突破一批基礎共性和核心關鍵技術,重塑工業轉型發展新引擎。技術創新成為中國制造業未來發展的重要出路,企業是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的重要力量,應該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的主體。那么,怎樣提高制造業技術創新效率、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入快車道?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緊迫課題。
1 指標選取與方法設定
1.1 指標選取
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是技術創新投入最主要的兩個方面。本文使用R&D經費和R&D人員數兩個指標作為技術創新投入的指標。有關技術創新活動的投入,最常用指標為專利申請數和新產品銷售收入[1-4]。其中,新產品銷售收入大多來自于國家相關部門發布的針對行業或地區的專項統計報告。但對于針對微觀層面的上市公司來說,新產品銷售收入涉及企業機密,樣本公司的年報中一般不會單獨公布,這一指標的微觀層面的數據難以獲得,專利作為技術創新成果的結晶,可以直接的體現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產出水平,企業專利申請的相關數據可以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很方便的查詢獲得。因此,考慮到數據科學性和可得性,本文選取專利申請數作為技術創新產出的衡量指標。其中,一級指標包括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創新投入的二級指標包括R&D經費支出(萬元)、R&D人員數(人),創新產出的二級指標為專利申請數(件)。
1.2 研究方法選擇
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是基于Farrell的效率理論,由Cooper和Rhodes(1978)[5]發展起來的線性規劃方法。DEA基本原理主要是通過保持決策單元(DUM)的輸入或者輸入不變,借助于數學規劃方法確定相對有效的生產前沿面,將各個決策單元投影到生產前沿面上,并通過比較決策單元偏離前沿面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其基本模型主要有投入主導型的規模不變CCR模型和規模可變BCC模型兩種。本文采用BCC模型來測度效率。設決策單元有n個:DMUj(j=1,2,...,n),每個DMU,包含m種輸入,s種輸出,輸入輸出向量分別為分別表示第j個決策單元DMUj第i種類型輸入的投入量和第r種類型輸出的輸出量,λi為為權系數,其對應的輸入、輸出數據分別為:基于輸入的帶有非阿基米德無窮小的BCC模型可表示為:

Malmquist指數最初由Malmquist于1953年提出[6],Caves等于1982年開始將這一指數應用于生產效率變化的測算,Fare[7]證明Malmquist指數可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化指數(TE)和技術進步變化指數(TC),而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又能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PTEC和規模效率變化指數(SC)。從t到t+1期的Malmquist效率變化指數具體分解形式可表示為:

TE測度從t至t+1期決策單元到最佳生產前沿面的距離變化情況,被稱作“追趕效應”,當TE>1時,說明決策單元的生產更接近生產前沿面,相對技術效率有所增加;TC測度技術前沿從t到t+1期的移動情況,被稱作“增長效應”,當TC>1時,表明技術出現進步,生產前沿面向“上”移動。
本文以滬深兩市上市的汽車制造行業公司為研究對象。樣本的選取主要遵循以下原則:(1)剔除上市年較短的公司。本文研究跨度為2011—2015年,若為2011年以后上市,則將該公司將剔除。(2)剔除數據不完整的公司。出于統計分析的必要,剔除有任何數據缺失的公司。(3)剔除ST、ST*類的公司。因為這些公司處于財務狀況異常的情況,會影響測算結果的正確性。最終整理出15家具有代表性的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共75個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上市公司的年報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
2 實證分析

表1 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技術創新效率測度結果
2.1 DEA靜態分析
本文基于DEA方法的BCC模型,利用DEAP2.1軟件對2011—2015年15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樣本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測算,其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
表1展示了2011—2015年15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樣本的技術效率及其分解的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可看出總體上技術效率偏低,有的企業在某些年份的技術效率值達到了0.8以上,甚至1,這些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較高投入產出效率(安凱客車,2012—2015年;精鍛科技,2011—2012年;江淮汽車,2013—2015年等),還有企業在某些年份效率值尚不足0.2,說明技術效率有待提高(萬向錢潮,2011—2015年;凌云股份,2011—2015年等)。再從分解的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來看,某些企業在某些年份的純技術效率值為1,表明此企業在這期在變動規模報酬條件下、在現有投入水平下均獲得了最大產出(精鍛科技,2011—2013年;比亞迪,2011—2012年;安凱客車,2012—2015年等),在規模效率方面,某些企業在某些年份的規模效率為1(精鍛科技,2011—2012年;安凱客車,2012年,2014—2015年等),表現出良好的規模經濟性。從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的比較來看,基本上純技術效率均低于規模效率,由此可見,相對于規模效率,制約中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技術創新效率整體提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純技術效率較低所致。純技術效率的經濟內涵主要表現在規則制度及管理水平等方面。近年來,伴隨著對制造業研發資源投入的不斷增加,創新規模在不斷擴大,但由于缺乏科學的制度安排及管理水平的落后,使得純技術效率無法提高,進而制約了技術創新的有效發展。由此也啟示,今后中國制造企業技術創新模式需加以轉變,應打破傳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改變過去單純依靠擴大規模的粗放發展模式,通過制度變革與管理創新,使其向制度科學型和管理有效型方向發展,并以此推動整個制造業技術創新效率的全面提升。
為了更加清晰地描述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均值隨時間變化的情況,繪制了歷年技術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均值的時間趨勢圖,如圖1所示。

圖1 歷年技術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均值時間趨勢
由圖1可看出技術效率均值從2011—2012年基本保持不變,從2011年的0.392到2011年的最高值0.393,此后逐年下降,規模效率均值歷年一直保持平穩,圍繞0.65上下徘徊,波動不大,有上升趨勢,純技術效率均值則呈現出先上升再下降的過程,從2011年的0.623到2012年的0.670,此后逐年下降的趨勢,特別是在2012年后,純技術效率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但規模效率卻在逐步提高,也意味著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創新規模不斷擴大,使得規模效率得到充分釋放,規模經濟性逐步得到提高,但相應的制度安排和管理創新并沒有及時跟上,發展滯后。上述結果說明,我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技術創新效率發展基本呈現一種規模拉動型的發展,管理水平和制度安排還有待提高。
2.2 Malmquist動態分析
本文利用DEA模型的投入產出數據,采用Malmquist指數模型對15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在2011—2015年的技術創新效率變化進行分析,通過DEAP2.1軟件進行數據處理,結果如表2所示。

表22011 —2015年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Malmquist效率變化指數
如表2所示,如果各項指數大于1,表明當期該指數正增長,反之,負增長。考察期內技術進步變化全呈現正的增長態勢,表明技術是不斷進步的,但技術效率變化基本呈現負的增長態勢,除了2011—2012年技術效率正增長外,其余負增長,技術進步率大于技術效率變化率,這也表明中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技術創新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術進步。其次,進一步將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和規模效率變化指數,純技術效率變化2011—2012年和規模效率變化指數2012—2013年呈現正增長,其余各年呈現負的增長態勢,但純技術效率有不斷惡化,而規模效率有明顯改善的跡象,純技術效率不斷惡化,規模效率增幅不明顯,兩者綜合作用致使技術效率改善并不明顯,最終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無法提高。因此,我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要想提高技術創新的效率,必須轉變僅僅依靠規模擴大的粗放增長方式,需要在制度建設及管理創新上有所作為。
3 結論
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1)我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技術創新效率整體水平偏低,效率均值在2011年達到最高值0.4,此后逐年下降,不同的企業和年份之間的技術創新效率差距很大,有的企業在某些年份的技術效率值達到了0.9以上,甚至1,而有的企業在某些年份效率值尚不足0.1,說明其技術創新水平有待提高。
(2)純技術效率均低于規模效率,由此可見,相對于規模效率,制約中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技術創新效率整體提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純技術效率較低所致,其創新效率發展基本呈現一種規模拉動型的發展,管理水平和制度安排還有待提高。
(3)我國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技術進步對于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貢獻較大,效率增長主要源自于技術進步的驅動,純技術效率有惡化趨向,規模效率增幅不明顯,兩者綜合作用致使技術效率改善并不明顯,最終導致總體效率低下。
[1]劉俊杰,傅毓維.基于DEA方法的高技術企業創新效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3).
[2]薛娜,趙曙東.基于DEA的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評價——以江蘇省為例[J].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研究,2007,(5).
[3]吳瑛,楊宏進.基于R&D存量的高技術產業科技資源配置效率[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6,(9).
[4]魏芳,趙玉林.我國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實證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8,(8).
[5]A,Cooper W W,Rhodes E.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78,2,(6).
[6]Malmquist S.Number and Indifference Surfaces[J].Trabajos de Estatistica,1953,(4).
[7]Fare R,Grosskopf S,Norris M,et al.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1).
(責任編輯/浩天)
F062.4
A
1002-6487(2017)11-0140-0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6BGL039)
任冶(1987—),男,安徽蕪湖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術創新與效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