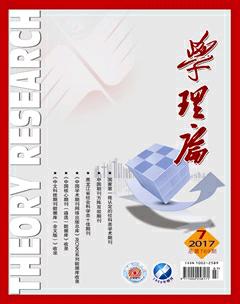整體世界史觀與“一帶一路”
劉彩紅
(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武漢 430072)
摘 要:吳于廑先生的整體世界史觀認為世界歷史的內容為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世界成一密切聯系整體的過程,包括橫向發展與縱向發展兩方面,從世界整體全局的角度來分析、探討、闡述世界歷史及其演變的規律。21世紀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是對古代絲綢之路精神的繼承和發揚,而且是順應時代背景的應有之義,從整體世界史觀來看,“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是符合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
關鍵詞:整體世界史觀;“一帶一路”;發展;開放;和平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07-0161-02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1]。同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又在印度尼西亞國會大廈演講時提出了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絲綢之路”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為起點,經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穿過中亞和西亞,最終抵達歐洲的貿易通道”[3],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最初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其命名為“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引起了國內外研究的熱潮。本文以吳于廑先生的整體世界史觀來論述“一帶一路”,闡明“一帶一路”是符合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
一、世界歷史的橫縱向發展與“一帶一路”
整體世界史觀認為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兩個方面。縱向發展是指人類物質生產史上不同生活方式的演變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會形態的更迭,橫向發展是指歷史由各地區間的相互閉塞到逐步開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聯系密切,終于發展成為整體的世界歷史的過程。而推動世界歷史橫向發展與縱向發展的最根本因素是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在物質生產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人們對新地區的開拓,與相鄰地區的交換和交往,必然不斷擴大[4]。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發展迅速,綜合國力得到巨大提高,擁有“投融資建設所需的強大的資金和制度支持(如規模龐大的外匯儲備、自主設立的絲路基金、亞投行等)、過硬的基建技術(如高鐵、港口、橋梁等)”[5],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其經濟總體上都處于上升期,物質生產條件也相對成熟。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奠定了“一帶一路”實行的物質基礎,這是對整體世界史觀的一種詮釋。
整體世界史觀中,世界歷史的發展是一種由點及線、由線到面的的發展過程。“一帶一路”戰略也遵循了這樣一種路徑。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根據“一帶一路”走向,陸上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6]。“一帶一路”所體現的點線面體的這種漸進立體的全方位的格局也是對整體世界史觀的體現。與其他地區進行聯系也是必要的,因為“橫向發展一方面雖然受到縱向發展的制約,但是對縱向發展也具有反作用。橫向發展與一定階段的縱向發展相適應,就往往能促進和深化縱向發展”,如我國的改革開放,如果一個地區缺少與其他地區的橫向聯系,其縱向發展必然遲滯。如日本歷史上曾實行的海禁政策就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整體世界史觀也闡明了人類歷史發展并不平衡,無論是中國內部各地區還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均是如此,從我國來說,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高,勞動力、資本等密集,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人均收入、生活水平等相對緩慢,從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說,“沿線國家由于受到基礎設施缺乏等硬件條件與體制政策不完善等軟件條件制約,發展潛力未能得到充分釋放”[7]。中亞地區盡管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經濟發展卻一直不平穩,特別是基礎設施的匱乏,再加上恐怖主義的影響,與歐洲國家包括鄰近的俄羅斯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這些表明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緊密、實現共同繁榮的互惠互利“一帶一路”構想的價值和意義。
二、開放交往與“一帶一路”
開放交往與各地區的橫向聯系可以說是殊途同歸的。古絲綢之路各國的交往,從歷史發展來看,“其意義的重要不在于絲綢的轉運而在于有了這條通達的道路之后,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可以隨著時代的演進而絡繹往返”[4],開放與交往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如中國的四大發明的傳播正是由于各國間的相互交往和開放的心態才得以傳播與擴散,使更多的人分享文明成果。“一帶一路”構想強調“弘揚古絲綢之路和平友好、開放包容的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設計,不針對第三方,不經營勢力范圍,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線國家都可參與,是一項完全開放的合作倡議”[8]。“一帶一路”遵循開放包容的古絲綢之路精神。
世界歷史的發展表明閉關自守就會落后。例如明代中國、印度莫臥兒帝國、奧斯曼帝國雖盛極一時,但最后離繁盛漸行漸遠,它們衰落的一個共同因素就是保守,中國自不待言,奧斯曼帝國的“保守主義”大行其道,“印刷業遭到禁止,因為它或許會傳播危險的見解……出口被禁止”;莫臥兒帝國亦復如是,“絕對嚴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礙了現代化:嚙齒動物和昆蟲不許殺害,因此大量糧食受到損失……種姓制度扼殺了創新精神,逐漸灌輸了教義,并限制了市場”[9]。它們的保守封閉落后思想可見一斑,也說明開放與交往的重要性。我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是很好的例證,只有堅持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經濟,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而“一帶一路”戰略也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的發展,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堅持開放合作。我國西部地區通過“一帶一路”既可以加強西部地區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優勢互補與聯系交往,又能加強西部地區與中亞、西亞等地區的聯系,提高了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水平與能力。而對東部來說,其開放的范圍也擴大了,沿著整個海上絲綢之路,東部除了與內陸地區的深入交往外,交往范圍也擴大了,開始遍及東亞、東南亞、南亞等范圍更廣的沿線地區和國家。
整體世界史觀所證明的“孤立、閉塞必然造成文明的停滯”,而“閉塞狀態的打破有待于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交往的增多”[4]。“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的、促進各國和地區間交往增多與合作擴大以及讓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沿線各國人民的構想。
三、和平發展與“一帶一路”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歷,和平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現在和平與發展更是成為時代的主題。而“一帶一路”正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和平之路,在歷史上,“絲綢之路就是一條和平之路,如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大食、波斯和身毒等沿途國家的商人穿梭其間,和平共處……明代鄭和下西洋拜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10],我們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懷柔四方,傳播中華文明,而從來沒有實行過霸權,可西方的新航路開辟后,無論是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的伊比利亞擴張時代,還是荷蘭、法國、英國階段都伴隨著血與火、刀劍槍炮的暴力與血腥的掠奪與征服,除了奴隸貿易,還包括鴉片貿易,中國是深受其害的,殖民者掠奪殖民地的黃金白銀還有原料、市場,以致形成了殖民體系。“一帶一路”遵循著和平合作的絲綢之路精神,“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和諧包容。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兼容并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6]。
當前有國外一些學者質疑說中國的“一帶一路”既然是戰略,那么戰略總是帶有軍事的意味,說中國的這種構想是為了擴大中國的勢力范圍,并且對沖TPP等對中國的排斥等。但是人們深知殖民主義的危害,很多人的先輩深受其害,他們也擔心其他國家走殖民主義的老路。我國的“一帶一路”不是殖民主義,一帶一路”的戰略“不謀求主導權,是在原有合作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多領域合作,同時來妥善對大國的關系加以處理”。而且,“這一戰略并非只是著眼于中國發展,而是以中國發展作為契機來實現地區以及世界的和平發展,從而走新型的大國和平以及合作發展的戰略。‘一帶一路并不排斥有意愿參與的國家及地區,正如時殷弘教授所說,絲綢之路經濟帶“不需讓渡任何主權,也不會衍生軍事意義的戰略存在”[11]。“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一種經濟構想或者說倡議,而非軍事目的,世界歷史的發展也表明“如果一個國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資源不是用于創造財富而是用于軍事目的,那么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9]。
“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兼顧關切各方利益,讓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沿線各國人民,這種原則進一步體現了“一帶一路”是和平發展之路,是符合世界歷史整體發展向著和平道路發展的趨勢的,將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四、“歐洲中心論”不合理性與“一帶一路”
整體世界史觀毫無疑問是反對歐洲中心論的,歐洲中心論者是以歐洲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中心,他們用歐洲的價值觀念衡量世界。長期以來在史學界,歐洲中心論思想就占據主流地位,許多地區被忽視、被邊緣化,例如中亞地區,吳于廑先生從他的世界歷史全局觀點出發,認為“只要著眼于全局,治通史者就必然會更多地把這帶荒莽草原收入視野,肯定它在世界歷史發展中難以估計的作用”[12]。整體世界史觀從世界全局的角度出發,發現了曾被忽視的地區的價值。“絲綢之路經濟帶”便是肯定曾被邊緣化的中亞地區的價值,因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中中國經中亞的路線是重點之一。吳于廑先指出,“要超越國別史和地區史的視野,對若干涉及不同時代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重要課題進行綜合比較的宏觀研究”[13],“一帶一路”正是中國從宏觀的角度比較中國內部各地區,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等各地區和國家的各項要素之后所做出的全局性的與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構想。
在反對歐洲中心論的過程中,吳于廑先生指出,“一部新的世界史必須在兩個問題上區別于過去任何一種世界史:一是它必須體現世界歷史的一致性;二是它必須說明世界歷史由閉塞、非整體的發展到整體的發展”[14]。“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并不是只有中國在唱獨角戲,還有沿線各國的參與,這一構想既從全局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種交往與互動,又尊重各國和各地區的包括宗教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差異性,所以“一帶一路”是一種包容、共贏、互惠的構想,在整體發展的同時,尊重各國和地區的差異性,兼顧各方利益、求同存異。當然,不僅要擯棄歐洲中心論,也不應該有其他的中心論,“一帶一路”的框架路線、原則等都是對某某中心論的否定,而且從全局出發,求同存異,互利共贏,這是從整體世界史觀的角度出發,是符合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
五、結語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要發展就不能孤立、閉塞,必須融入世界經濟。“一帶一路”戰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是對時代發展潮流的適應,從整體世界史觀來說,和平發展、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共建共享的“一帶一路”戰略是符合世界歷史的橫縱向發展規律的。遵循世界歷史整體發展的趨勢,順應了時代潮流,是一種綜合考慮國內外環境下的合理構想。雖然會遇到各種挑戰,但是這種順應時代、和平發展、遵循歷史發展規律的戰略將會促進沿線國家的發展與進步以及中國自身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3-09-08.
[2]習近平.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3-10-04.
[3]李永全.思路列國志[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總社,2015.
[4]吳于廑.世界史(總序)[M]//吳于廑,齊世榮.世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李曉,李俊久.“一帶一路”與中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重構[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10):55.
[6]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N].人民日報,2015-03-29.
[7]盧鋒,李昕.為什么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邏輯[J].國際經濟評論,2015(3):30.
[8]金玲.“一帶一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J].國際問題研究,2015(1):91-92.
[9]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
[10]葛劍雄,胡鞍鋼,林毅夫,等.改變世界經濟地理的一帶一路[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11]時殷弘.“一帶一路”—祈愿審慎[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7):152.
[12]吳驍.吳于廑與斯塔夫里阿諾斯世界史觀之比較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05.
[13]陳志強.論吳于廑“整體世界史觀”[J].世界歷史,2013(2):53.
[14]吳于廑.時代和世界歷史—試論不同時代關于世界歷史中心的不同觀點[J].江漢學報,1964(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