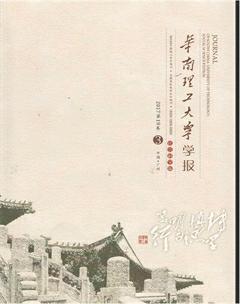需要保護即需要賦權:動物權利論的邏輯錯誤
摘要: 在動物權利學說的論證邏輯中,動物需要保護所以需要賦予其權利是極其重要的一點。一些西方學者試圖將權利作為解決傳統動物保護不力問題的口號與工具,一些國內學者則將生態保護作為支持動物權利的重要理由。但“需要保護”與“需要賦權”并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首先,需要保護并不等同于需要賦權;其次,動物需要保護也無法推導出動物需要賦權;最后,賦予動物權利不符合動物保護的客觀現狀與現實需求。所以,動物權利論“需要保護即需要賦權”的邏輯是錯誤的。
關鍵詞: 動物權利,邏輯錯誤,保護,賦權
中圖分類號: H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055X(2017)03-0026-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3010
近年來,隨著動物保護熱潮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提倡動物保護,甚至因為動物保護意見的不同而爆發了“玉林狗肉節”等群體性事件。在反思沖動與理性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動物保護已經不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道德考量,而是當今社會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一些學者以西方“動物權利”學說作為根基,提出通過法律途徑賦予動物權利;[1]也有一些學者以“動物無法滿足法律主體的必要條件”等理由反對賦予動物權利。[2]然而批判動物權利,并不能僅僅依靠法律教義學上的概念推演。動物權利本身是西方的一個倫理學概念,國內學者在論述自身的動物權利學說時對原學說既有繼承又有改變。批判動物權利應當既分辨兩者的差異又尋找兩者的共通點,并在此之上證偽“動物權利”。
一、原學說:更好的保護需要賦權
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歷史始終與動物為伴,對人與動物關系的思考古已有之。1824年,現代意義上第一個動物保護組織——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在英國成立。此后,很多國家都有了自己的動物保護團體。雖然參與此類團體者的口號和目標不盡相同,但基本都是以避免動物受到不必要的傷害為基本理念。
動物保護運動的興起雖然一定程度緩解了動物的處境,但許多動物保護激進主義者認為動物依然沒有真正受到人們的重視與正確對待。1975年彼得?辛格出版了《動物解放》一書,將人類對動物虐待的根本原因歸因于人類對動物的“物種歧視”,提出相應的解決方式是“平等對待原則”,用以論證“平等對待原則”的理由則是動物與人一樣具有感知痛苦能力。《動物解放》全書有超過一半的篇幅在描繪動物遭受屠宰、養殖、實驗以及虐待時所承受的痛苦,從而論證動物的確具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并論述動物正處于遭受痛苦虐待的境地。在這些論述中,辛格不僅僅批判了人類面對動物痛苦時的麻木不仁,更發出了一個重要的疑問:已有的動物保護(組織和理念)為何不能真正阻止人類對動物的虐待?辛格的回答是以往的動物保護者的邏輯——“對待動物殘忍的人也會同樣殘忍地對待同類”與“基于人類對動物的同情而保護動物”并不足以真正消除人類對動物的虐待,理由是前者的本質是對動物的歧視;后者則讓人誤以為正確對待動物僅僅是一種慈悲。[3]22-67
從動物解放所要求的具體內容來看,動物權利學說與以往的動物保護并無二致,即防止動物感受到人類施以的痛苦,包括禁止對動物的野蠻實驗,不違反動物天性的圈養動物,不虐待動物(閹割、烙印、電昏、死亡、強迫進食或禁食)以及素食。結合辛格對以往動物保護的批評可見,他并沒有在以往的動物保護之上提出新的善待動物的方式,而是試圖提出新的學說以克服以往動物保護不力的處境。批判物種歧視也好,提倡動物解放也罷,其實質是為了從觀念上與以往的動物保護邏輯相脫離,說服人類像對待嬰兒與殘疾人一樣正視動物感知痛苦的能力,真正實現“避免動物痛苦”這一動物保護的內容。
辛格并不否認以往動物保護的積極意義,但他認為單憑道德善心不足以實現真正的動物保護,他試圖尋找一種強制要求人類保護動物的手段。這一點與其他一些動物權利論者是相同的,加里·L·弗蘭西恩就將這種單憑道德善心是不足以實現真正的動物保護的情況命名為“關于動物的道德上的精神分裂癥”,認為人類往往在意識到需要保護動物的同時,依然實施著對動物的虐待。[4]78-80為了對抗人類的這種認知與行為的分裂,實現對動物更好、更徹底的保護,辛格、弗蘭西恩等動物權利論者提出平等對待原則。
而從平等對待原則推導到賦予動物權利,是因為辛格認為權利是平等原則最好的解釋。并且人們往往認為權利是專屬于人的,權利是回擊人類優先理念的最好口號。比照嬰兒以及殘疾人,他們往往與正常人具有顯著的能力區別,但他們依然享有與正常人一樣的被平等對待的權利,說明智力與能力的區別并不影響權利的獲得。在辛格看來,嬰兒或者殘疾人獲得權利并不是所謂的“固有尊嚴”或者“內在價值”推導的結果,而是因為嬰兒和殘疾人能感受到被傷害的痛苦,動物既然能與嬰兒或者殘疾人一樣能感知痛苦,就能享有權利。也就是說,辛格將權利視為一種并不需要嚴格推導的語言與口號,其實質是強化避免動物受到傷害的保護。
華 南 理 工 大 學 學 報(社 會 科 學 版)
第3期姜淵:需要保護即需要賦權:動物權利論的邏輯錯誤
在動物權利論者中,與辛格一樣將權利二字視為一種動物保護口號的不乏其人,G·L·弗蘭西恩曾經說過“所謂‘權利就是我們用來保護人類不被當作別人財產的一種機制。”瑪麗·沃倫也說過“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幾乎任何一種重要的道德權益都以權利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否認動物擁有權利(不管我們如何細心地對其加以限定),那么,人們就會以為,我們可以對動物做出我們想做的任何行為,只要我們不侵犯任何人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說動物擁有權利,這可能是說服許多人認真考慮“不虐待動物”這一訴求的惟一方式。” [5]所以說,辛格等人提出動物權利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對動物更好的保護。權利只是一種口號,他們的邏輯是“需要更好的保護即需要賦權”。
二、發展的學說:生態保護需要賦權
90年代國內開始關注并引進西方動物權利學說。1993年楊通進教授發表了《動物權利論與生物中心論——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兩大流派》一文,為國內在環境倫理的大背景下研究動物權利奠定了基調。此后,有學者將動物權利的核心矛盾歸因于“道德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問題”[6],也有學者將動物權利的核心矛盾歸因于“天賦價值的論證標準問題”[7],但總的來說,國內倫理學界對動物權利的論證鮮有新穎的觀點與突破性的進展。
相比倫理學界對動物權利研究的乏善可陳,深受環境倫理影響并正蓬勃發展的環境法學界不僅密切關注著倫理學界的研究進展,并且結合自身的環境保護需要,對動物權利有了進一步的研究與論證。陳泉生教授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出發,提出“生命平等”這個概念,討論人們應當尊重其他生命體的生存權利。首先,陳教授的出發點是物種的多樣性保護,物種多樣性是生態保護的一個方面,也就是說他的研究是為生態保護而服務的。其次,在分析“生命平等”這一邏輯時,他提出其他生命體具有“平等價值”,“平等價值”指的是任何一種生物對于生態系統的和諧運行與發展都具有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的價值。這里所說的價值指的是生物的存在對于生態系統的有用性,平等指的是在生態系統中每一種生物的有用性是其他生物無法替代的。換言之,“平等價值”就是每一種生物具有的獨特生態價值。最后,他借鑒辛格等人所提出的動物權利理論,認為賦予動物權利可以實現動物的“平等價值”,最終達到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陳教授認為,動物的生態價值是必須予以肯定與尊重的,如同人類因為自身擁有獨特的內在價值而被獲得權利,動物既然具有獨特的生態價值,就應該賦予他們權利。[8]由此可見,陳教授的動物生存權論遵循的是“需要生態保護即需要賦予動物權利”。
此外,江山教授從法律對主體的保護邏輯論證動物權利的證成。他認為,法律是以主體為核心的邏輯體系,因為法律的根本是對主體的保護,法律保護的范圍即是主體的外延范圍;包括動物在內的自然資源與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必須獲得法律的保護。如果將包括動物在內的自然資源與環境排除出主體的范疇,那么法律將無法保護它們。如果法律將包括動物在內的自然資源與環境作為客體進行保護,那么對它們的保護無法對抗主體的意志,最終無法實現真正的環境保護。江教授將法律的保護范圍做了一分為二的劃分,法律對主體是絕對的保護,而對客體是相對的、為滿足主體需求的保護。環境危機是因為人類過分侵害自然而造成的,如果將自然作為客體保護,是無法對抗人類這一主體的侵害意愿的,法律也就無法從根本上對自然進行真正的保護。然而對自然的保護不僅必要而且迫切,所以為了滿足保護自然的需要與解決法律將自然作為客體保護不力的矛盾,只有在現有的法律體系內擴大主體的范圍,賦予自然以權利。[9]簡言之,就是不賦予包括動物在內的自然資源與環境權利就無法解決環境與生態的危機,只有賦予它們權利,才能保證它們得到真正的保護,最終解決環境與生態問題。
除了結合生態保護論證動物權利的內在邏輯,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動物權利能滿足生態保護的外在效應。陳慶超博士在分析動物權利時候提出,動物權利具有三項基本觀念和實踐準則,除了不應該無故造成動物痛苦以外,還應該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給動物繁衍的機會,以及應該給動植物留下它們自己的生存與活動空間。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給動物繁衍的機會是說,動物的繁衍是符合生態系統自身運行規律的,有利于維護生態環境并最終保障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給動植物留下空間也是給人類留下生存的環境與空間,因為人類與動物一樣生存在同一個地球,這里動物的利益需求與人類最終利益需求是一致的。另外,陳博士還提出動物權利具有兩種外部效應,一是能體現人類高尚的道德情操,二是能具有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現實效用。人類與動物是息息相關的共生關系,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最終能受益于動物的生存與繁衍,陳博士基于此認為賦予動物權利是保護動物并最終使人類克服環境危機的有效手段。[10]與之相同觀點的還有陳偉博士,他認為相較于行為能力的局限,動物更應該被考慮的是“生命自由”——也就是動物作為生態多樣性的存在價值,由于行為能力的局限而不承認動物權利的法律將會因為無法履行其生態保護職能而走向失敗。[11]
總結國內動物權利論者的邏輯,雖然各者論證的角度不同,但往往包含著“需要生態保護即需要賦予動物權利”這樣一條邏輯。而將之與辛格等人“需要更好的保護即需要賦權”的邏輯相比較,雖然兩者中保護的含義不同,后者指的是對動物更好的保護,前者指的是生態保護,但其本質是相同的,兩者皆以動物需要保護作為論證動物權利的條件,可以歸納為“需要保護即需要賦權”。
三、對“需要保護即需要賦權”的批判
動物權利論遵循的“需要保護即需要賦權”邏輯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錯誤,就是 “需要保護”與“需要賦權”并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首先,需要保護并不等同于需要賦權;其次,動物需要保護也無法推導出動物需要賦權;最后,賦予動物權利不符合動物保護的客觀現狀與現實需求。
需要保護不等同于需要賦權,在“需要保護即需要賦權”中,保護是目的,無論這個目的是出于滿足人性的悲憫還是滿足環境保護的需要,賦權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目的不等同于手段,實現保護目的不等同于實施賦權手段。雖然賦權與保護是有關聯的,賦權手段往往是為了實現保護目的而實施的,例如賦予自然人以生存權,目的就是為了保護自然人主體的生存利益,但保護目的并不一定是通過賦權這一手段得以實現,例如一個自然人在山林中躲避猛獸的侵襲,同樣是保護了自己的生存利益,但這與賦權沒有任何關系,純粹屬于自然人本能的自救行為。由此可見,保護目的不等同于賦權手段,需要保護并不直接等同于需要賦權。
實現保護目的既可以通過賦權手段,也可以通過其他手段,需要保護不是需要賦權的充分條件。權利的定義是紛繁復雜、眾說紛紜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權利是從主體自身出發最終指向其利益,賦權是從保護對象的利益出發,為其設置的多維保護體系的行為,與單純的保護行為的區別在于:它對于主體來說是一種自由,而不僅僅在于它能為主體帶來利益。辛格的“需要更好保護即需要賦權”邏輯目的在于批判以往的動物保護不力的困境,但其邏輯出發點依然是人類的悲憫之心,區別只是在于將以往單純對第三者(動物)的悲憫轉化為感同身受的悲憫。“需要更好保護即需要賦權”的邏輯核心在于人類而非動物,動物雖然具有感知痛苦的能力,但這只是更加喚起人類對其悲憫的理由,離開了人類的悲憫心理,或者說如果人類冷酷地罔顧動物的感受,則依然不產生人類保護動物的關系。而賦權是不以他人的道德或者感受為要件的,以即將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的生存權為例,無論他人對他的罪行多么深惡痛絕,無論社會多么想處之而后快,無論他短暫生存的幾個小時能不能提供更多的利益,但在執行死刑之前他的生存權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因為他尚未被剝奪的生存權是不以利他性為必要條件的,這一點與人類基于對動物的悲憫而保護動物有著本質的區別。由此可見,辛格提出的動物需要更好的保護并不能推導出賦予動物的權利。
生態保護需要同樣不能推導出動物需要賦權,陳泉生教授等學者的“動物的生態價值是一種獨立于他人的自我價值”的看法是不準確的。動物的生態價值與其經濟價值的確存在著區別,前者并不像后者一樣直接滿足人類的實際需求,并且前者也為除人以外的生物提供生存與發展條件。然而,動物的生態價值最終仍然是為人類服務的,人類保護生態環境是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其他生物的生存與發展利益由于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而與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利益保持了一致,人類最終是為了自身而不是動物才去保護生態的。人類在生態保護時依然遵循著以人類自身利益為標準的評判方法,對于生態系統本身來說并沒有好與壞之分,地球本身并不在乎它承載的是鳥獸齊喑的沙漠還是生機盎然的叢林。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保持著動態平衡的生態系統,絕大多數的動物的存續是生態系統保持平衡的基礎,人類就需要給予保護,而在特定時刻特定地域某些特定的動物的存續不利于生態系統的平衡,人類就不應當也不會給予保護。例如在許多外來物種入侵導致生態災害的地區,人類往往會想盡辦法消滅泛濫成災的外來物種。由此可見,動物的生態價值是有利于人類的價值,并不獨立于人類存在,人類保護生態環境中的動物是基于自身的需要,并不是從所謂的權利主體——動物自身出發。
從辛格等人對以往動物保護不力的批判與國內學者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中,我們能理解動物權利論者的良苦用心,他們認為人類無法對動物實施真正滿足道德與生態需要的保護,其根源在于動物與人類的不平等地位,如果賦予動物權利就能將動物置于與人相同的層面,阻止人類基于個體私欲而對其產生的侵害。但人與動物關系的高低其實是相對的,雖然動物權利論的初衷是將對人的關懷普及到動物, 把動物提高到“人” 的地位,但客觀結果卻必然是降低人的地位, 使人“淪為” 自然狀態的獸, 導致“人”的喪失。[12]此外,肯定動物權利還意味著原本清晰的權利概念變得模糊。原本法學意義上的權利是一種“以法律保障主體自由的形式來實現正當利益的手段”,而一旦因為保護的原因將動物權利法定化,權利就變成“權威支持的正當利益”保護。“權利主體”與“被道德關懷的客體”也就無法區分。如果權利可以直接借保護的名義由他人賦予,那么這是否為強勢者把自己的利益包裝成他人的權利加以強制推行提供了渠道, 并最終帶來以權利之名抹煞權利的危險呢?
即使我們肯定了動物權利,是否就能達到最大程度地保護動物乃至保護整個生態環境的目的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回答怎樣對待動物才是真正地保護動物。我們可以引用動物權利論的一個基本觀點,對于整個生態系統來說,動物與人類一樣具有特殊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與價值。地位指的是任何一種動物都在地球生態鏈中處于某種位階,區別只是位階的高低;價值是指無論位階的高低,動物的存在都是保證地球生態鏈完整,生態系統正常、有序運行的必要條件。這種地位與價值是由自然客觀規律所決定的,而不是由人類主觀賦予的。在整個生態系統中,無論動物或植物以至全部環境因子,都有自己的運行規則,動物王國的行為法則,是由千萬年物競天擇的適應性決定的,不是由人的意志所能改變的。無論是從動物自身的地位與價值,還是從整體生態系統來看,“原位保護”都是動物保護的最佳方式。也就是說,遵循動物自身習性,盡量減少對動物所處的自然王國的打擾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動物保護。以人類的方式去影響與干涉動物,無論是侵害還是賦權,其實都與真正的動物保護背道而馳。
參考文獻:
[1]蔡守秋.簡評動物權利之爭[J].中州學刊,2006(6):58-64.
[2]嚴存生.“動物權利”概念的法哲學思考[J].東方法學,2014(1):63-69.
[3]彼得·辛格.動物解放[M].孟祥森,錢永祥,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4]弗蘭西恩.動物權利導論:孩子與狗之間[M].張守東,劉耳,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5]WARREN M A.The Rights of Nonhuman World[J].in R. Elliot and A. Gare eds,Enviro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6]楊偉清.從動物權利的討論看道德的交互性本質[J].倫理學研究,2005(6):100-104.
[7]張德昭,徐小欽.論動物解放/權利論的天賦價值范疇[J].自然辯證法通訊,2004(4):42-48.
[8]陳泉生.論環境時代憲法對其他生命物種權利的尊重[J].現代法學,2006(2):78-85.
[9]江山.法律革命:從傳統到超現代——兼談環境資源法的法理問題[J].比較法研究,2000(1):1-37.
[10]陳慶超,陳建平.效用與崇高:從動物權利理論看人與自然正義[J].中州學刊,2007(3):150-153.
[11]陳偉.再論動物權利的理論基礎——生命自由先于行動自由[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4):98-101.
[12]徐祥民,鞏固.自然體權利:權利的發展抑或終結?[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4):80-88.